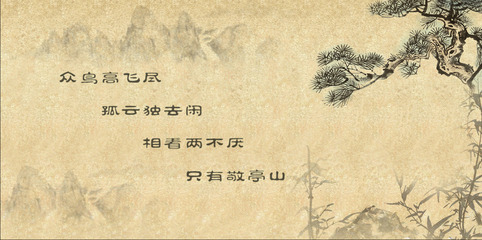诗人海子
诗人海子

如果海子还活着,今年50岁。由1964年生而1989年死,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今天,诗人海子如果回首往事,又将如何谈论他的生、他的死、他的诗呢?世界空旷,往事遥远,过去的与现在的海子,在告别与重逢中,多次与我们互相辨认。
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侧翼的海子,由那时间不定期刊物《十月》的编辑,同为诗人骆一禾的鼎荐下崭露头角。骆一禾长于海子,二人性情与诗歌的语言,都有八十年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内在一致性的狂放,互引为同道。不同的是,骆一禾居编辑一职有话语权,而海子出身安徽怀宁县农家,自闭低调,虽居地繁华北京昌平,却不善于不喜好于主动与外人亲近互动。有关海子诗歌外的生活话题,有限的信息来源,有限的研究资料,零星驳杂无趣,若浓墨重彩则失之偏颇,或不触及,则不能详尽海子的心路历程。即便海子研究权威者、诗人西川编撰的意在回归文本的《海子诗全集》也见左支右拙。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同年5月,海子的诗歌阐释者骆一禾脑溢血身亡,海子一度淡出诗歌的视野。等到1993年,因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自杀的“提携”,峰回路转,再度出现在诗歌的星空。海子自杀之谜,各方面的猜测一或为情所困,一或江郎才尽。缺乏想象力的武断粗暴,既遮蔽了诗人海子现世与超脱纠结的青春焦虑,也误读了诗人之诗自由与理想的同程长途跋涉。诗人之死,震撼巨大而持久,在重创精神的价值与尺度的同时,诗歌与生命的关联也被重新认识。
海子走了,海子的诗歌还在。几乎有同等的意思,似乎诗歌就是海子生命的延续。在小说家看不起诗人,诗人看不起散文作家的文学圈里,诗歌则自有它的狂欢与自恋。每年,在海子的忌日,在各地发起的海子纪念日活动,以及其后渐次举行的诗会,由春天出发,花枝摇曳,一路旖旎。活动与诗会虽是来自民间的自发,性质却有半官方意愿的文化默契。诗歌现场热闹好看,诗人们自说自话,固然其中鲜有新声,但不失有致敬的色彩与意味。
海子与诗歌互为幸事,或以人名,或以诗名,都是身后荣。由“病句走大运”的质疑嘲讽,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传唱诵读,其实,历史并不罕见某人生时“待定”的刻薄,而其身后却有“特定”的厚遇。待定的假设是,如果海子健在至今,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诗坛云卷风舒,其人其诗恐无疑被待定所囊括,诗与名陟罚臧否,不得而知。待定在于今天可以认同,而明天不必有所归属。特定则相对容易,比较而言也合理,如果在诗学广义拓展的范围内研究,海子诗歌自然有机杼见纹理,肯定褒扬值且大于并多于否定贬低值,其诗歌史意义远甚于诗歌的本身。
海子的最后遗言是:我的自杀和人无关。决绝而坚毅的文字里,无论海子是诗人的本身,还是诗歌的象征,都让我们潸然泪下。海子的死是我们生命中跳动的一部分,而诗歌成为我们活着的、见证力量美好的唯一理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