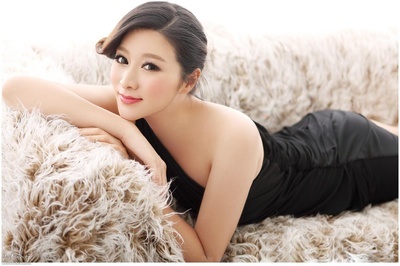异乡的陌生人
——谷禾的诗集《鲜花宁静》读后
赵卡
谷禾的诗怀有善良的意志,我们不妨说这种善良的意志是对世界的一种潜在的致敬,并以修辞性的沉思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那么,我毫不怀疑谷禾是站在惠特曼这边的,尽管看起来他离希尼和弗罗斯特更近,尤其是指间夹着矮墩墩的笔“挖掘”的希尼,谷禾对希尼的朴素到精确的技艺赞叹有加;但惠特曼的滔滔不绝的丰富性风格更吸引他,使得在某种意义上 ,他的声调和气质的浓烈程度完全给人一种美国式的印象。
对我们的不断衰落的古老乡村和无节制膨胀的城市而言,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异乡的陌生人更焦虑和更异己的东西了,还要耐得住连续的寂寞,不从意义本身中找自己的麻烦,对诗人而言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尴尬的东西应该是(虽然有点古怪)身份,因此,谷禾由希尼的身份意识反观到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对“我是谁”的身份问题的追寻,正是他本人已经意识到了却难以摆脱的东西——农业的身体被粉碎成了城市上空的尘埃,像哀歌令人窒息的扩散。那么他非常容易被指认为乡土诗人,其实,他不是这样的诗人,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讲,但人们更愿意接受他是这样的诗人——谦卑,诚实,饱满,狂热,幸福感漫延至文本的每一个缝隙里。
谷禾的诗集《鲜花宁静》足够厚重且具有包容性,在风格上有点像一个诗人的晚期诗作,他所搜寻的记忆材料谜一样的流动着,使人沉醉于其中的确定地视觉形象,超出了一切对象的概念和图式。若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像一个诗人的晚期诗作”此种看法也不算为过,我们闻出了他保存记忆的气息多么强烈,如同普鲁斯特对气味的敏感绝不是偶然的。谷禾的暧昧在于,他的诗本身没有悬念,但他的身份却是乡村和城市中的一个悬念,他有能力倚重经验写出青春的乡土和陌生的城市,并在熟悉的城市中屡屡回望陌生的乡土;就写作本身而言,或许,这才是中国目前最恰当的诗篇,就像叶芝在晚年的诗中重新发现自己并为此感动,因为他突然变得年轻了。在文本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断定,年轻人是绝写不出谷禾这样的诗来,但换种说法,年轻人绝对会喜欢上他这样的诗。
谷禾的诗弥漫着一种令人震惊地狂热,他对句子始终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直觉,按臧棣的说法便是“一个句子的直觉始终比诗的直觉更关键。”我们看到的文本景观是,谷禾那雪崩般的句子追赶着句子,极具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意味,却又不是那种法国式缜密的风格,这种对激情的偏重在中国当下的诗人中是罕见的。谷禾的诗基本上抛弃了寓意,他持续地埋头向内心掘进,这是一种能力,说明他对怀疑主义是持怀疑的态度;他几乎不假思索的自然抒写,而不是出其不意的写作方式,让诗篇如散文结构般灵活简洁,对一般读者而言,这又是另一种能力,这种口语属性的具有活力的句法可以称得上完美。但对另外一些独断的读者来说,谷禾的句法无法称得上完美,他的诗缺乏格言警句,或者可以这么说,完美的句子至少看上去要像格言警句,这和一个诗人的基本素养(关乎技艺)有关,反驳这样的看法还真是一个问题。
谷禾在他的同代诗人中显得如此传统而现代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既不抛头露面也不离群索居,他在城市的气氛中建构铺排他的爆发性诗句,奇怪的是很多人仅仅把谷禾确认为一个乡土诗人;这是偶然的也是错误的,谷禾在他的诗中根本无惧偶然的事物和事件,我觉得,谷禾最准确的身份(也是他最强烈的愿望)是一个心灵诗人。他对事物的敏感是让诗句先于我们发现诗和事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在经验的边界处,谷禾和灵感玩的惊险游戏是让诗意不可遏止的发生。他抒写的题材广泛,不止乡村和城市,举凡游历、阅读、祈祷、思索、回忆和爱情等等,他像一个大诗人敛聚诗歌所能涉猎到的各种主题,他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让各种主题的诗适应他的语法和句法,他拒绝屈服于当下任何时髦的书写范式,他想要构建的是一个与人类的尊严相匹配的世界。
波德莱尔认为“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见的词,这样的词会是透露出什么让他心驰神往。”谷禾在他的诗中融合了多种的修辞手段,桀骜不驯的用词,写出了大量关于自然与人生关系的诗,有着猛烈的视觉和反复的声音效果;他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思考空间和深度,抽象与具体,每一首诗仿佛一个中年人的反省式自问。谷禾对亲人和朋友的关注也是他最重要的着力点,尤其是写父亲,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赞成卡夫卡日记里的一句真实的令人吃惊的话,“我写下的每一句话已经是完美的了。”他对爱情、生死、诗歌甚至政局都有自己的戏剧化的观点,他问,“爱情能在我们的身体里驻留多久?”(《爱情之诗》)这种反讽意味的句子虽带着颓丧的情绪,却又不乏喜剧性成分;“好吧。且看诗歌的光芒怎样沿着我的身体升起来”(《在长途汽车上读扎加耶夫斯基突然停电》)透出一股冷酷的气息,给人一种濒临灭亡的空旷感觉;“每一位亲人和朋友的离去,我都觉得他是替我在死,是我的一部分猝然死去”(《我的悲伤如同舷窗外的白云波涛汹涌》)仿佛孤悬状态下的泣泪怀悼,有一种绝对的被抛感;“我是那个囚在车里忍不住把头脸伸出窗外巴着脖子向前方眺望的人”,“我有了片刻的生出翅膀的荒凉”,在《四月七日上班途中在京通快速路遭遇堵车》一诗中,诗人对孤独渐渐生出了一种真诚的惶恐感,每个被囚的人似乎都携带着川流不息的词语,不免产生出强烈的自足的幻觉来;“昂山素季从满座的军人中间走过”(《昂山素季从满座的军人中间走过》)看上去有点因文生事的意思,但我们真切的听到了诗人的批评的声音,谷禾习惯于观察表象之下的幽暗,他有感而发,绝没有一丝对女性的嘲讽,反倒像是大力宣扬一个观点或命题,“她只是轻轻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子”。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我们没必要把谷禾妆扮成一位诗歌的圣徒,他只是一位有写作态度的诗人。谷禾的《鲜花宁静》在构成了诗人自我认同的空间里到底写了什么呢?我只能这么说,我读到了一种诗人的特殊精神症候,他担忧太过深刻会展示出自己的忧虑和悲伤,他在不断行走中以求得赋予他极端的情感体验,并在体验中完成自我争辩,他崇拜精神序列里的永恒性以及永恒性里的激烈冲突,对他来说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诗学形式;在这本诗集里,谷禾绝不克制抒情的语调,语速迷人般流畅,语句端正而纯粹,风格受制于极度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中缺少秘密的繁复,他表现出来的浅尝辄止正是他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最谨慎的虔敬。最后,我想说,犹如齐奥朗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结果却变成了旅游胜地一样,对诗人谷禾而言,《鲜花宁静》的境遇亦贴切地如此。
2014-10-1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