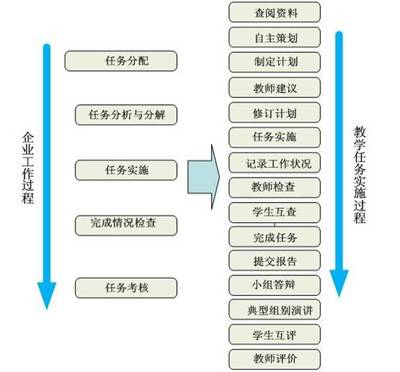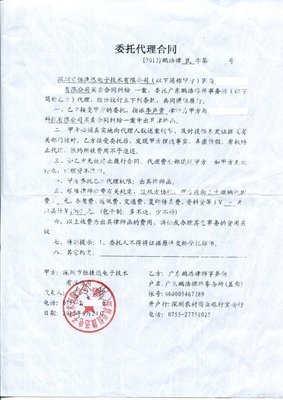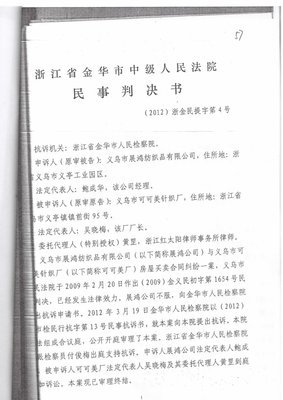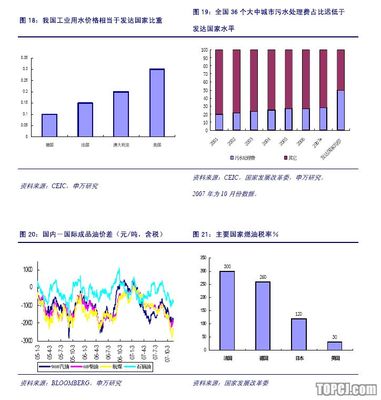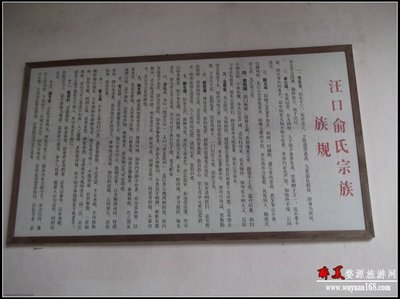
在西周,天子是全中国人民和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但他无法靠个人和直系宗族来控制全部臣民和土地,当时的办法只能靠宗法分封制。他直接控制王畿,此外的则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诸侯。除了王畿内公田的收入 ,他就靠诸侯的朝贡。王畿内分封为许多卿大夫的采邑。同样,各诸侯在其国内也进一步分封。卿大夫在其采邑内再立侧室贰宗,继续分封。这样就建立起一整套宗法统治体系。
周天子是天下姬姓人的大宗,受封的姬姓诸侯对他来说是小宗。姬姓和非姬姓诸侯在其国内是大宗,受封的同姓卿大夫对他们来说是小宗。以下依次进行这种大小宗的划分。凡小宗都受大宗的约束。宗的成立源于所受封的土地。最先受封者死后,子孙奉他为始祖,立庙曰宗。有宗有土,即是社稷。他的嫡长子世代承袭封土,称为宗子。一般来说,天子、诸侯的国法和卿大夫的家法,仅施行于本宗族的范围。宗子对同族人有直接处置裁判的权力,是为宗法。
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规定出人生而具有的等级制度。世袭土地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就成为贵族,疏者也就成为贱者,即隶属于前者的农民或其他平民。后者无权获得土地所有权,但可以通过“受田”形式获得“私田”的使用权而有个体经济。这种受田也照宗法分封办法来实行:农夫从宗族宗子手里受田耕种,其长子长孙亦可在贵族的允诺下世代承袭为户主,成为受田范围内的家族。非长子的余夫如果能从贵族那里得到另受的私田,亦可承袭,另立门户为家族;不得受田的余夫则称为闲民,只能帮助别人耕作或从事工商别业。农户的宗子当然不能有贵族宗子的那种权力,但对其家族家庭也有宗法约束力,尊宗敬祖的观念也完全相同。
中国传统所重的整体乃是宗法人伦整体,因而也得重视在宗法人伦之中有其一定地位和作用的个人,不过这种个人与西方的个人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所重的个人乃是个体私有者,他们之间靠商品交往等形成的社会联结和政治国家,也同中国人的那种整体有别。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更重个人而我们更重整体。无论以往的中国文明的整体性或西方的个性,都不是什么抽象的,可以简单说成是好或坏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是建立在家族私有制上而另一个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上的,都具有双重性或异化性。不做这样的分析、对比,就一定会简单化和片面化。有些人在看到西方个人主义泛滥,战争和罪恶严重突出时,就颂中非西,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重整体、重凝聚,如何崇高等等;而当看到西方重个性自由解放,使生产、科技和社会飞速进步,大大超过中国时,又说些颂西非中的话,认为中国人强调整体,是扼杀个性的发展。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矛盾的话常常出自同一个人之口。
中西公私观很不一样。西方以明确的个人私利做标准,所谓公利一般便是各个私利个人间的社会结合方式。他们的统治阶级政府也标榜公利,自称是全体公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但因为有明确的私利划分,在冲突中这种虚伪性就比较容易暴露出来。在中国则不然。统治者以家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资格出现,并且确实也只有在给整体和各个成员谋得切实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时才能充当这种代表,因而他是国家整体“公”利的维护者和标志。但同时他又借整体内部的宗法结构(靠血缘亲疏,对整体的功劳大小来规定)把自己变为高踞于其他成员之上的特权者,有自己的特殊私利。所以在他们身上公与私就融合为一,互为表里,难解难分了。他要求大家都为国家之公效力,自己也得作表率;他要求一切都为整体并各得其所,同时自己也就有理由攫取最大最多的一份,甚至堂而皇之地化公为私。对此,个人是很难反抗的,只有到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矛盾极其明显尖锐时,才有可能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标榜公而营私,先为公而后为私,阳为公而阴为私的例子真是不可胜数。
历代开国的君王将相多为“圣贤”,统治一稳定就逐渐停滞腐败了。他们是些“君子”,但又常常是些“伪君子”。其实这并不奇怪,而是中国“公”“私”难解难分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双重性有时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时则比例不匀地分布在不同的人身上。例如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以无私的英雄主义气概努力奋斗,艰苦创业,他们在客观上和主观思想上都突出一个“公”字,轻视和仇视各种腐败的现象和人物。这些人是很伟大高尚的。可是由于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大业还是宗法人伦的,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还是宗法人伦的组织和制度,因而这种伟大的形象与功绩,又总在为重建不平等和少数人营私创造着条件。所以这个阶层中的个人虽然优劣悬隔,不可一概而论,却又彼此联结,不断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关系的种种扑朔迷离,根源在于家族所有制和宗法人伦制的统一。家族对外是个私有单位和血缘集团单位。对内部成员而言则是个公有的集体,又是个以家长为首的宗法等级结构。权力财富的等级分配,同以家长为核心的血缘亲疏相配伍,彼此“各得其所”,“各有本分”,从而在“公”的形式中实际贯注了不平等的“私”,又以大义凛然的“公”的面孔维护了这种不平等。所谓国家所有制,在贵族的诸侯国和大一统的王朝里都是家族所有制的扩大形态,实质相同。因此,这里所谓的“公”决非“天下为公”之公,乃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里的“公”。这是“公”的异化,同西方文明里的“公”(如他们的政府、公司之类)一样,都是私有制的变形。不过西方的容易看出些,中国的更加隐晦、复杂些,在含情脉脉的宗法人伦的面纱下更加难以揭露罢了。
有些人不研究其中的曲折联系,看不到异化,见“公”就赞颂,这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同时他们又以此对比西方的“私”,颂此而贬彼,这也是只看表面(其实二者都是私有制)并且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历史动力,对发挥人类潜力有巨大意义,那么就应该承认以“家”为本位的私有,虽然较多发挥了家族集体力和家长个人的作用,却阻碍了其中多数人的发挥。而以个人为单位,以商品关系而不是以血缘宗法关系来建立的私有制,在以往历史上更有利于个人潜力的发挥。西方个人私有制虽然弊端明显,罪恶突出,但又确实为个人的发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宗法制的实质在于把人与人的关系确立为统治服从的君臣关系。但这些君臣关系却主要借宗族的血亲、世袭、长幼等关系来形成、建立、维系和巩固。所以中国古代的阶级压迫剥削制度与宗族关系有不解之缘,与宗法制度密不可分,可以把它称之为“宗法制社会”。例如在西周,统治阶级主要是姬姓家族,辅以与之结盟的异姓贵族(如封于齐的姜太等)。周朝便是姬姓王族之一姓一家的天下。其统治主要靠姬姓分封诸侯去控制,统治各地各族。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权力,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形成大宗,是为周王世系,它是中心;而王的叔伯与诸弟便是小宗;小宗在宗族上隶属、围绕大宗,政治上就成为周王的臣属,形成诸侯拱卫周王的局面。按此办法,诸侯在其的封国内又建宗庙社稷(姬姓诸侯对周室而言是分支),再分大小宗,诸侯世系是大宗,他的叔伯诸弟又是他的小宗,做他的卿大夫即臣下,以维系其地位和对国内土地与人民的统治权力。等而下之,卿大夫与其家臣的关系亦复如此。这样,周天下就靠此宗族上的层层从属关系,建立起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士、庶人等许多层次的统治服从关系,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秩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