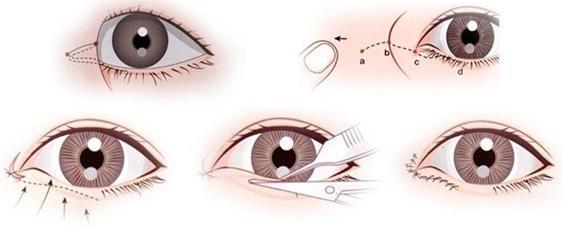苏雪林
(一)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苏雪林,感觉她太好强,太刻苦,以致,有些------无趣。
写下这段话,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一直不太愿意这样描述一位已故老太太,可我又无法说假话。踌躇着,犹豫着,最后想,我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女子记录一下自己当下对老人家的了解和真实感受,应该也不为过吧。
苏雪林早慧应该不假,但灵动、敏锐、有韵味可能就谈不上了。她涉猎学术、美术、文学不同领域,强在她的刻苦、自勉,一生写了40多本书,两千多万字,实实在在著作等身,可她自己都说,“我写的东西,无论学术研究也好,文艺创作也好,评论时事也好,就是没人看,被人提到的永远是那几篇选在初中国文课本中的‘短文’,这种现象怎么不令人气结?”她的学生唐亦男引用作家萧乾的话作推论,“是不是因为跨越了两个世纪,不是走在时代前面,就是已经与时代脱节,所以得不到读者共鸣呢?”这叫什么理由?!
苏雪林耗费了毕生的心血写作,她太希望流芳千古了。可是,这类愿望哪能由得人自己做主呢?她自己认为四十来岁,她没有按照一般人生理、心理的走向,产生感情纠葛第二春之类的问题,而是升华为创作,写出她以为最具文采的《青春》、《中年》、《老年》、《当我老了的时候》等等,我今天读来,并没有看到哪怕一句让我心里一凌的句子。难怪同时代才女张爱玲,孤傲地只愿意别人把自己与苏青相提并提,其他女作家她是看不上眼的。喜好、口味各有不同,可是天分、才气的确不是人人都有,就算你瞪大眼睛,攥紧拳头,龇牙咧嘴,上窜下跳,也是枉然。前不久狂小子韩寒做客湖南电视台,评价了几位大师的文采,遭到不少议论,他后来在博客里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作为一个作家,文笔和文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必须要拥有独特和出色的文字技术和文字风格,这是所谓的思想性和感情真挚是不能代替的,这也是汉字的魅力所在,中国历来的作家都是很看重这点的,从诗经开始,到唐诗宋词,到四大名著,无不如此,再到后来的白话文中,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胡适鲁迅沈从文包括张爱玲都做的都不错。”
文笔和文采是需要天分,需要鬼斧神工的,这一点有点像“幽默”和“机警”的关系,林语堂说过,“幽默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刻的。”我们通过刻苦努力,可以做到机警,至于幽默?难!想文采斐然,跨越几个世纪的流传,单纯依靠勤勉和刻苦,实在也够难!
(二)
好像有人提到过,苏雪林小时候画画,别人要看,她觉得不够好,三下两下,把画撕掉也不让人看。我觉得这样的小事很能说明她的性格。与别人第一次大的冲突,是在她18岁,进入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那时候,她成绩好,又擅丹青诗词,自然傲视群芳。不承想皖北一富家女的转学入校引起一场风波。那女孩子公然挑战,扬言要盖过苏雪林,(那时候她还叫苏小梅)。两人各有拥趸,类似今天的粉丝团,两大阵营少年气盛,明争暗斗,最后闹到对吵、谩骂,于激烈处,为首的两位还动了手,学敌揪了小苏同学的头发往墙上撞,小苏同学性格何其刚烈,连来这里上学都是以跳水自杀相威胁才争取来的机会,还怕打架不成?抓起一块砚台,砸得女孩子头破血流。后来事情还发展到罢课学潮,影响很大,学校给小梅记小过,给学敌记大过才了解了此事。至于学业上的PK,究竟谁胜谁负?苏雪林自己说以几分之差险胜,石楠却在给她写传时说,苏雪林以几分之差惜败。也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有一点倒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挑灯夜读,夜夜苦熬,苏雪林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苏雪林后来说自己后悔的两件事,其一就是这件事,其二是为了跟其他女同学攀比,逼着母亲为自己准备漂亮衣装,为难了可怜的母亲。
只是她似乎终生好斗,第一次留法期间,又混迹于其他学生当中,背信弃义,违反协议,向有恩于他们的教育家吴稚晖举起反旗,苏雪林在自传中反思:“我们竟以自己一念之私当作热烈悲壮争公理的举动自鸣得意。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为耻。”而伴随她大半生的骂鲁事业也多少源于性格因素。
个性往往源于家庭环境合成长经历。苏雪林的奶奶似乎有着欺软怕硬的秉性,有着好几个儿媳妇,却最喜欢欺负生性孱弱的大儿媳——苏雪林的母亲。明明家有女佣丫头,偏偏只要儿媳伺候,单说这按摩推拿一项,“我母亲的右手拇食两指常瘀着血,作紫黑色”,而苏雪林的奶奶整日卧床,还得善终,多亏了雪林母亲终日按摩让她经脉疏通。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为了让自己儿子有奶吃,她自己不喂奶,还强迫雪林的妈妈放下自己的儿子,去喂养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小叔,以至于苏雪林的大哥落下胃病,年轻轻就送了性命。如果奶奶对谁都这样刁蛮霸道倒也罢了,偏偏有续娶的儿媳来自官宦之家,根本不吃她这一套,还敢跟她对骂,结果她没辙,只有偷偷抹眼泪,然后变本加厉地欺负逆来顺受的苏雪林妈妈。
这一切想必给了小女孩强烈的刺激,要做强人,要出人头地,这样的念头在小女孩心里萌芽应该一点也不奇怪。也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苏雪林一直发愤,一直握紧拳头,一直以刻苦争斗的姿态呈现她的生命,就在1957年,她61岁那年,从1月6号到3月5号两个月的时间,除了读书,还写下五万多字,因为过于劳累,眼病加重,右眼几乎失明,能够这样投入,当然有着精神上的享受,希望赢得外界肯定的愿望当然也是动力源。
据说她在解放前夕曾和邓颖超见过一面,邓夸她文章写得好,很爱读她的《绿天》。苏雪林非常兴奋,还对人说,“共产党里有人才!”别人的夸奖和认可,会影响到她的情绪甚至对人对事的认知。
她去法国,先是希望学美术,感到自己功底差,来不及,后来转向门槛低的写作,一方面因为在大学任教,工作的需要,也多少为了和一般的女作家有所区别,她着手相对枯燥、单调、理性的学术研究。也出过一些成绩,可是后来偏狂到非要把屈原的楚辞和西亚文明联系起来,当时有一批中国学者出于缺乏自信,试图寻迹中华文明源头于西亚两河文明。苏雪林也并非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拗于她的研究和考证。谁提不同意见,她就跟谁急,甚至连胡适提醒她研究方法不对,她也差点翻脸。她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终于在1980年,以83岁高龄推出180万字的《屈赋新探》。不管别人怎么说,她终于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完成了她的研究。这倒也真正体现了她出身徽骆驼特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有这股劲,总能折腾出点事,不然天都不答应。
但是如果真如胡适所言是错误方法错误方向上的研究,我无限悲哀地想起白岩松的一段话,“最棒的人是又聪明又勤奋,其次是聪明但懒惰,再次是愚蠢还懒惰,最糟糕的是又愚蠢还偏偏勤奋,因为破坏力大。”但愿老人家还是第一类吧,我无力研究她做的学术,不敢也不愿意刻薄老人家。
(三)
不过,正是因为有着学术上执拗和寄托,她才可能摆脱许多寻常和不寻常女子在情感上的烦恼。
她16岁那年,父亲指定了她和在上海做五金生意的张家的婚事,希望成名成家,希望得到更多人认可的苏雪林当然不满意者束手束脚的婚约,在她留学期间,有一位曾经失恋的男子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她也心动过,也权衡过,可是在父母和社会的压力之下,她忽略了自己的情感。实际上她的情感似乎也没有那么细腻和敏感,在她尝试着去接纳和了解那个指定的未曾见过一面的夫君张宝龄之后,对这个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机械系未婚夫,只是通过鸿雁传书,一来二去,在张结束学业之际,居然就主动邀请他来法国完婚,甚至还准备起结婚的嫁衣。没承想这样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于是,苏雪林羞愤交加,有多少成分是因为自己的情感得不到呼应,又有多少成分是因为唯恐自己成为笑柄,也许,丢脸让她更为心痛。
她后来写了《绿天》,在《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里交待原委,为自己挽回面子,更有一篇篇美文粉饰自己甜蜜的婚后生活,可怜她自己也承认,那是最甜蜜的谎言。缺乏的,需要补充的,便在脑子里臆想,在笔尖流淌了。不管怎么说,那时候的苏雪林还有着女人的体察和角度,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也因此这本虽然满是谎言的书还是打动了许多人,为她赢得了名声。
她和张宝龄的婚姻是失败的,虽未离婚,过了争吵的头两年后,几乎一直在分居中有名无实。苏雪林太少花心思在为妇之道上,她有着别样的野心和抱负,视野根本不在灶台闺帷之间。在她眼里、心里都没有为张宝龄留下足够的空间,再木讷的人也能感觉到心的温度。苏雪林对张还有怨辞,因为信教的原因又不能离婚,就这样分居两地,互不来往。没有看到张宝龄这个老实木讷的工科男子只言片语,他后来过继了兄弟的儿子,也就安稳过日子了吧。
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子有着相当的名气,婚姻不和也是众人皆知的秘密,按理说那些才子或者貌似才子的人,应该环绕周围作狂蜂浪蝶状,就像同样姿色平常的苏青,虽然也许没有人真心要娶她,但示爱者接二连三。苏雪林没有,似乎只在武汉大学时有一个体育教师表达过爱慕之心,和圈子里的人并没有什么绯闻传出,顶多也就是猜测她暗恋,还无法断言,那暗恋对象究竟是她的那位著名老师,还是她大半辈子谩骂的另一位名人?
从有些事似乎可以得到一些有意味有关联的推测。苏雪林是吃苦耐劳之人,也有些生活的情趣,新婚之时还有后来随武大迁居四川乐山的时候,都曾经种植大量蔬菜瓜果花卉,还不辞辛苦兼任泥水匠、木匠等等。可是就像写文章,她似乎把笔墨用得太实,在文人眼里未免失了美感。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曾经为了给猫杀跳蚤用了樟脑丸,害死了几只可爱的小猫,又为了把一株合抱粗的芭蕉移植到窗下,因为不思量自己搬不动也拖不动而白白送了芭蕉性命。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有勇无谋傻大姐的意思,没有够分量的智慧,也没有轻巧的聪敏,甚至没有平常人的瞻前顾后。她自己也说,“然而我现在虽说能劈柴、能种菜、能做一点木匠和泥水匠的工作,却还不能好好烹调一顿肴膳,好好洗清一床被单、一顶帐子,好好缝纫一身衣服”,这样的女子既不实用,也不风雅,难免因为过于粗重、硬朗,不太讨异性喜欢。
苏雪林大半辈子都是和姐姐子在一起相依为命的生活,这也许是合适她的方式。婚姻虽然是两个人的,更是一个人的,完全是一个人内心对对方的心理体验,同样的情形在甲是天堂,在乙可能就是地狱。苏雪林对于爱情,似乎没有多少细密的心思,衣食无忧,心无旁骛,专注于她的事业,也许就是她最想要的生活。
(四)
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授课的时候,因为写别字、念错音受到学生的告发,自学成才的人往往像这样“开口奶”不好,怕她误人子弟,很多教授主张解聘她,幸亏王世杰校长力排众议,说有学问的苏远胜过不懂运用学问的“两脚书橱”,这才得以续聘。在苏雪林的自传里,提到这一幕时,特意用括号加了这样的注释“别字是拜采五先生及杜表叔所赐,讹音则拜我父亲所赐”。也许是我过于敏感,字面下隐隐的怨恨和不满让我不太舒服,难免猜测她是一个习惯指责,不习惯自省,习惯怨愤,不习惯感恩的人?
确实有人把她当作“睚眦必报”之人,譬如他的反鲁,有人说是因为她暗恋鲁迅得不到呼应,因爱生恨,坚决站在了反鲁的第一线。我发现她与鲁迅真正的交往实际只有两面之缘,1928年3月14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说,“中国文人的私德,实在是好的多,所以公德,也是好的多,一动也不敢动。白璧德and亚诺德,方兴未艾,苏夫人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者欤?”“苏夫人”即苏雪林。信中提到的“结婚纪念册”是指《绿天》,这本书首页就印有“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的字样。
这大约见过的一回,未见苏雪林提及过,第二次见面倒是相互印证了。鲁迅1928年7月7日的日记,“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并女及侄”,看上去着实平常平实又平淡,无风也无浪。可是在苏雪林心里却翻江倒海,按苏雪林的说法,众作家都对苏雪林客气友好,只有“鲁迅对我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她认定鲁迅是恨着她的,还推测是因为她在鲁迅论敌陈源的《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的缘故。
联想起一件往事:《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出版后,苏雪林曾想请人代呈梁启超,结果遭婉拒,苏后悔自己没有寄一本给他,因为“得任公先生揄扬一下,岂不声价十倍”!老太太七、八十年之后,还不无遗憾的念念不忘错失良机。
我猜想事情也许是这样的,在一个什么机会下,苏认识了鲁,苏自然很兴奋,对鲁也许谦恭有礼,有点文艺女青年希望得到提携的模样。第二次见面原以为可以一回生二回熟,如得鲁迅“揄扬一下,岂不声价十倍”,所以特意带了一本《绿天》,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没想到鲁迅没有预想中对文艺女青年的热情,虽然还是送了书,火热的心即刻变得“拔凉拔凉”的,他原来不赏识自己,甚至都不记得自己了。这对于苏作家的自尊构成了伤害,如果她知道现在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里的这部她送的结婚纪念册,毛边,却没有裁开,似乎鲁迅没有读过。她会怎么想?如果“鲁迅藏书”中另有一本,也是毛边,却裁开了,翻过了。她又会怎么揣测?
苏雪林可能不知道鲁迅藏书里有两本《绿天》,她题赠的那一本似乎没有看过,没有题赠的一本则好像翻阅过。不管这是一个怎样的谜面,在我看来鲁迅并不一定恨着她,她甚至不一定在鲁迅很郑重的视野里,浅浅的记忆里无非一个能写结婚纪念册的女子吧。但是,那个女子难道把这样的漠视当成了莫大的伤害?
(五)
苏雪林是在鲁迅去世,人们悲痛哀悼的时候,亮出反鲁旗帜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她坐卧不宁中于11月12日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托人带给蔡元培,但别人看信如此激烈,没有带给病中的蔡先生。
葬礼过后,心有不甘的苏雪林将这封信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在了武汉新办的一本杂志《奔涛》上,一时间,像扔了一枚炸弹,各方人士反映强烈。信里不乏人身攻击,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嫉”,“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等等,完全是泼妇骂街的架势。
她似乎忘记了,同一个她,曾经在《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四期发表论文,充满激情的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认为他的代表作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还高度评价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站到永久的地位了。”论文发表在1934年11月2日,是令苏雪林不快的宴席之后,可见那时她并没有张扬内心的刺痛,反而还是大唱赞歌的。可是永远真是太短暂,不到两年的时间,苏雪林就来了个180度的华丽丽地转身。
对于她的手法,她的老师胡适都看不过眼,曾写信规劝:“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馀如你上蔡公书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胡适,这个向来对女弟子温文尔雅的博士,忍不住严肃地告诫苏雪林,“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对于老师的教诲,苏雪林并没有听进去,从亮出旗帜的那一天起,就咬住鲁迅,不遗余力。1988年11月,已经91岁的苏雪林,还是没有冲淡平和的习文,她撰文《大陆刮起反鲁风》,说有人在鲁迅日记里发现“每月某日,招妓发泄”的记录,说他外表像孔老二,也搞起玩妓女的事。事实上,在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当时正值上海“一。二八”战后,不少少女失去亲人,沦为孤儿,难免流落酒肆,卖唱为生,鲁迅邀来一谈,与以一元,怎么就成了招妓呢?!
苏雪林不管这些,不求证,不思考,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不管真相,就狠狠攻击,甚至到了丧失基本鉴赏力的地步。我们都记得《野草》里散文诗《立论》,鲁迅举例说,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贺喜的人中,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了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收了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遭到合力痛打”。如果既不想撒谎又不愿意被打,“那么,你得说,‘唉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喻!哈哈”有谁看不出先生是在讽刺世故、虚伪的人生吗?苏雪林看不出来,她认为这恰恰是鲁迅唆使人家怎么世故,怎么虚伪。她是怎么了?如果看不出来,她实在太笨;如果看出来还故意歪曲,那她的人品?
更为惊悚的是,1936年底她在《论偶像》一文里,骂鲁迅是臭秽之物,却被人奉作偶像,因此居然提议“改窜原著”,“改窜原著,我以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补救办法”。如果原著都可以想到去改窜,那么歪曲、肢解、片面,还有什么不可能?
回望这段历史,我只能叹息,还是叹息;摇头,还是摇头,究竟是什么蒙蔽了她的心灵?
(六)
对于苏雪林的反鲁,有几种猜测,一种是“党国”效忠说,因为一开始就担心“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1966年她将自己骂鲁文章合集出版,题为《我与鲁迅》,也不无夸张的认为,国民党丢了大陆与鲁迅有关,如果鲁迅在台湾登陆不到半年,台湾也将赤化,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可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在别人再三动员之下,都不肯参加国民党呢?也有一说说苏雪林对鲁迅单相思,因爱生恨,她自己不承认,我也觉得有点像“恨水不成冰”的臆测,缺乏可信度。她自己在接受陈漱渝采访时说,“我对鲁迅反感,主要是因为他人格分裂。鲁迅一方面从国民党的文教机构领薪,每月得二百块大洋,至死才罢;另一方面又在文章中轻蔑地称国民政府为南京政府。”这样的理由似乎也不足以支撑她几十年歪曲、辱骂、甚至造谣的热情。
无意中看到斯琴格日乐打赢了官司,那个挑起事端的金莎要赔偿她一万元精神损失费,并且删除博客。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官司了吧,大家隐约知道一个开头,青春美少女揭露资深美女“泼妇骂人”,有谁真正关心事情的真相呢?当事人不定正捂着嘴躲在角落里偷偷乐呢!例如我,原来哪知道这个叫金莎的造作美女,现在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一心想出名的“雏”,还看了她的部分博客,知道她以前就懂得故作神秘地虚假炒作自己和曾经的师兄JJ林俊杰子虚乌有的所谓“恋爱”,顺带还知道小妮子的什么美容新书要出版了,就在9月份。这场架吵得真是时候,不知道新书会多卖几本?
以前也有人曾发现规律,每当那英要出新专辑,就会有她和高峰分手或复合的消息先期喧嚣尘上。吵架、绯闻、走光甚至车祸,都成为炒作的常规手法。我无所事事突发不太善良的联想,就像《发胶星梦》,40多年前的胖女孩其实就是超级女生们的鼻祖,苏老前辈有没有可能也早早尝到了笔战,用笔战炒作的的甜头呢?
顺便梳理一下,最早让她扬名的一场论战是在1921年,她25岁,进入北京女高师第二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女子周刊》,批评了谢国桢的《白话诗研究集》,没想到引来谢国桢支持者的忿怒,在报纸上开始对擂。这场笔墨官司甚至引起了胡适的关注,在《晨报》登出《启示》,反对以名字压制舆论,以行动支持了苏雪林。这场论战让苏雪林名声大振,引起京津沪文化圈的广泛关注。
苏雪林一直很在乎自己作品的反应,可是也正如她所说“我写的东西,无论学术研究也好,文艺创作也好,评论时事也好 ,就是没人看,被人提到的永远是那几篇选在初中国文课本中的‘短文’,这种现象怎么不令人气结?”气结之余,会不会想起当初声名初起的“论战”这一招?
苏雪林非常善于争辩论战,30年代,曾经参加过好几次轮战,那基本上是学术之争,影响也远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也许她会有些不甘心,某个夜晚,突然来了灵感,如果选中鲁迅作为开火对象,又是在国人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那爆炸的当量何其了得!何况现在鲁迅已死,不可能再提携自己,再加上第二次见面一直郁积在心头的不快,凡此种种,会不会促使苏雪林在鲁迅去世,哀声一片的时候,奋笔疾书4000字,孤注一掷地发表在《奔涛》上?
类似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现在不还时不时有文人借助大骂名人来提醒公众别忘了自己,不甘寂寞又没有足够的信息量吸引聚光灯,骂名人不失为一条捷径),反响的确强烈,各地报刊争相刊发声讨苏雪林的文章,苏雪林很有雅兴的把这些文章剪下来,捆在一起秤了一下,五斤多重。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她是在秤报纸还是在秤别的什么呢?
但是,苏雪林内心非常失落,她一直盼望左翼重要作家茅盾、田汉、郑振铎、丁玲、胡风等人“站出来同我说话”,可是,“左派重要文人并无一人出面”,甚至书信的对象蔡元培先生都未置一词。这种只把谩骂当做蜘蛛网拂掉了事的态度,其中摆明的彻底的轻慢和不屑,真的要让苏雪林“气结”。
苏雪林把反鲁当做了半生的事业,时不时发出声音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被骂的人死了,他还要骂,大约要骂到自己也死了,这一桩‘骂人公案’才能完结”,这本是她写在《论鲁迅的杂感文》里攻击鲁迅的句子,岂料成为自己的真实写照。
当代文坛多数人都认为苏雪林对于鲁迅的攻击带有狭隘的偏见,“苏的这种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除了在读者面前暴露她自己的卑劣和下流外,如果有人要加以批评或辩驳,都全是亵渎笔墨的事!”骂人终究不是文人的正道。
苏雪林一生刻苦勤勉,如果留下来的标签,只是“反鲁”,肯定不是她的本愿,幸亏,她还有其它可堪告慰的标签。

2008,8,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