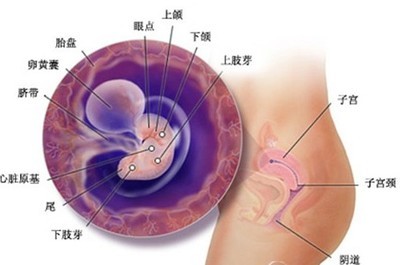中国,你准备好了么?
——为《我提倡真正学》出山送行
張懷遠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任何事情的成功,前提都必须是思想正确。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欲想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思想曾经准备好过么?当今的改革,思想已经准备好了么?
一味向后看是没有出息的
翻阅中国历史,一般在革命时反儒批孔,守成时崇儒尊孔。虽然在批与尊之间并没有梳出清晰的思想理路,但也反映出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21世纪初的中国,改革正处在焦灼和胶着状态,有嘴上空喊,身子不动的;有明唱改革,暗盼守成的;更多的是希望真改革,却找不到路径或无法推动。正当此时,一股儒家的势力夺路而出,大呼“儒家的出场适逢其时”。这不能不耐人寻味。
要之,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思想或思潮,即使荒谬,对后人也还有研究、参考或启示的价值,起码有档案的意义,更不必说有建设性和建树意义的思想了。儒家思想中当然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儒学作为一种曾经被独尊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东西(历史上就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它毕竟过时。落花流水春去也,风光不再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推而广之,岂止一种儒学,世界上任何主义和学说,都不过是一得之见,充其量只能解一时之困。饭总是要不断地做,不断地吃,留到明天就是旧饭,或许变馊,或许发霉。没有人可以提前做出让人吃永年的饭。除了精神,没有永远的万岁的东西,哪怕它曾经是真理。任何一种虎虎有生气的理论或主义,都不可能永垂不朽,各领风骚十数年或数十年就不错了。有的主义(主意)的生命甚至只有一秒的时间,过后就没有意义,比如打枪时候的瞄准,其意义就在扣扳机之前的一刹那,一旦子弹射出,主义(主意)的使命即告完成。
人类一直在路上。需要不断地创立寻找继续前进路径的思想和理论,不能指望祖先承包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所有难题。不要误以为古人已经把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事先给我们都准备好,我们可以像查字典那样对号入座就可以了。那样的话,岂不像一个劲地缠着祖爷爷讨要压岁钱的孩子一样可笑么?要明白,祖爷爷们没有背着为后代排忧解难的义务,不要死抓着他们不放。自己的困难还需自己想办法解决。遇事不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图谋从老古董中寻找答案,是一种不自信的体现。那种希望一镢头从地底下挖出一缶黄金,从而跻身权贵的想法,是一种幼稚和蒙昧。
从许多事实和现象,可以看到当今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就是遇到危难,总习惯返回头从旧武器库中寻找兵器。可惜,旧库里的刀枪剑戟等,已经不敌今天的电脑信息战,不中用了。当人们感到不请回老子、孔子这些古人,就没有着落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贫困?
此外,还应该注意,文化经典是有可能变为文化桎梏的。因为人性中有“刻舟求剑”的弱点,容易把标志阶段性的“记号”误认为是永恒的真理,从而造成自我误导。岂不知,老祖宗根据住山窟洞穴的现实找到的思路,拿到有暖气的楼房还能用吗?传统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有时候,它会像死人一样,紧紧拖住当代人的身子,绊住你我他的腿。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破除另一种迷信
对纯粹虚无的东西笃信不疑,对纯粹虚假的东西信以为真,是一类迷信。传统的对于人格神仙的信仰就属于此类迷信。还把庸俗作风带入:用金钱贿赂“神”的办法免罪消灾;用向寺庙布施的手段祈求赐福保平安;以为把《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小说人物当“财神爷”供奉起来就可以发财;甚至平时不烧香,有了灾难才慌忙抱佛腿。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笑话却不自醒。
人类的迷信仅此还不够,更有新奇者,遇事总想推源溯始地从祖宗那里找根据,一部《论语》要管千秋,一本《圣经》要念万代,“《古兰经》是我们的律法,圣战是我们的路径,牺牲在通往安拉的道路上,是我们的终极理想”。现实中的困惑,从原教旨那里寻找出路。所以,东西冷战结束之后,原教旨主义的喧哗和躁动,足以让整个世界惊骇。近些年来,国内儒学走红,有些人误导儿童重穿宽袍大袖的古装,咿咿呀呀地捧读《弟子规》之类的古书。不是说《弟子规》不可以借鉴,而是不能用匍匐在书下的姿态去读。明明是误入歧途的闹剧而不自晓。
复古怀旧可能是一种通病。康有为什么要“托古改制”?从孔子到现在,为什么总有人歌颂夏商周三代圣贤?如今又有人怀念毛泽东了。假如历史隧道畅通的话,我很想送他们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尝尝当年阶级斗争的残酷味道,叫他们体验一下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酸楚滋味。说老实话,幸亏我当年没有饿死,否则,今天哪会坐在这里做文章?!
迷信的尽头是解放。当今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对象,包括以上两种迷信。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或许更紧迫些。
人类前进的标志,是不断有原创意义的精神产品出来,而不是在死抱着《论语》、《圣经》、《古兰经》不放的状态下过活。不仅独尊儒术不可取,独尊任何主义都不可取,都有可能走向迷误。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任何主义也都有局限性,只有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万古长青。人类历史上,在一个相对不太长的时期内,集中地适用一种思想或学说做指导,是可以的;假如靠独尊某一种主义作为统治思想长期讨生活,还要“罢黜百家”,没有不跌跤子的。
人类的新纪元是依靠原创性思维开启的。物质的新陈代谢在不断进行中,思想的更新在不断进行中,每个人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自我,整个世界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必须破除各种迷信,当前尤其是要破除从老祖宗那里寻答案,从原教旨那里寻找出路的迷信;破除死抱住本派的原教旨教义,以为是天字第一号真理,强烈排他的迷信。
蓦然回首,“上帝”(神)正在你我他心里
人必须有精神依恃才能活得滋润,这便是信仰,信仰的对象,被称为神(上帝)。为了信仰,西方人找到上帝和他的代理人耶稣,中东人找到安拉和他的代理人穆罕默德,印度人找到释迦牟尼,中国人找到的是泛神论的各样神仙。
历史以来,教派林立,主义纷呈,学说骈俪,百家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它们之外和之上,有没有一种可以统领或整合它们的东西?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到底是谁,还是他们之间谁都不是,而仅仅是宇宙自然?他们,还有李耳、孔丘,再加上耶稣、穆罕默德等人在一起开会议事的时候,最高的精神遵循是什么,最后的精神归宿在哪里?有所争议的时候,谁听谁的?谁是敲下最后一槌的人?地球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神或“上帝”只有一个,还是多个?假如只有一个的话,谁信仰的“上帝”是正宗的?假如这些问题不撕捋明白,吵闹和扰攘就不会断绝,恐怖袭击也会不断上演,地球村里将永无宁日。
人是这样一种怪物:它必须要找到使自己精神安居的地方,才能活得润泽。这就是精神家园。信仰乃是精神家园之根。神本来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为什么抱着金碗讨饭吃?为什么原教旨主义阴魂不散?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最高和最后的根据:真正应该信仰的“上帝”究竟是什么?
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却了神,所以真心诚意地造神。迄今为止,人类几乎所有的“上帝”或“神”都是自己造出来的。所有神职人员也都是人,而不是神的化身,他们也会腐败堕落。西方宗教改革之初,教会中的丑闻不断的发生,公然贩卖赎罪券,并声称能以之赎回炼狱之刑。中国太平军起义,洪秀全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次子,但是“上帝”代理人的把戏总有露馅的时候。果不其然,很快就与杨秀清发生内讧火并。如今科学与技术已经发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地步,此类戏法很难再玩了。“上帝”究竟在哪里呢?“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毋劳远求。“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真正的神或“上帝”就在你我他心里,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即追真求正精神。
为了建立全球统一的经济市场,需要统一各国的度量衡(或者确定科学的换算方法);为了建立全世界统一的思想市场,需要统一的评判尺度,即价值坐标或价值维度。
追真求正精神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真”,一个是“正”。“真”即客观事实和规律一直在发展中,“正”即在遵循自然规则的前提下时时调整自己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理性的位置,从而做到和谐相处。天底下的所有真理正义都是从这个价值维度,或者说价值坐标出来,而且用它来衡量的。只要你是人,人类的原精神就适用于你,或者说,你就必须自觉接受人类原精神的自律。
——这就是我提倡的真正学对于真“上帝”的发现。
人类都共居于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把大家联在一起,只要大家都遵奉同一的人类原精神,所有的问题都不难解决。在这个同一的价值坐标之下,可以产生很多具体的普世价值,这本来就是题内应有之义,也不会产生互相冲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大道至简,说破天则淡如水。古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后来被人们弄复杂了。《周易》说,自然界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总是用简单和平易来显现它的智慧与功能。因为平易才容易被人了解,简略才容易使人遵从。只要把握好这个平易简要的原则,天地间的道理就可以通达了。(《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欲使中国人的精神不致分裂,欲使人类的精神不致分裂,必须找到一种统一的精神宗旨。实际上,它已经存在,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也就是人类的真“上帝”。当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最需要出场的恰恰是这个长期被冷落的真“上帝”。这不啻一场思想革命!
送人香料不如授人以麝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经典,包括主义、教义、教导等,都是告诉人们要这样,不要那样,即具体怎样做。这让人们觉得很便当,只要遵照执行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但是危机和危险也正在这里。因为任何具体的指点都是针对一种具体的情况,时过境迁,正确的指点也会变成错谬。我们更需要探知这些具体的教导背后的根据,即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最高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缺憾。由此也惯成人们的一种毛病,希望别人告诉他外财黄金埋在哪里,好让他一镢头挖出;而不是学习创造财富的知识和理路。却不明白,没有谁能告诉他,除非是“神”,而这样的“神”又是不存在的。必须破除一种迷信:没有哪一路神仙可以给你指路,能为你指路的真正神仙,毋宁只是用人类原精神武装了头脑的自己。不是“文革”时期高调呼喊的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那是纯粹的现代迷信。
检视人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创设宗教及相关的制度机构机制设置,用他律的形式实现自律,或者把自律架设在他律的神圣台阶之上,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由此可以实现维系一个族群精神的统一。此举有优点也有弊端。优点是简单省事,不必费脑筋;弊端是体现了人类的不自信,拱手把自己的精神交给虚无缥缈的“上帝”,“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无论“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还是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都是迷信与愚昧。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应该做自己这艘航船的舵手。而要如此,必须首先找到确定前进路标的坐标,毋宁说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神。现实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的普世价值固然令人欣喜,更重要的是掌握构成普世价值的维度或坐标,这样,才能不断地发现更多的普世价值。人类的精神文化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在各种宗教和各种主义之上,必定还有一个共主性质的精神,无论哪种具体的宗教或主义,只有符合这种精神才能立得住,否则就不行。同时,只有用这种精神整合各种宗教或主义,实现人类精神境界的一元多样,世界才会更精彩。不要凡事等着圣贤、伟人指点迷津,那样的人是没有的。遇事要问自己——问秉持了追真求正精神的自己。这样比“‘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或者“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肯定要复杂麻烦些,但是无限风光就在这里,无边风景也在这里。
中国的教育方式需要改变,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方式都需要反省与改变。以往的方式总是劝导人们要具体地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以为更要紧或者更根本的是告诉人们什么是衡量真理正义的坐标,从而让人们自己根据随时变化着的活的情况,决定怎样去做。为此,我提倡以追真求正精神为宗旨的真正学。
真正学学者要告诉人们的是:凡事要怎样做,不须问我,要问你自己。问自己内心的神灵即理性的自己,也就是说,自觉地按照追真求正精神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如此而已。
总之,送人以香料,不如授人以麝,有麝则香来。
怪圈从哪里打破
综上所述,我要说的中国革命和改革乃至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思想准备,是指确立追真求正精神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哪怕是曾被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根本站不住脚的东西。
照此来看,中国民众的思想准备好了么?反观中国历史,陈胜吴广起义时准备好了么,太平军起义时准备好了么,洋务运动时准备好了么,戊戌变法时准备好了么,辛亥革命时准备好了么,五四运动时准备好了么?直到今天,中国改革的思想准备好了么?
反省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一直很难突破。
一个怪圈是所谓治乱循环的怪圈。自从秦朝末年以来,中国历史一直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怪圈里盘桓:皇朝专制加剧——农民起义爆发——皇朝政权更迭——皇朝专制加剧——下一次农民起义爆发——皇朝政权再次更迭。起码到1949年,依然是这种规律的延续。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运行的思想尚未准备好。因为起码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环境差不多一脉相承,不仅药没有换,汤也没有换。辛亥革命名为革命,其实并没有革了旧文化的命,正如鲁迅在小说《风波》里所揭示的,赵七爷们无非是在“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复辟之后,马上把辫子放下来而已。作为普通民众的七斤嫂,还为七斤剪掉了辫子悔恨地跳脚呢。
此后引入的主义虽然吸引了很多志士仁人的眼球,以为这回可找到最终的真理了,甚至发出“砍头不要紧,主要主义真”的壮烈声音,但是,实践已经证明了其主义之不真。否则,中国怎么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改革?!直到今天,帝王情绪、以真龙天子的意识仍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以我之浅见,根子就在于孔子及其儒学。儒学的核心思想具有逆文明性质,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负面的。起码体现在:一是把中国哲学中阴阳平等平衡的观念阉割了,由“天尊地卑”演绎出“男尊女卑”,并据以确定社会秩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甚至弄到“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的地步。直到今天,民众中的官贵民贱的潜意识仍挥之不去,官本位的阴魂驱之不散,公务员吃香的局面仍在延续。这些现象与儒家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社会到了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各行各业的专业精英(也包括公务员中的精英)比公务员(官员)职业更占优势,人们找政府办事就像找一个修鞋匠修理破鞋那样自然,不是被迫地围着官员团团转的时候,才是回归正常秩序的时候。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政府,没有代表广大民众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社会就会乱套。因此,民众必须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管束者,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同时,政府也必须无时无处不在民众的监督之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双方以宪法为契约,各自履行自己负担的权利与义务。因为政府毕竟处在强势地位,所以,对它必须在机构设置上有到位的限权措施,否则,民众就会被奴役。儒家不可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的思想,它的局限性是无法掩盖的。
二是性善论。孔子一贯把三皇五帝和周公视为可以绝对信赖的圣贤,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在制度设计上为“真龙天子”、“大救星”预留了位置,把一切生杀大权拱手交付于他。这样做本来就是违背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则的,必然走向崩溃。造一部车子,在设计驱动装置的同时,必须设置制动装置,否则,很有可能翻车或掉沟。哪能在构建政府时,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一个所谓领袖人物?!而且还尊为最高指示,压倒一切。世界上,只有人类自身的原精神是最高指示,其他都必须遵循和服从。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没有随时自救的机制,如此一来,只能等到玩不转的时候再重新洗牌,一切推倒重来,而新政体和机制仍然是原样驴推磨那一套。于是,中国历史只好不断地在怪圈中循环。这一笔老账不清算,中国社会用无安宁之日。多少年来,不是批儒批过了头,而是很不够。
另一个怪圈是“人——文化——制度”三者互相咬合的共生关系,不知道从何处打开缺口。人创造了文化和制度,文化和制度反过来又制约了人;文化与制度之前也有互相影响与制约的关系。走不出这个怪圈本身就说明思想准备尚未做好。
链条从何处断裂,往往有多种途径,由政治强人做推手,显然是最有效的一着。蒋经国毅然决然地“解严”时,僚属并非都同意,是他做了劝解的。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时,很多基层官员哀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宿变回解放前”,也不理解。不丹国王在国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推行君主立宪制,开启了民主进程。曼德拉固然是伟大人物,在我眼里,德克勒克似乎更伟大。没有德克勒克,或者把德克勒克换成金正恩,曼德拉可能至今仍在监狱里坐着,甚至干脆从肉体上被消灭。邓小平搞改革,有重返政治舞台的回冲力在起作用。不丹国王之所以开明,是因为他曾在英国留学,感受了时代风潮。相形之下,蒋经国和德克勒克更值得赞扬,因为他们纯粹是向自身体制的弊端开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幸,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实现用正确的思想引领前进的方向,都能有政治领袖来执行或肩负这种思想。
现在我想追问的是,假如在“人——文化——制度”三者处在胶着状态,政治强人一时无法出现,文化和精神信仰迷失不扬,传统制度仍以惯性力继续向前滑行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想奉劝人们,请记住,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既不要返回原地,也不要转移到你认为值得学习的别人那里再重新出发。就从你目前站立的地方,瞄准“北斗星”作为定位标,以确定前进的方向好了。我说的“北斗星”就是追真求正原精神。
不是一味地反传统,只是需要用人类“最高法”即追真求正精神(而不是某一个教派的所谓原教旨律法)整合各种思想、主义、教义,以“真”和“正”作为坐标,在两者的经纬交汇点上求得自己需要的答案。即使别人用过的好东西,自己使用的时候,也还要加以检点,比如民主。2011年,埃及民众示威游行,迫使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推翻了专制统治。此后遵循民主程序建立了民主制度。新上台的总统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代理人,穆斯林兄弟会的计划是以选举的方式获得国家统治政权,以伊斯兰教法治国。于是,军队介入,罢黜了总统。如果军队不干预,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未来,很可能会演变为一个神权政治主导的国家。可见,民主手段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多数人决定有时候也不是正确的,军事政变也不全是反动。
在没有代表先进思想的政治领袖出现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制度好,固然也可以规范着人们学好,可以促使人们的思想优化。那么,在文化与制度互相咬合难以打开的时候,该从哪里下手?我以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倡导真正的信仰精神,从根本上改变和改造人的灵魂入手。比如大力倡导在民间开展“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弄明白什么是决定实践正误对错的标准,特别是当下此刻应该怎么办。当年为改革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由官家倡导,针对的是复古倒退的“两个凡是”;如今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发起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不妨首先由民间发起。当今社会“网络党”是一股十分强大的民意力量,很多社会难题可以在这里攻破。总之,只要人的思想正确了,文化氛围会跟着转变,也可以推动制度的变迁,从而推动社会向理性化的方向迈进。
任何新思想新学说都是人们心中应有,而眼中尚无的东西,需要有人首先鸣叫一声,提醒众人。我首倡真正学,正是为此。
2014年1月于蔚县静也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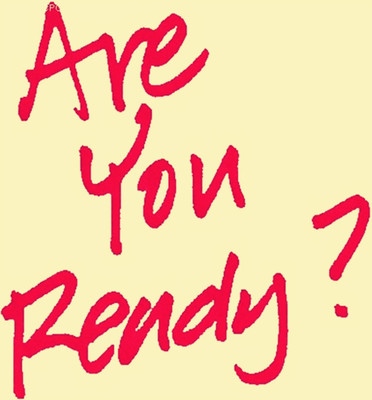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