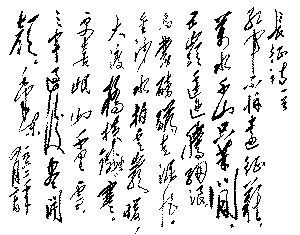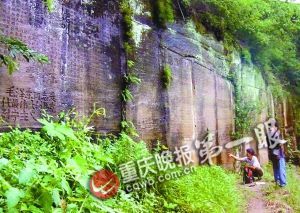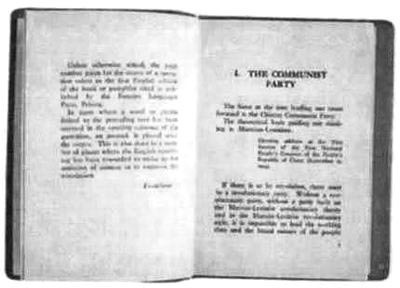闲来无事,老伴在院子角上辟了一块采菜地,种上几棵西红柿黄瓜白菜什么的。当初我极力反对,还和老伴吵了几句。说是又不是没吃没穿,吃饱了撑的慌?可老伴仍是坚持,说是不为吃不为穿,只是喜欢,没事转转路,看看绿色,心里就舒服。另外,找点事做,锻炼锻炼也是好的。原来没种菜时不是也时常踏青?现在看自己种的心里感觉就不一样!这最后一句打动了我,于是欣然答应,有时也参入其中。
其实我小时侯也种菜的。那时兴人民公社,地是公家的,大家的身份是公社社————员,出工就在公家的地里干活。可收过了队里分点粮食,却总不够吃,吃菜就更难了。本来,社员们在田间地头辟出丁点菜地,也能解决下无菜之炊。可那时经常刮妖风,搞不好就“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于是眨眼间好好的黄瓜瓠子南瓜秧子就被扯掉了。还说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载资本主义的苗”。可草不能吃怎么办?于是社员们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法,“敌进我退、敌退我‘栽’”。社员们心里明镜似的,一定会有“敌疲”的时候。等风声过后,菜园子又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来。后来上面扭不过社员们的持久战,终于承认社员有种菜的自由,各家各户分了点菜地,叫做“自留地”,名正言顺地种起菜来。
那时候种菜可不是容易的事呵,白天要出工,要干公家的活儿;工余时间才可以种菜。那时侯出工干活,收的粮食却不是自家的。除了向国家交公粮余粮,剩下的已多乎哉不多也,于是社员们大都消极怠工。种自留地则不一样,种的菜都是自己的,种得好就吃得好,不种就没得吃的。所以种自留地积极性忒高。但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加上那时吃不饱,肚子里没油水,如果干集体的事累了,就没法种自留地了。所以社员们出工大都偷懒,所谓“出工不出力”。于是就有了“出工象鸭子,手工象兔子,干自留地象猴子”的民谣。
“人上一百,各种各色”,当然有人勤快有人懒。勤快人种的菜好有得吃,“一分耕种一分收获”嘛。懒人没得就嫉妒,嫉妒之余就挖空心思想意外之财。于是就有顺手牵羊的,有小偷小摸的。趁人不注意摘一条黄瓜扯几棵白菜还是好的。更有甚者是贪得无厌的,把人家的菜摘光不说,连菜地也践踏得不成样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办?这就要看受害者的个性了,有的人当时骂几句就偃旗息鼓,自认倒霉算了;有的人则一连骂三天三夜不歇息,姑娘女子连同祖宗三代骂个遍,搅得一湾人日夜不得安宁。我母亲是个极勤劳的人,有时会连夜挑上百余担粪水不歇息。她种的菜向来为人称道,于是被偷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母亲又是个极良善之人,平时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施舍些给别人,如果有人经过,她总会说“有没有菜吃呀?我这儿有”。可有些人做事就是没道德,把菜偷光不说还把菜地给毁了,于是母亲也会生气。但是无论怎么生气,母亲却不骂人。在我的印象里,母亲除了骂我们兄弟“短命的”以外就没骂过别人。有一次,菜地被毁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母亲气得直哭,一边哭一边对我嘟囔着:“你骂呐骂呐!”可偏偏我也不会骂人,憋了半天也吐不出一个字儿。心想:您咋不骂呢?您教过我骂人吗?现在想来,这人也忒没道德了,又没人骂你没人抓你,咋不好好的摘菜呢?毁了多可惜?
斗转星移,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虽然早已是耄耋老人了,母亲可是勤劳善良依旧,仁义慈爱依旧。没事总爱在房前屋后种几株瓜豆什么的,有人路过,还会说“有没菜呀?我这儿还有”。现在母亲随弟弟住在乡下,有时来城里住一段,可总说不习惯。我想,难道还舍不的她的菜地她的菜?
我进城以后,已经多年不种菜了。没事转路,总爱走出老远去菜农的菜地里看看,有时想起母亲的菜地来,心里总爱拿母亲种的菜比量。心想,如果是母亲,这菜会长成啥样呢?
跟我母亲一样,我妻子年轻时也喜欢种菜,也乐意和别人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摘菜时遇见别人,也常说“有没菜呀?我这儿还有”。
现在种菜成了她的一大乐趣,她说不止看着绿色植物心里舒服,还有一种劳动的快乐和自豪。记得前些时央视讨论过幸福的话题。什么是幸福呢?我想,也许幸福就是人们喜欢干什么,没人管着、卡着、压着,叫做自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