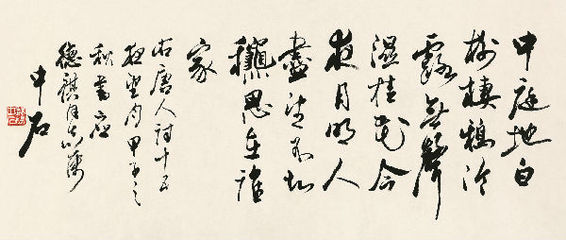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菜。
中学时学古诗词鉴赏,各种条条框框规矩格式常搞得我们狼狈不堪。书上将不同篇章一一划分——思乡、怀古、咏物言志等等,每一类型都有相应的赏析方法。以至于让我感到,诗词的写作是否也是有模板的,像京剧一样程式化?而对于鉴赏来说,最佳的方式应该是“意会而不言传”,当用文字表述出来时,不得不说这已然是一种误解。
在所有诗词类别中,思乡诗是我们接触的最早恐怕也是最多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早被载入幼儿必背古诗词,成为少儿的启蒙读物了。相比古人,现代人的经历在某种层面上趋于同一,历史远不如前那么波澜壮阔;相比长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论是生活阅历还是情感经历均单纯浅薄,还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相比其他远离家乡来到北京上学的同学,我又缺少了一份背井离乡的诗意。
其实在当今交通、通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一个人离家能有多远呢?“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回到家见到父老颜色改的慨叹也不会有了。然而,“月是故乡明”,那种离家越来越近,越来越激动的心情仍会存在,古今不变吧。这一点对于我这个一直长在家乡的人来说,不是思乡,而是一种熟悉和留恋。
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韵律简洁,意思也不难懂。开头叙事,然后抒情,最后一句表达志愿,格式中规中矩。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间那些迫切的询问。童孩、旧园、新树、垂柳、茅斋、梅花、沟渠、石台、院果、林花,意象繁多琐碎,意识流式的相继迸发。诗人见到同乡,思绪就如流水般漫延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家乡的故景旧物一一涌现眼前。诗人在异乡待久了,甚至有些“乐不思蜀”,年岁渐长竟也没有归意,对于家乡的印象还如当年,因此遇见来人,勾起了旧时印象,却也知道多年过去总会有所变化,于是便焦急地一一打听。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向知情人打听家乡近况更令人兴奋与焦虑的事了。兴奋如陶渊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那是久别重逢的喜悦;焦虑如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是百转千回的慨叹。这是一种怎样的矛盾心理?欲问还休——害怕听到变故又渴望知晓实情。宋之问不敢问来人,他马上就到家了可以自己看;王绩却仍远离故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乡当然要问个透彻、清楚、明白。而且他问得如此细致甚至琐碎,如“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这样的问题,可见诗人其实有多思念家乡。对于一个男人,思乡之情似乎有些难以与人言说,这种感情常常隐秘在心底,某一个时刻——可能是见到月圆,可能是听到乡音,也可能是偶然尝到一口熟悉的家常菜,都能勾起这股暖情。不等同乡一一说明,作者就兀自抛出了许多问题。“新树也应栽”中的“新”字对应着上句的“旧”,今夕对比,让人感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旧”这个字确实伤感,哪怕才活了二十年,也是有过去可以追溯和回忆的,怀旧和年岁无关,和心境有关。听到“旧”字,仿佛颜色顿时褪去,时间瞬时苍老。而“新”字又是那么刺眼和感慨。“应”字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假如旧园还在的话,这么多年了,也该有新树被种植,过去的那些老树有的已经死了吧。当我们说什么事应该怎样时,我们多半怀着美好的愿望,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一句满含诗人的联想和期待,似乎是否能够得到同乡的证实,也不那么重要了。“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当”、“总”诗人用两个肯定意义的词道出了自己对家乡景物的熟悉和怀恋。即使过去多年,想必沟渠的水流依然流淌,石台上必定布满了青苔。诗人不满足只了解到家乡总体的概况,院里哪个先结果,林中哪枝先开花,是不是还和过去一样?诗人实在是太迫切了,以至于一时语塞,竟想不到还要询问些什么,于是催促同乡一一道来不要有所迟疑。最后一句“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寄托了诗人的志向——当然是归隐田园。这向来是中国文人最终极的志愿。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后,王绩确实如他所愿,躬耕于田野。
季羡林写到“思想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怅惘,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确实,思乡之苦总能激发人们的自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 身份使人变得多愁善感;孤独的处境给人以冥思的时间。因此才更易于参透人与时空的短暂关联,才更加觉得家乡这个词有多美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