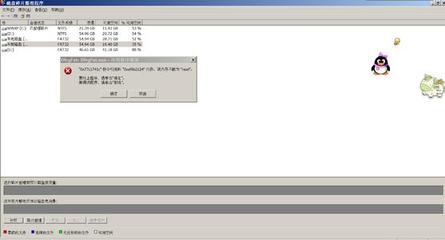荒友在一起聚会,竟然对我的身体大加赞赏,说下乡这么多年,没得过腰肌劳损和风湿病真是
不容易,你现在还能活蹦乱跳,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对自己的身体也挺自豪的,市里组织体
检,我除了血压略高,还真没太大的毛病。同样下乡,同样干活,我怎么就没有腰腿疼的毛病呢?
细细想来,这还应该感谢母亲。我下乡的行李是最多的,两床褥子,八斤棉花的厚被,外加一床狗
皮褥子。母亲给我准备行囊的时候,反复对我说,到了农村要好好照顾自己,棉衣要到“五一”才
能脱,不要为一时的美丽,酿成一生的不美丽,腿要是变了形,穿什么裤子都不好看。要知冷知
热,狗皮褥子是咱家的传家宝,你带上,无论天气多冷,有了它你不会得腰腿疼的病。
那床狗皮褥子长120公分,宽80公分,黄颜色。不是一整张皮子,有缝制的痕迹,两只狗耳
朵,正好对称在褥子的上方,看上去特别漂亮。狗皮柔软,干净。据母亲讲,姥爷家养了一条大黄
狗,像小老虎似的,威猛高大,皮毛光滑如同绸缎一般,人见人爱。一年的冬天,大黄狗被一家狗
肉馆下毒毒死了,他们想把大黄狗毒死偷走吃肉,没想到被姥爷发现了,投毒的人跑了,大黄狗躺
下了,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因为是寒冬,所以狗的皮毛特别好,姥爷找了个皮匠,把狗皮扒下来,
仔 细熟好皮子,钉在住宅外墙皮上放了一个冬天,最后缝制成一条褥子。

最初姥爷享受这条狗皮褥子,姥爷去世后,狗皮褥子落到了妈妈手里。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把狗皮褥子给父亲送去,狗皮褥子伴随父亲
过了十个月的隔离审查生活。父亲回家后对狗皮褥子也是大加赞扬。
我下乡后,炕上铺着毯子,上面是一个炕被,炕被上面是狗皮褥子,再上面又是一条褥子。白
天我把上面的褥子卷起来,盖在叠得方方正正的被上。底下的狗皮褥子就裸露在外面,荒友都喜欢
躺在上面,说是很舒服。
由于有了狗皮褥子,我一般不住在炕头,我喜欢住在炕稍。我不惧怕北大荒的风雪严寒,每个
晚上我都睡得热热乎乎的。劳动之余,我也喜欢坐在狗皮褥子上面,背靠着行李,倚在小木箱旁
边,写字或者读书。特别是窗外秋雨绵绵的时候,我把自己陶醉在书中,走向另一个王国,真的感
觉很充实。
1974年冬天,我上山伐木,带行李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带上狗皮褥子。大兴安岭冬天的那种
冷,是我一生中感受到的最冷的天气。我们住的帐篷,床上温暖如春,我们光着脊梁穿着短裤打扑
克;床下冰天雪地,脸盆里的毛巾冻得梆梆硬。夜里烧炉子的人一迷糊过去,炉火熄灭,屋子里就
冷的让人难以忍受。由于有了狗皮褥子,我的忍受能力,一般要比别人高得多,在大兴安岭山上的
那个冬天,我和狗皮褥子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1995年,我们搬入学校给的三居室,妻子清理家中物品,对我说,狗皮褥子被我扔掉了,好多
地方已经磨得没有毛了。我对妻子说,狗皮褥子为咱们家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