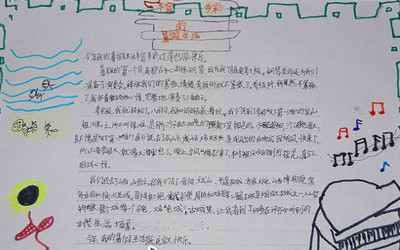难忘的同学情
(初一5班同学回忆陈子明同学二则)
回忆中学时期的陈子明同学
谢其相
四十九年前的 1965年9月1日,我们开始了在北京八中初中一年级的学习生活。那一年北京八中开始招收女生,面向社会招收了15名女生,都安排在我们初一五班,和30名男生共同组成了这个班集体。那时我们大多只有13周岁,是全市各小学学习优秀的佼佼者,也是懵懂少年向蓬勃青年过渡时期,聪明伶俐、天真活泼、求知欲强是大家共同的特点。陈子明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由小学考入中学,又赶上教学实验从这届新生开始,大家学习劲头都很足。八中优良的校风,浓厚的学习氛围,学校丰富的图书馆藏和多项课余活动,使我们这些初一新生感受颇深。
那时候的子明还没有表现出更突出的学习能力,只是在第一次数学考试后,才让同学刮目相看的。初一的数学并不很难,同学们又都是小学时的数学高手,拿惯了高分和满分,可这次期中考试成绩一下来都有些傻眼: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成绩是67分,自己都看着别扭,这是打小学习以来没有过的低分。左临右舍不少同学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数学李秉纯老师现场点评,告戒大家要重视数学学习的特点,要适应中学教学方式,也特别告诉大家:陈子明同学成绩是97分。自此,这个身材不高眼睛有些近视坐在第一排的男生,算是被同学们记住了。
转眼到了1966年6月,我们在顺义下乡劳动锻炼回到学校,“文革”的邪风刮起,造成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由此开始。对我们来说,正常的学习骤然停止,一生中最美好的学习刚开个头就被掐断,虽然许多同学在近十年之后又开始了文化课的学习,提出要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可“文革”灾难性的后果对这一代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救的。
在66年6月到68年底,学业中断,我们这些初一学生无所事事,随波逐流,看着高年级同学成立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校长和老师、无厘头的辩论会、成群结队到西单街上抓“流氓”私设公堂拷打,还有抄家和“大串联”;好一点的就“练块儿”--玩单双杠练肌肉。
这两年多的时间,是和子明接触最密切的一段时光:我们一同去串联,一同成立“战斗组织”,一同找地方下乡劳动,还一起玩单双杠“练块儿”,不一而足。
说起去外地串联,我和子明、王柳、孙大奇几个同学搞到了去沈阳的火车票,可出发的时候已是初冬,火车也不正点,我们在北京火车站露天广场夜里排队时到室内避寒,错过了开车时间,只好上了去天津的车。在天津住下以后就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我觉得能免费串联就多看看城市和景观,却发现子明对大字报看得很认真。那几天正好政府号召串联学生返校闹革命,我们几个对是否返校有不同看法,子明表示应该回到学校去。因为没有搞到其他火车票,就结束了短暂的串联回北京了。66年在冬季串联返京后就结束了。
67年初,学生们的串联热情意犹未尽,政府则号召徒步“长征”式的串联,我班里白羽和几个同学徒步串联到狼牙山,我和哥哥及一个邻居学生徒步“长征”串联45天,由北京向东走到秦皇岛北戴河,又折向天津塘沽走回北京,风餐露宿,练得一副好脚板。回到北京已经是春节后了,同学们又陆续回到教室,但学校仍是停课状态,大家只是上午到班里聊天神侃,中午就一哄而散了。记得这年春夏,子明提出要成立个红卫兵组织,搞些自己的活动。当时学校各种红卫兵组织已经不少,我们这些出身不够优越的则逍遥旁观,加之年龄尚小,也不知道成立组织或加入别的组织有什么意义。而那时的子明已经显示出一定的认识水平和和凝聚力,显得比我们成熟,他认为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独立开展活动。于是经他一鼓动就成立了我班男女十几个同学参加的“北京八中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简称“红联”。成立伊始按当时的流行的做法,在学校走廊张贴了一份“宣言”,阐明我们这个组织的“纲领”,具体内容是子明起草的,落款是“八中红联”。记得“宣言”贴出不久,一位高年级同学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份新张贴的大字报,还嘟囔了一句:这个“红联”是谁组织的?边说边看。我正好看到这个场景,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偷着乐呢”。
成立了组织,就开展活动,主要有:张贴大字报,阐明对运动的看法;组织大家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召开批斗会--批斗过当时的校领导;开展班内部的谈心活动等等。关于开展谈心活动,是作为“红联”领导者的子明主张和布置的。他认为“干革命”要联合团结全班同学一起参加,不分出身和派性,“红联”的成员要主动找其他同学谈心,争取他们“进步”。记得子明安排我去找张小平同学“谈心”。我那时实在不知道该谈什么和怎么去谈,就旁观了一次子明与别的同学“谈心”活动。谈心谈话过程中子明声调不高,态度诚恳,用手势配合着话语内容。这以后子明又催促了我一次,我学着他的样子硬着头皮找小平同学谈心交流,感觉效果还不错。张小平同学,你现在何方?还记得我回忆的这件事吗?
那时候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一般是骑车去。每辆车不会闲着都是一人带着一位,路上骑累了就换着骑。子明骑着一辆“倒轮闸”女车,没骑过的人一时掌握不好要领。记得我几次三番骑下来比较熟练了,就经常与子明搭伴轮流带着去各学校转。一次子明突发奇想,说让我试试闭着眼睛骑行,蹬一百下再睁眼,考验一下掌控车子的技术。我说那不行,不用蹬一百下就撞马路牙子翻车了!过了几天我问他闭目骑行试过了吗?他说有次骑车回真武庙家的路上试了一下,大约没蹬到一百下就碰到障碍物了。我俩哈哈大笑了一番,十四、五岁的我们总是这么开心的样子。
“文革”期间虽然不上课,但我们还是经常到教数学的黄庭松老师的宿舍去,听他给我们分析时局,帮我们答疑解惑。黄老师那时不到30岁,是江西人,习惯吃米饭,经常把食堂买的馒头烤糊了再吃,他说这样对肠胃好,我想也许他不习惯北方的面食吧。记得67年底或68年初,黄老师从家乡探亲回来,给我们分发喜糖,说是这次探亲在家乡结婚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只是顾着吃糖,听老师讲着家乡的见闻。子明问黄老师新娘子是哪儿的人,老师说是赣州附近公社的,结婚了才接到赣州城里的。子明说,黄老师人家农村户口的女孩嫁给你,就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啦,增加城市供应负担了。这好像是我头一次听说“商品粮”、“农村户口”什么的,更搞不清商品粮、户口、农村户口的关系。短短的对话,足见子明那时的知识面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已远在我们之上了。记得黄老师听子明这么一说,也是憨憨的笑了。
初一开学时,我加入的是学校航海队,学习划舢板、打旗语和射击,子明、白羽等同学参加的是体操队,还有一些同学参加乒乓球队。“文革”后这些校外活动都消失了,但年轻人的精力总是要通过体育活动宣泄出去,我们几位:白羽、子明、王乃仪、张贵禄等喜欢上了单杠双杠,每天总是做单杠引体向上、双杠的双臂支撑等运动。子明几位参加过体操队训练的,根据大家的水平,设计了一套单、双杠的“标准动作”,比如从双杠的一端开始做上杠动作,然后通过肩倒立和滚翻移动到双杠中间,在接着几个力量动作到双杠的另一端,以一个分腿绕杠跳下结束。完成这套动作还是需要一些力量和技巧的,记得子明和白羽先做示范,边做边商议确定动作的衔接,之后我们再依葫芦画瓢的去做。子明他们有体操队训练的底子,完成动作连贯自然,我们几位门外汉就只有勤学苦练的份了。那段时间单、双杠下撒满了我们的汗水,双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我们自身也力量足了身材壮实了。一开始子明单杠引体向上的记录是45个,双杠双臂撑上起也是45个,成为我们的标杆。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苦练,我和白羽等同学也达到了这个指标。子明爱看书,平时我们几个玩单双杠时他不怎么参加,我们练了一段时间感觉良好了,就笑话他说我们已超过他了,可往往是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他,一上器械还是动作熟练力量不减,不免羡煞我们。他自己则得意的说:膀宽腰细必定有力!他自己就是这体形。
除了体育体力上子明似乎有先天的优势,在阅读和记忆能力上也比较突出。一天我和他在学校传达室翻看报纸,他拿着一份新到的《参考消息》对我说,让我选任意一版面,他只要看三十秒,就可以背述内容。我同意测试一下,看着传达室墙上的表,半分钟后我念一个新闻标题,他就将新闻的主要内容复述一遍,版面十几个新闻都测试了,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的。
1967年,我们“红联”还组织了2次下乡劳动,一次是去北京东郊一个农场的葡萄园劳动,一次是到卢沟桥一个农场参加秋收。在卢沟桥农场劳动时正值葡萄成熟的季节,农场以每斤2分钱的价格销售葡萄,我们几个同学各自拿着脸盆去买葡萄,新鲜的葡萄使我们大饱口福,连正常的饭食也免了。那时我们7、8个男生挤在一间小平房里睡觉,夜里还有起来吃几口葡萄的,搅得别人也睡不踏实,闹出不少笑话,其中子明情急之中的一个“灌口”一时成为我们的笑谈。回忆那时场景,只有用历历在目最为恰当了。
1968年8月子明与那宗兴同学去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因为那年7月下旬我利用暑假学生乘车半票的政策去了宁波,没有见证他们离京的场景,只是后来看到一些照片。记得去宁波前,子明找到我,送我一本袖珍的“毛主席语录”,在空白页上书写着:送给亲密的战友其相同学。多年后有一次子明跟我说,因为没能和我一起去插队,他曾难过的掉过眼泪。人们都说青少年时的友谊是一生中最纯洁的感情,我特别相信这一点。
1969年2月,我和同班的白羽、潘小平、孙大奇去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插队,与子明时常有通信往来。每次回到北京,总是要见上好几次面,聊聊各自的见闻。有时他到我家里来一聊就是好几小时,以至于我兄弟姐妹都认识他了。我也经常到他真武庙的家里,记得子明姥姥对我颇有好感,除了我是子明同学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能听懂老人家说的江浙话---因为我家长也是江浙人,在家里都说江浙话---于是老人家显得特别高兴。
我们的中学时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折腾和倒退,也塑造了我们这一代特殊的性格特征。眼下的中国正努力向着正常国家的方向上演变,我们这些50后们除了少数还在台上做着最后的表演,绝大多数已被抛向边缘,但我们年轻过快乐过所以无怨无悔。
和子明的交往一直到他2014年10月21日的仙逝而戛然而止。近50年的友谊不是文字可以承载的,谨以此短文纪念子明同学。
2014年11月2日
同学情-----怀念陈子明
徐先凤
1965年9月,我考入北京八中,八中原是男校,从我们这届才开始招女生,初一共6个班,前3个班是试验二小来的,初一四班是育才来的,后两个班的90名是从社会各个学校考进来的,只有15名女生,编在初一五班,子明和我们同班。
开学后,我们正常的学习快1年时间,虽然男女生之间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子明在班里,还是有点名气,他很聪明,尤其数学很拔尖,初一时,已自学高中的课程,我们都很敬佩他。
快期末考试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学习,不上课,更不用考试了,我们这些14-15岁的少年,高兴的很,班级打乱了,各干各的,整天东跑西颠的闹革命,搞串联,因观念不同,分成很多派,直到67年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实现了联合,组建了联合的校革委会,我们才回到班级。
成立了班委会,参加军训,下乡劳动等活动,后来又复课闹革命(也没正经上课),我和子明都是班委会成员,才有了接触,子明是头,领导我们,他很聪明,很自信,善于思考,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很严,谁作的不好,或作错了,他就进行批评,且一点情面不讲,说话尖锐,是非分明,我挨过他好几次批评,有一次,开斗私会,他批评我说;“你是校革委会委员,应起带头作用,彻底批判派性,不能含糊其词,斗私不撤底,就是有私心。”
他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事事带头,68年7,8月份,66,67届开始分配,有内蒙插队的,他不但自己带头报名,还召开班委会,要求我们都积极报名,我当时也是个积极分子,但家里老人说啥也不同意,告诉我说:”家里不同意你报名,因你们68届还没开始分配,你不能自己先走,啥时分配了你再走。“为此,我和家里吵了一架,但也没有拗过家人,子明,许红,那宗兴等68年8月都去了内蒙。
自己没去成,很失落,整天跟家里生气,闹起别扭,68年10月份,哥哥支援三线建设,把我带到了贵州,从此与同学失去了联系,直到2004年末,才联系上同学,第1次参加了同学聚会,36年后第1次见到了子明和同学们,子明虽经历了很多,但还是那么淡定。以后也就是参加同学聚会,见过几次面,也没时间多聊。
接到子明去世的消息,很难过,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同学感情难忘,子明走好!!!
2014年11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