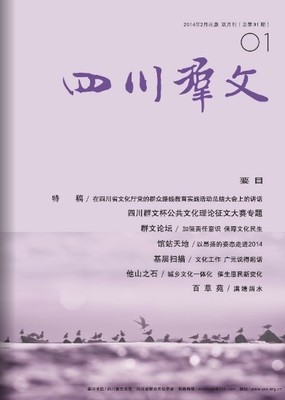杨慎戎泸行旅诗的意境与特色
“杨状元替主充军”的故事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百年流传,家喻户晓。历史上的这位杨状元,名慎,字用修,号升庵(公元1488~1559年),四川省新都县人,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第一,累官至翰林修撰。世宗即位,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公元1521年),以“议礼”得罪,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71岁客死异乡。半生谪戍生涯中,去来行役,“往复滇云十四回”,多次奔波在川滇黔古道上。
明代,从升庵原籍成都平原通去云南的道路,主要有三条:
建昌道(南路)——从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入,渡金沙江以达云南姚州(今姚安县)境。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走的就是这条路。
石门道(北路)——从成都经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浮岷江经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转云南河(横江河)而去云南老鸦滩(今盐津县),越豆沙关(即所谓石门)以向昆明。
川黔道(西路)——从叙州沿长江东下,经南溪、江安诸县,绕道泸州过纳溪县以去永宁(今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穿过黔边直去云南的曲靖。明王朝开国之初,傅友德平定云南的四川方面军胡海洋、郭英部队,就从永宁集结启行。杨升庵行役往来,走的主要是这条道路。
在这三条川滇古道之中,就有两条分别从叙(古称戎州)泸两州经过,泸戎境内的山山水水,印下了杨状元的历历行踪,留下了他众多的品题吟咏。
嘉州一日到叙州
杨升庵生长京师。母丧还乡守制,是从陕西经剑阁陆路入川。他第一次路过叙州,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从成都浮流东下。那次,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赋诗的雅兴。后来发戍充军,是从北京南下,过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取道黔边以入,没有路过叙州。直到嘉靖五年四月,惊闻其父廷和病笃,“匹马间道,十九日至家”,从石门道回川,才又从叙州匆匆过路。不过,在这以后,随着往来行役,路过的次数也就多了。《明史·杨慎传》说:有明一代,“著述之富,记诵之博,推慎为第一。”这位沧落天涯的杨状元,所到之处,无不赋诗纪行,书怀述志,偏是他留在叙州的诗极少,今仅可见七绝《舟次叙州》一首:
嘉州一日到叙州,好似乘风列子游。
乌鹊南飞月明里,喜声先报蕊珠楼。
蕊珠楼,在泸州,是杨升庵晚年流寓所在。其在泸州(古名江阳)所赋《江阳病中秋怀》组诗之七云:“卜居草草结檽轩,江郭西偏寂不喧。蕊珠楼接芸香阁,”即此,不是指成都那个有名的蕊珠楼。嘉州,沿岷江下叙州,水程253公里,冬日水枯,舟程3日;夏秋涨潦,水疾如箭,当日即达。杨升庵此番泛舟,正是在他赋为上述《病中秋怀》不久之后的一个夏秋之交。如此江流放船揽胜,李白曾经写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脍炙人口。他说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至于舟中人自己有什么感受,他是怎样过来的?杨状元在这首诗里说:是飞过来的,像《庄子》里所多次提到过的那个仙人列御寇一样,乘风飞过来的。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何等得意,何等自如,何等的潇洒!
短短7字,道尽夏日岷江河上放流疾驶所见的无边风景。神韵天然,与李白的名篇互相发明,引得众多游人望风怀想,跃跃欲试。
江上之风,扑面飒然而来,杨状元披襟以当之。夹岸青山、鸡犬、桑麻。田间农夫,牧童吹笛,好一派神仙画图!然而杨状元自己却不是神仙中人,他原本钦命谪戍一犯军,有家归不得。当他的航船抵达叙州城下的时候,已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孟德当年“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名句,自然涌上他的心头,这“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乌鹊,能飞到哪里去呢?禁不住行旅思乡之念,油然而起,览景思怀,倍觉伤心惨目。如此万端幽怨,偏又不能直接道来,只好学个稼轩居士“却道清凉好个秋”,写下了末句“喜声先报蕊珠楼”,说是让南飞的乌鹊,告诉泸州的故人和亲友:“明天,我又回来了。”如此这般,细细读来,应有何等凄楚!
杨升庵的诗,在明代独立于“前后七子”之外,别树一帜。他的有些诗,初看似乎很浅,明白如话,但仔细推敲,便发现也颇有一点像江西诗派那样,“句句有来历,事事有出处”。笔力千钧,而又熨贴自然,不显生硬。不唯没有雕琢的痕迹,反显得别有新意。这首《舟次叙州》,应即如此之作。
可怜烟草江安树
这类游子怀乡之词,在升庵集中,比比皆是。有些,更是一气呵成,直抒胸臆,其《董坝》诗云:
扁舟孤棹宿枫林,猎火渔灯逼岁阴。
千里思家回白首,青山江上叠愁心。
董坝,旧属江安县,今在泸州市江阳区境。明时,设水驿,为过客泊舟舣船之所。细心的读者,当然可以看出这首小诗与唐人张继那首有名的《枫桥夜泊》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样的离人愁思,一样是江枫渔火。此情此景,何等相似。然而,二者却又不相同,张继的愁思,是一缕淡淡的清愁,伴随着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在夜空中缓缓地飘荡;杨状元的愁思,不是离愁,不是个人私怨,而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赶出朝堂,眼看嘉靖皇帝诸般虐政,却再也无由直言进谏以匡时政,“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然自己老朽且病,雁去帆来,已成白首,犹自思念无穷。频频回首,不尽依依。愁思万丈,有如那江上重重叠叠的青山,叠叠重重,竟理不出个条理和头绪。如此融化前人词语以为己句,却又毫不牵强,天衣无缝,给人以新的美学享受,应当说是杨升庵诗的一大优点,而人或以“杨慎爱作伪”目之,未免有些学究气。
升庵集中,还有另一些叙州境内戎旅之诗,从更深层次,反映了作者的的内心思想境界,如《过南溪怀二刘参之承之兄弟》云:
京国交游四十春,刘家兄弟最情亲。
风流云散三生梦,水逝山藏一聚尘。
沙步维舟催解缆,邻村闻笛倍沾襟。
可怜烟草江安树,愁见当年送别津。
参之,名景宇;承之,名景宗。旧在京师,并与升庵为挚友。后来功名失意,退隐还川。升庵集中,多有投赠他们之作。风流云散、京师繁华,裁诗置酒高会的时代已非;水逝山藏,则是二刘兄弟竟已作古。思念故人,能不感慨!当年,就在这南溪城下江步头,升庵过境远行,承之赶来话别,升庵赋为《南溪舟中与刘承之话旧》,已自不胜感慨。其辞云:“晴月初江对佳人,明烛深林慰苦辛。征棹来帆成白首,鸣俦伴侣啸青春。万重山塞浮云外,咫尺沧浪积水深。歌罢语阑还别去,朔风寒雪倍伤神。”升庵行戍,承之赶来船舟慰问,晴江月下,共话京师“青梅竹马”少年时,感慨世事蹉跎,已成白首,自己而今还要征棹来帆,跋涉奔波,远去重山一万重。才相逢,又离别,更添得白雪皑皑,北风凛冽,愁云惨淡万里凝,够伤心了。哪知道今度重游,竟连承之也再不可得见!依旧是江步维舟,依旧是岸头村笛,景犹是也,己犹是也,而人事已非,连承之也已物化,再也不能剪烛篷舱,共诉愁肠。《诗》云:“鹦其鸣矣,求其友声。”而杨升庵故友安在?再无从觅旧时相伴登高长啸侣,但闻得荒江野渡吹笛梅花三弄声,就连当年最最不堪的舟中诀别,也再不可求。晓风残月,依旧是夜冷清江;兰舟催发,所要去的,偏又是江安城下当年与二刘兄弟最后分别之处。此情此景,更谁能领会得其中滋味!
李清照怕对“梨花”,怕的是镜中人比黄花瘦。杨状元此番愁见江安,怕的是触景伤情,唤起了对于亡友的无限哀思与自己的万种忧愁。难为他削籍充军已经几十年了,然而嘉靖皇帝兀自饶他不过,“每问近来慎作何状。”世事如此,我们的诗人,能复何望哉!屈原有怨,还可以发而为《骚》,杨状元却是连“怨”也不敢。他不能不惧及祸会从天外飞来。满腔幽怨沉郁于胸,所以,他写下的也就只能是“愁见当年送别津。”这里的愁,不仅是愁无由重见故人,愁自己不得金鸡放赦,重登朝堂,再为国家效力,同时也是愁烟瘴边三千里远戍。就在这次去滇途中,他吟成了字字当作哭声读的七律《自江安登陆历诸险道》:
镜吹晴泥阻且修,琉璃岸倾铁马愁。
藤萝箐出深井底,连天云在孤城头。
眼前行路嗟如此,身外功名复何求。
欲求缩地壶公术,厌作乘风列子游。
从江安舍舟陆行,经梅岭(今江安县红桥镇)、大坝(今兴文县共乐乡一带),以达永宁而合于去云南的川黔古道。铁马,川黔边民行走泥泞山路时使用一种特制防滑具,钢铁锻打而成,底面状如锯齿。绑在鞋子下面,行走雨雪山路,防坠防滑。卷地北风,崖间冰凌百丈。滑得像玻璃板一样的边关古道,漫漫而修远兮,永远也望不到尽头。北宋年间,林广征剿乌蛮乞弟,沿着这条道路经淯井(今四川省长宁县)、乐共城(今兴文县境内),向鸦飞不到山进军,“天大寒,士卒皆冻堕指”;唐代“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派鲜于仲通将兵八万进攻云南,在泸水(今云南省泸南县)全军覆没,走的也是这条路。几百年过去了,杨升庵而今再来,一样是北风其凉,风雪载途,密箐深林,孤城废堡。这一切一切,令人不由不想起当年“万人冢上哭悠悠”的寡妇孤儿,不由不想到自己“永远充军”那“椒花落时瘴烟起”的云南荒服之外。望前途,一片漆黑,一派渺茫。复念自己24岁状元及第,金榜题名;“议大礼”为首撼门哭谏,更加名满天下。哪知道一朝得罪,这一切件件激起嘉靖皇帝的嫉恨之心,嘉靖十六年,立太子大赦天下,也特别传旨不赦免自己,真正是如东坡贬谪天涯时所言:“平生文字为吾累”,不得不学他“此去声名不厌低”了。在这山穷水尽之际,我们的诗人,已经再也没有学为“乘风列子游”的雅兴,只希望能够有费长房的缩地之术,早日走完这永远也走不完的滇黔行役戎旅之路,在清净无为之中,寻找自己的归宿。杨升庵晚年的思想,与老庄日益接近,在这首诗中,也明显地流露出来。他对于重登朝堂,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对于以嘉靖皇帝为代表的大明王朝,已经彻底绝望了!
鱼凫关外雪山关
庄子“齐物”,同生死,等贵贱。作为这种思想的反映,《庄子》里的仙人是快乐而无忧无虑的。然而我们的杨状元,却自半点也快乐不起来,“厌逐乘风列子游”,正是他日暮途穷,与老、庄日趋接近而又始终未能从老、庄那里找到自己归宿的思想境界。这种理想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在他的另一首《雪关绝粒谕从者》诗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仆痡马病漫兴嗟,戎旅华封本一家。
我骨已仙元不馁,何须食柏与餐霞。
雪山关在叙永县南60公里,海拔1840公尺,是泸州通去滇云的必经之路,咽喉险阻。所谓“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之地。冬日北风怒号,冰雪封山,人马经过,每有失坠之虞。杨状元行役至此,粮糗断绝,困阻在驿店里,仆痡马病,难以继续前行,实在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太史公云:“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恒,未尝不呼父母也。”然而杨状元偏自不呼,不唯不呼,他还说是自己“骨已仙”,连食柏餐霞也不需要,无所谓,满不在乎。他说,旅途行役,辛苦往来也好,还是安居高堂华屋之下也好,从本质上讲,其实都是同一的,“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也”。老庄哲学思想,在这首短短的七言绝句里,得到了至为完美的表述与充分展现。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杨状元,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真的能够这么坦然,这样出尘潇洒么?嘉靖三十七年冬天,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根据云南巡抚王昺的命令,在4名指挥使的率领下,寅夜来到泸州杨慎家门,不由分说,把这位年届七十,两目昏眊,四肢不仁的老人重新逮捕起来,锒铛锁赴滇云万里。杨状元“登舻一望一魂销”,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但永远不能遭逢金鸡放赦,再登朝堂,而且是连四川也回不来了。“宠饯江阳殊霭霭”,极目所见的是,“梅心柳眼皆春意,僰舞夷歌亦舜韶。”故乡的各族同胞,是如此亲切,故乡的山川风物,是如此关人,然而杨状元明白,嘉靖皇帝永远不会饶恕自己,衰老且病的他,是永远也回不来了!在他行将进入黔山之际,永宁诸贤再次为他送行,祖帐城南鱼凫关外。当年,杨状元第一次从这里路过时,永宁诸贤送至鱼凫关。当时的杨状元即席挥毫,题下“凫关捧日”四个大字,同时写就“华夷统镇连千里;黔蜀分疆第一关”楹联,付人一并镌刻关门之上。虽然才人去国少不了几分惆怅,却也还未识得这永远充军烟瘴边的愁滋味,赋下新诗,说是“生还如有日,相伴老渔蓑。”哪知道三十年过去,自己兀自不得回来。无为也好,齐物也好,理想的哲学,毕竟代替不了生活中严酷的现实,杨状元再也压仰不住的满腔怒火,终于全部爆发了出来,他字字投枪、声声泣血地写下了《永宁诸贤送至鱼凫关》:
鱼凫今日是阳关,九度长征九度还。
何补干城与心腹,枉教霜雪老容颜。
扑面朔风,断非是渭城朝雨;永远充军,更非复奉使行人。阳关外头,王右丞劝行人更尽一杯酒,为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鱼凫关外,杨状元生离死别,谁复忍、谁复忍劝他更尽一杯酒呢?远瞻前路,度不完的密箐深林,翻不完的丛山峻岭。“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雨雪正纷纷。”风萧萧兮路漫漫,从此生为隔世之人,死作异域之鬼。伤心惨目,有如是耶!如此伤心惨目,孰能无怨哉?杨慎《鱼凫关》之诗,盖自怨生也。屈原《离骚》之怨,是婉转反侧,“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对于虽然昏聩到十二万分的楚怀王,犹自怀有最后的一线希望。而我们的这位明代第一才人,连最后的一线希望,也随着紧紧套在自己手脚上的械锁锒铛之声而彻底幻灭了。此时此刻,他还能够有什么呢?所能有的,也就只能是亘古无边的悲愤和哀怨。《小雅》怨谤而不乱。杨升庵的哀怨,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范畴,可是他批判的锋芒,已经远远不仅是对准那些“作我干城”的纠纠武夫与“为王前驱”的心腹爪牙,而且是指向暴虐不仁的嘉靖皇帝,指向以这位暴虐昏君为代表的大明封建王朝,这比起屈原的《离骚》来,自然别又另是一番红素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