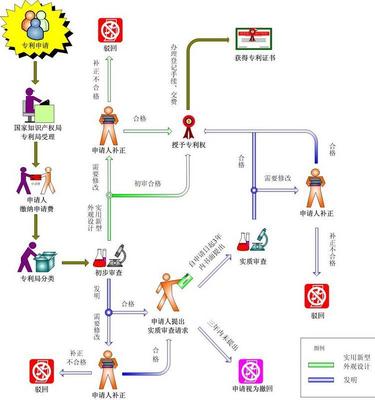摘要:专名是有意义的。专名的意义不是对象,也不是一个或一组限定摹状词,而是专名的界定性。专名的界定性意义,由实指的内容或蜕变了的限定摹状词所承载。专名意义跨界同一之所以可能,就在于由限定摹状词到专名的蜕变关系或认识关系。(本文发表于华夏出版社2013年出版《批评与回应----陈嘉映哲学三十年》一书)
关键词:专名;意义;界定性;对象;摹状词;跨界同一性
专名的意义是意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专名,就是自然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比如“嬴政”、“泰山”、“《资本论》”、“五四运动”、“孙悟空”等。专名的意义是什么?关于专名的意义主要有两种理论,简单地讲,一种是摹状词理论,即认为专名的意义是一个或一组限定摹状词;一种是直接指称理论,就是认为专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正如所见,这两种意义理论都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专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专名的界定性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单独地来讨论专名的意义问题?因为它与其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相比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一般来讲,其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即具有描述性,而专名却似乎可以完全没有这种描述性,比如“孔乙己”、“拿破仑”;或者脱离这种描述性,比如瓦房店已经荡然无存的地方可以继续称“瓦房店”,已经没有河流经过的小镇可以继续称“达特河口”。(本文设定,所讨论的专名都是熟知的;待知的专名暂不讨论。)这时,专名的意义是什么?首先,专名有没有意义?穆勒认为,专名“没有内涵,它指称被它指称的个体,但不表示或蕴涵属于该个体的任何属性”。[1]42确实,“拿破仑”三个字不管从字源还是字面上看,都没有直接表示出拿破仑的任何属性描述性意义,不过,我们能就此说专名“拿破仑”没有任何内涵或意义吗?不能。之所以存在专名无意义的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看到某些专名所具有的单纯的界定性意义,没有能看到表达式的属性描述性意义与界定性意义的区别。比如一个远方的父亲需要给一个具体情况他一无所知的孩子命名,因而不便将其描述性地命名为“小花”或“黑蛋”等,但命名活动的进行是不会有任何困难的:他(她)不能叫“美丽”,因为这是妻子的名字;不能叫“发财”,因为这是自己父亲的名字;也不能叫“阿三”,因为这是邻居孩子的名字;……就是说,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使名字具有有效界定性,原则上叫什么都行,否则叫什么都不行,都无法成为专名。(关于“两人同名”的问题,笔者同意克里普克的处理,[2]78兹不另述。)这样,即使不直接表示或蕴涵任何属性描述性意义,只要表示或蕴涵在一个需要的范围内的有效界定性,那么,比如专名“拿破仑”应该就是有意义的。
专名的意义就是界定,专名只是一个界定表达式。我们当然可以使专名同时具有直接的描述性意义,比如那位父亲可以将孩子命名为“家宝”。应该看到,使专名同时具有描述性意义,只不过是对专名的界定性施以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罢了。当界定时,这种界定有可能表现为某种属性描述,比如“葫芦岛”、“飞来峰”,但这种描述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界定,我们特别要注意把起界定作用的描述与起描述作用的描述区别开来,比如,“飞来峰真像飞来峰”。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飞来峰哪一天因为什么根本不再像飞来之峰,我们仍然可以说:
“那就是飞来峰”。尽管有些怪异,但原则上没有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这时候给它改一个名字(这在生活中显然是多此一举;比如,没有人会要求马大哈“周到”、穷光蛋“钱多”改名换姓),这不要紧,因为,起界定作用的“飞来峰”与这个新名字的意义无所谓区别,犹如“赤县”与“神州”作为专名其界定性意义无所谓区别。
2、专名意义的直接指称理论与摹状词理论。
知道专名有界定性意义是不够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专名的意义(指界定性意义;下同)是什么?即专名界定性的表现方式是什么?专名通过什么来界定?比如专名“太阳”,其表现方式能否就是引号里所排列的那两个字?即能否仅仅是一个标签、符号?显然不能,我们知道,用这两个字作专名,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这肯定不行。能否直接就是外在对象?撇开其已被揭示的困难不谈,[3]、[4]沿着原思路进行下去,这里最起码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如果表现方式就是对象,那么是对象的什么?必须看到,仅仅说意义的表现方式就是对象是不够的,因为,没鼻子没眼睛的“对象”除了表明对象性,并没有表明什么,太阳和月亮同样都是“对象”,就专名的意义而言,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怎么能使对象太阳和月亮分别得到界定获得专名?“专”从何处来,“名”因什么起?这样,所谓“对象”就不过是相互无所谓区别的“个体”的通名罢了。
那么,意义的表现方式就是关于对象的一个或一组限定摹状词?克里普克指出,专名与一个(组)摹状词并不是同义的。[2]99应该说克里普克是有道理的,论证也是充分的。因为专名的摹状性意义,即使在现实世界,也可以是流变的,进进出出的,没有哪一个或一组摹状性意义,就专名而言是不可变化、必不可少的。刚被命名的婴儿“亚里士多德”,几乎不具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任一摹状性意义,但我们不会说那是另一个“亚里士多德”;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剽窃者,或一个假冒为亚里山大大帝老师的骗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把他称作“亚里士多德”。鉴于此,有人认为,专名的意义应该是足够多但又不确定的摹状词簇。换句话说,专名的意义可以是关于同一专名的相异的这一或另一摹状词簇。此即所谓“不定簇理论”。[5]303不难理解,如果这一理论行得通,那么就实现了摹状词簇对专名的完全覆盖,专名意义属性描述理论中最伤脑筋的问题应该说就解决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很有趣:一方面,这一理论明显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无论怎样的摹状词(簇),都仅仅是对专名比如“哥德尔”的反思认识即限定摹状。说他“是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者”也好,抑或“不是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者(是剽窃者)”也罢,这对于“哥德尔”本身根本就不造成任何问题。既然如此,正如塞尔所言,我们就“不必争论究竟是哪些特征确定着对象的身份”。[5]303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无法自洽。因为,如果关于同一专名的相异的两个摹状词簇不相容,那么专名的意义就会自相矛盾,这在理论上让人无法接受;这个问题下面还将谈到。那么专名的意义就只能是弗雷格所说的“有关某指称的完整知识”?[6]3什么是“完整”或“整体”?不难理解,那只不过是一个盛满了摹状词的“无底洞”罢了。显然,在我们力图搞清专名意义的时候,类似的“无底洞”是无法给我们任何教益的,相反只会使我们望而却步。
3、“这”与专名。
如果专名意义的表现方式不能是简单的符号、对象,以及对象的一个或一组摹状词,那么能否是一堆、一束、或一片无所谓属性描述且又具体的“感觉材料”?是实指或亲知的“这”(或“那”;下同)?[7]242[8]100、350-370应该说这一理解是有启发性的,是符合直觉的。为了帮助理解,可以指出,比如一个熟人的名字的意义,往往就是那张熟悉的、呈现着或浮现着的,即当下的、即时的、本真态的、无所谓属性描述但又有效界定着的脸,即“这”。为简便起见,下面请允许我将“当下、即时、本真态”等集中表述为正在。刚才提到的“无所谓”,简单地讲就是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即无从谈起。(正在、无所谓两个概念及相关问题,笔者在拙作《悖论的根源》一文中已有充分讨论,这里无法详述。[8])要注意的是,正在的“这”无所谓是什么“心像”或“物像”;它仅仅是“这”。因为,所谓“心像”或“物像”,是对“这”的反思,而当“这”正在时,反思都是无所谓的;相反亦然。同理,本文谈到正在的专名时,它是一个语词还是一个事物,也是不作反思区分的。[9]因此,作为语词的专名如何确定其指称的问题,具体地说,克里普克-普特南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理论”,本文暂不讨论。“这”甚至可以是限定着的走路的姿态乃至话音等。请注意,一定不要去摹状,否则就有可能不再是“这”了。这讲的是直接专名或逻辑专名,间接专名或普通专名也是这样。比如问:“拿破仑是谁?”答:“就是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皇帝”,或“1815年惨败于滑铁卢的法军统帅”等。读者可能要问,这岂不又回到摹状词上来了吗?不,应该看到,就问者而言,或通过专名的传递、确立过程来看,这里的摹状词不是直接地构成专名的意义,也不是简单地、同义地缩略为专名。这时发生的是一个认识到另一个认识的转变。这时的摹状词是在专名比如“拿破仑”认识――生成过程中蜕变着的摹状词,摹状词的原本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或者说已经无所谓了,这个蜕变了的摹状词的意义已不再同于摹状词的意义,犹如上述无所谓属性描述的“行姿”、“笑声”、“个性”一样已经是“这”的意思了。可以指出,刚才提到的“名称如何确定指称”的问题,从笔者的角度看,实际上也就是名称如何获得意义即完成界定的问题;讲的是“命名”如何可能的问题。实质上,每一次从摹状词到专名的过程(相当于上述传递链条中的一环),都是一次“命名”过程,即专名比如“拿破仑”的认识-生成过程。
我们可以联系实际想一想,当我们仅仅想起或说到“拿破仑”(或任一熟知的间接专名)时,不论情形如何,是否会有一由摹状词蜕变而来笼统且又具体(不会与其它专名混淆)的、与直接专名类似的、正在的“这”?任何一个熟知的专名能否没有“这”?另外,摹状词一旦完成为“这”,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摹状词这时都无所谓区别了,就是说,赖以或借以完成界定的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是一个还是一簇摹状词,区别都是无所谓的了。(刚才所谈到的“不定簇理论”,撇开其理由不谈,其结论可以说正好满足了这一点。)比如通常:“不错,你讲的那个人(‘1815年惨败于滑铁卢的法军统帅’),就是我讲的那个人(‘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皇帝’)”,这里的这个“那”,就是正在且相互无所谓摹状区别的专名的表现方式。可见,“这”也是一个描述,只不过是一个无所谓属性描述的描述即界定性描述罢了。专名意义的表现方式就是这个“这”吗?不,专名意义的表现方式当然不能只是本能的反映,不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不能是发愣,专名的意义不能仅仅就是这个“这”,而是表现或实现为专名的“这”,是作为比如“拿破仑”而存在的那个“这”,是正在的“拿破仑”本身;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
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专名理论陷入了两难之间,即:说专名意义是属性描述(表现为专名意义描述理论)行不通,说专名意义不是属性描述(表现为直接指称理论)也行不通。根源在于,双方都没有看到,在这里,既不能说专名的意义具有属性描述意义,也不能说专名意义不具有属性描述意义,因为,当专名正在时,其属性描述意义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时描述本身是无所谓的;相反亦然。专名正在时它是唯一的,属性描述是无所谓的,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专名意义无所谓,这样,“这”作为一种界定性描述就呼之欲出了。“这”是专名意义的表现方式,没有“这”,专名意义就将失去承载,理解上就会出现混乱。它是直觉启示的结果,也是理论追寻的结果。
说到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要注意,第一,“这”仅仅是“这”,不能是句子的成分,比如不能是“这是白的”中的“这”,因为我们只是在讨论相对独立的或正在的专名的意义,而不是讨论在上下文中的无所谓正在性的专名,这一定不能混淆。第二,通过“这”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专名也是一个认识过程的结果,作为一个认识结果可以单独具有界定性意义。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描述性意义,但作为一种(非属性)认识结果,专名与其它语言表达式并无实质区别。[10]107所以说,间接专名(意义)的认识或者说在主体间的传递,不能就是摹状词的传递,但也不能是离开摹状词的仅仅名号的传递。第三,本文不考虑专名意义的来源问题,即不考虑专名具体的认识-生成过程;目前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把认识(生成)过程中或起点上的东西比如对象或限定摹状词当作专名的“源”或“原”。
以上表明,作为专名意义的表现方式的“这”,可以由直接的感受构成(比如“太阳”),也可以由间接获得的摹状词构成(比如“拿破仑”),甚至可以由想象蜕变而来(比如“孔乙己”),但不论如何,只要能有“这”就行,专名就是有意义的。当“这”时,逻辑专名、普通专名、空名的区别是无所谓的。实际上它们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骑青牛的“老聃”、西游记里的“玄奘”,是不是空名就很难一刀切下去。这里丝毫没有要否认比如专名“孔乙己”与专名“《孔乙己》”在现实性等方面存在差别的意思,而是因为专名正在时,外在反思比如它与其它专名在现实性上的差别等都无所谓了。罗素所谓实指或亲知,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作为“正在”理解,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4、专名的跨界同一性。
说专名正在时确定摹状都凝结为“这”,摹状之间的区别也无所谓了,读者可能就要问,这时,就专名或“这”而言,摹状词的进进出出是否就停下来了呢?或者说“这”就不再有变化了呢?不难看出,一旦谈到“变化”等,已经是在反思“这”了,已经是变化中的“这”了。并且一旦反思,变化、差别中的“这”又重新沦为属性描述了。反思地看,当然一切皆变或不变(即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或稳定性),不过,当专名正在时,变与不变都是无所谓的。关键在于,就专名或“这”而言,摹状词的进进出出与摹状词一样,总是对专名或“这”的反思,它不能直接(或正在地)进入专名正在的意义,因为它不可能直接进入专名正在的意义,否则是悖论性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有悖论和逻辑矛盾。[12]
读者可能尚有疑虑:正在的“这”所赖以形成的确定摹状如果具有流动性,它怎么会不影响到正在的“这”呢?下面我们再改用举例来说明。日常生活中,我(不管是谁)总在变化中,但“我”肯定不会变,无论如何,“我”不会因为上述变化而不再是“我”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思想、身体、环境的任何变化没有使“我”变得不再是“我”而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我”是正在的或仅仅(唯一地)是“我”,其它(变化中的我,或我的变化)这时都是无所谓的(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要问,当我仅仅想到“我”时,我这时的比如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我”有什么相干?变化中的我无所谓是正在的“我”,而仅仅是属性描述或反思中的我。“我”与我是不能混淆的,犹如界定描述与属性描述不能混淆一样。正如洛克所言:“橡树至幼苗、至成树、至砍伐仍是同一的橡树”。[13]34应该说这是不难辨别的。
这么讲来,一旦界定专名的意义就是固定的?当然,界定肯定是固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专名“玄奘”不能一会儿说的是玄奘,一会儿说的不是玄奘。不过,界定并不就是固定;“同一”是对使用中(各种情况下)的专名的一种反思,表明使用中的专名有同一性或固定性。就熟知的专名而言,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搞清的问题是,在各种情况(摹状)中的玄奘,作为“同一个玄奘”(这是不成问题的),同一(固定)的根据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与专名的意义问题息息相关。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各种情况中把真(假)玄奘识别出来?显然,在现实世界中“验明正身”的工作只能由各门具体科学来完成;另外应该看到,要求对可能世界,初步地讲就是对能想象的世界中的玄奘通过比如DNA检测做“验明正身”的工作,以保证专名使用的同一性,这并没有使同一性更可信,而是更可疑了。正如陈嘉映先生所指出的:“求援于物质起源或物质结构来解说语词所指的同一性完全不得要领”。[5]317那么同一性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专名赖以形成的使各种限定性描述无所谓化的特性。专名同一地是各种摹状词消融和蜕变的结果,并且,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专名的使用具有融通(合)性。就是说,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专名究竟由哪一个(簇)摹状词蜕变而来,作为专名时这已经无从辨认、融为一体了。所谓“跨界”就是无所谓“界”;否则是悖论性错误。
“事物在何种程度有所变化却仍然是同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变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是它自己?”[5]316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事物的什么东西不变与变,导致这个事物的保持与丧失?”这应该是一个关于个体事物(本身规定或区别于其它个体事物)的本质特征问题。事物的本质,(下面就要讲到)可以且应该是事物之间相对而言的限定性描述,这与某一专名跨界同一性问题有共性(皆为“专有”)但显然也有区别(一为描述,一为界定);比如,克里普克的论证就归谬地表明,几乎任一限定性描述都不可能是专名跨界同一的内容(但却可能有效地构成某一事物的本质规定)。鉴于此,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及其所造成的混乱。[5]316-319
5、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
这里有必要集中对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作一简要讨论。可以说,克里普克的专名意义理论是典型的直接指称理论。其理论背景是模态逻辑-跨界个体同一性-本质主义。[14]296-314已经讲过,他对专名意义属性描述理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过头了;他由此割断了专名与摹状词的必不可少的联系,因而同样是错误的。比如,我们往往由“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而记住了“哥德尔”;克里普克假设哥德尔是一个剽窃者,并且“哥德尔的欺骗行为被揭露出来了,那么哥德尔就不会再被称作‘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了,但仍然会被称作‘哥德尔’。因此,摹状词并不是名称的缩写”。(原文如此)[2]89显然,这一点对“哥德尔”的任何属性描述应该都是适用的。这确实证明了专名的意义不可能直接就是某一个(组)摹状词的意义,但这是否同时说明专名“哥德尔”可以脱离所有的属性描述而存在呢?他曾认为:“实际上,名字的指称物很少或几乎从来不是由摹状词决定的。我这句话不只表示塞尔所说的:‘确定那个指称物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摹状词,而是一组、一族属性’。我说的是,这种意义的属性根本没有被使用”。[15]387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他的观点有所松动,[2]97-99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可能世界,其中可以有与现实的哥德尔“一点也不像”[2]115、122-123的“哥德尔”,但我们能不能假设这个“哥德尔”不满足任何属性描述、包括假设的属性描述?把话反过来讲,可能世界中能否有一个与现实的哥德尔“一模一样”[2]115、122-123的人却可以不是“哥德尔”(是“施密特”),并且这一假设不需要使用任何与现实的哥德尔相异的属性描述?答案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具有任何属性描述(不满足任一摹状词)的“哥德尔”或“施密特”,是不可捉摸、无从谈起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假设“哥德尔”并不是“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正如克里普克所言,哥德尔还是被称作“哥德尔”。但这并没有说明专名“哥德尔”可以不具有任何属性描述,因为,摹状词的“出”与“进”一样,都是关于“哥德尔”的,实际上都是在摹状。不难理解,说“哥德尔”“是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表明专名没有脱离摹状性;说“哥德尔”“不是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者”(“是剽窃者”),也同样表明“哥德尔”没有脱离摹状性。关键是不要把摹状词的“出”看作是彻底地脱离专名。如果假设的“哥德尔”离不开假设的摹状词,这样问题便又回到起点上:专名与摹状词的关系究竟如何?
实际上克里普克所谓的起源性、结构性的“本质特征”,必须是也只能是一个(簇)限定摹状词,一个相对的认识结果。就此而言,专名与通名、个别本质与普遍本质无所谓区别。比如作为“克里普克”本质的起源性的“受精卵”,同样应该同时有对其基因和结构的限定性摹状,否则难以构成“克里普克”的本质。而这些摹状,应该是相对的,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后验的”,或者说是可改变、可改进的。然而,就克里普克而言,为避免本质特性对于专名也有“进进出出”问题,本质特性就必须有别于普通的限定摹状词,所以它们同时又必须是必然的。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但显然也有问题,克里普克清楚地知道问题所在,所以他干脆自己替读者“提出如下不同的意见:‘你已经承认热可能被证明不是分子运动,黄金可能被证明不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那么当你说这样的不测事件的发生是不可能的时候,你的意思可能是什么呢?”[2]141他举例辩解:“关于黄金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复合物这样一条不严格和不精确的陈述,粗略说来应当由下述陈述代替,即存在着一种具有最初被认为是黄金所具有的各种特性的复合物这一点在逻辑上是可能的”。[2]143按字面理解,就是说,黄金有可能被证明并不是黄金,所以黄金有可能被证明不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这就要问了,我们究竟是在说“黄金”还是“假黄金”有可能被证明不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克里普克曾这样认为:“黄金显然具有原子序数79。黄金具有原子序数79这一点是黄金的一种必然特性还是偶然特性呢?我们当然可能发现我们是错误的。作为这样一些观点基础的关于质子的全部理论,关于原子序数的全部理论以及关于分子结构和原子结构的全部理论,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确不是自远古以来就认识这一点的。因此在那种意义上,黄金就可能被证明不具有原子序数79”。[2]125、126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说黄金可能被证明不是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这样的不测事件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呢?这一点,克里普克诉诸所谓“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什么是克里普克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呢?普特南曾简要指出;“用来说明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东西却平凡的很:化学和有关说话者的指称意向的事实”。通俗地讲,就是用对比如现实世界中的水的本质特性的可能会有的认为(“H2O”或“XYZ”等),去想象可能世界里的水的本质特性,不符合现实认为的“水”即被除名。[16]52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能是怎样的呢?首先,它与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摹状词理论有所不同,不过它总不能仅仅是一种永远都飘在天上的抽象吧,这样,只要这种形而上的东西脚一落地,问题便又回来了。前面已经讲过,作为“水”的本质特性,不论怎样,事实上都难以作为可能世界中“水”的同一性的根据,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对“水”的认识,不会在某一点上完全停下来,对“水”的任何本质特征的认识,都不可能置这种认识本身的发展变化于不顾,更不能就此认为,同一杯水,当我们如此这般(“H2O”或“XYZ”)地了解它的本质特性时它是“水”,否则就不是“水”;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这里必须要看到,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强烈地表明了一种需要。所谓“本质”,根本目的就是要抓住专名的固定性,或跨界同一性,而这是专名断不可缺少的。克里普克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长话短说,问题就在于他对专名的界定性不了解,对专名与摹状词之间的认识关系不了解,对专名同一性的根据的特殊性不了解,最后通过“本质特征”使“同一性的根据”实际上又回到他所坚决反对的摹状词上去了。
参考文献:
[1]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蒉益民.空名问题的几种解答[J].世界哲学,2005(6):78-83.
[4]蒉益民.从弗雷格之谜及信念之谜看心灵内容与语义内容的关系[J].世界哲学,2006(6):82-87.
[5]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弗雷格.论涵义和指称[M] ∥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8:3.
[7]罗素.逻辑与知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罗素.人类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9]丁和平.悖论的根源[J]合肥学院学报,2007(4):25-29.
[10]张尚水.关于专名[M]∥逻辑学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1]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丁和平.悖论与“自指”[J]安徽大学学报,2007(2):43-47.
[13]洛克.人类理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朱新民.现代西方哲学逻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15]克里普克.同一性与必然性[M]∥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88.[16]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