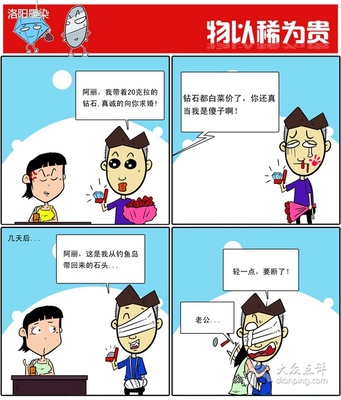不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国有一句格言,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的「时」,意思就是你对当下所遭遇的问题和处境的判断,你要「识」的不是是非与原则,也不是价值和观念,而是此时此刻的利害。你识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顺时势而為,你就是聪明人,就可以出落成為成功人士,俊杰也。否则,你就可能变成一个倒楣蛋,你就是笨人,说得好听点叫迂腐。
我不知道如此深入人心的智慧格言到底应该怎样翻译成外文,我也不知道是否西方世界也拥有同样的格言,西方人之间是否同样[]存在於如此广泛认同的智慧。我只知道,在中国,识时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碰到问题你先别管它对和错,要紧的是此时此刻你怎样做才算得上是最上算最合理的。对和错是会随着「时」而变的,你不能太拿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较劲。所以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很少几个不承认什么「普世价值」的地方。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经历过各种的政治风雨,就是一场持久的「识时务」训练,那些脑子里逻辑性强一点原则性多一点的人,不善识时务,不是在反右中倒楣了,就是在文革中倒楣了,再不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倒楣了。
上个世纪中国流行政治学习,每个单位的人,不管文化程度有多高,经常要一起读报或读档,读完以后还必须发言,轮流说几句,不说不行,就像一种仪式。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有书面的政治小结,上面关照一定要写进去某些关键内容,比如「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发展是硬道理」等等。后来我琢磨出来了,这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识时务练习」。如此训练下来,如果再要搞一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文革,严打,禁止练功,等等,不管有多荒唐,还是能搞起来,还是不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人太聪明,经过这些年,大家更聪明,识时务者太多了。但是拒绝识时务,不甘为俊杰的人,还是有的。十多年前,《黄祸》、《天葬》的作者王力雄,读到作协第五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后,对其做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分析,随后公开声明退出作协。
王力雄这样说:「80年代,前辈陈荒煤和好友史铁生介绍我进入作协。虽然我从未指望通过作协得到什麼收益,但那时至少把成為作协会员视為一种荣誉。一般而言我的性格并不激烈,也不苛求,我能理解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个人与机构的无奈。然而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人格、良知与气节」理应是传统文人或现今作家们最讲究最追求的东西,但却恰恰不在「时务」的范围里。中国的作家协会,和中国的其他所有全国性政治和非政治组织,诸如工会、
妇联、青联、工商联、以及眾多某某家协会一样,是按照党的指令成立和存在的一种「垂直结构」,先有一个头,掌控一切,然后从这个头上生长出下面一级一级的身体,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般的群眾性专业团体,是同行们先有了自愿结社的「平面结构」,再按照民主程序產生上面的头。
中国这种垂直的协会,完全拷贝自前苏联。前苏联的体制,政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定义,叫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就是「全部」,「一切」的意思,意味着国家要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一切。
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这个定义的政权,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而现在,世界上获此殊荣的最大政权,显然非中国莫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起动,因為体制一方太强大,它控制了一切,而民间的力量太弱了。而中国民间力量之所以这麼弱,和我们的作家们教授们知识分子们都太识时务有关。
一个社会要进步,应视不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惜,我们社会不甘识时务的人太少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