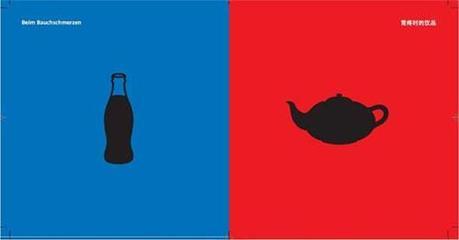来源: 张宏斌的日志
一、焦国标博士的学术经历
焦国标(1963~),河南省杞县人。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新闻学专业博士课程。1996年获新闻学专业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中国文化报》编辑、记者。2001年12月,焦国标博士进入北京大学,开始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焦国标博士在担任北京大学教师之前,就已经是国内颇具影响的杂文家了。199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焦国标的杂文集《奉献与义务的边际》;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专着《文化名流的报刊生涯》;200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新闻之外的敏感》;200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独立的悲伤》。
在到北大报到的当日,焦国标写了一篇杂文《写着杂文进北大》,他在文章中说:
我的人生经历并不顺畅,仅升学一项即可谓“蹭蹬”无比:初中升高中我考了两年,高中升大学我考了三年才走人,读博士也是考了两次。硕士毕业分配和博士毕业分配,也皆不如意。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一句格言:“每一个挫折都是成全”。今后我将努力实现“每一个非挫折更是成全”。曹操说:“设若天下不有孤,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胡适说:“设若没有蔡先生,正不知我胡某人会沦落到哪个三流小报做编辑”。焦国标说:“设若没有北大新闻传播学院龚文庠院长,也许我再写两辈子杂文也写不进北大”。这时候的焦国标是乐观的。他可能并未料到,他的北大执教生涯只有短暂的三年,这既是由于他具有“五四那一代人的气质”,也是因为北大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高压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五四”那一年代的气度与风骨。这些都事关重大,并非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龚文庠教授所能左右。
二、震惊世界的《讨伐中宣部》
2003年底,焦国标参加了一次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会上很多人在发言中抱怨中宣部和地方党委宣传部统辖得太死。焦国标在会上做了五分钟的发言,题为《拯救中宣部》。此后,焦国标以此次发言内容为主线,费时四个月,撰写长文《讨伐中宣部》,终于在2004年3月完稿。文章完稿后,发给一些朋友传阅。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将此文登陆在独立作家王力雄的《递进式民主》网站上。文章上网后,迅速传遍中文世界,香港《开放》杂志和《亚洲周刊》都做了节选转载。《讨伐中宣部》被迅速翻译成22种语言,《纽约时报》等知名国际媒体都做了报道。
《讨伐中宣部》一文长达一万四千字,全文分五个部分。文章开宗明义,“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以简洁明快的口吻说明了“讨伐”中宣部的理由。以下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全文的文风泼辣生动,说理明白晓畅,极富感染力。焦国标博士在文章中将“中宣部”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诊断,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考察,格局纵横开合,气魄刚毅宏大。文中说:“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焦国标博士的《讨伐中宣部》中,有许多段落是直接涉及学术自由的,语气之直接、定位之精准均令人叹服。这表明他对于“中宣部”这一机构对于人文学术的限制与伤害已经有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并对其专横跋扈的种种行径达到了忍无可忍、不吐不快的程度。他在文中说:
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
焦国标博士立志做一个“好的知识者”,做中国的弥尔顿,并有意识地将此文与《论出版自由》媲美。文章的历史意义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方能断定,但是“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在中国知识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之下,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在《讨伐中宣部》一文所引起的反响当中,有两位老者的评价与回应最值得注意。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先生在评论此文时说:他大体很厉害,很刻薄,但是基本道理我是赞成的,我是根本赞成,这个中宣部要不得,不应该要有个中宣部。……你共产党就管党员。你把你的党员管好,其它的事情按宪法办,共产党必须服从宪法。[47]另一位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先生在评论此文时说:本来,这中宣部啊,它从来就居高临下,从来只会“我领导你,我指挥你,我教育你”。我觉得我们党开口闭口就教育老百姓——(老百姓要说)为什么你要教育我啊?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啊?……我觉得它这个题目啊,先不讲它的内容,这个题目就很好。……我觉得中宣部应该有这种气魄,你骂我,我可以跟你反驳,公开地辩论嘛,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我跟你争鸣不可以吗?问题是它中宣部一跟你争鸣,就跟你平等了,所以它就不争鸣了。……启蒙嘛,是需要启蒙,他们也需要启蒙,但是哪怕他自己认识到这是错了,他还是不改,因为我有权,我有权就不管是非。[48]
这些热烈的回应本身也表明,“不应该要有个中宣部”不仅仅是焦国标个人的观点,而且代表了中国的“好知识者”们对及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共同关切。

三、从《讨伐中宣部》到《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
《讨伐中宣部》公开发表之后,焦国标开始昼夜接到骚扰电话,在他给学生上课时就曾连续接到18个骚扰电话。焦国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歌篮采访时说:“我就把它写到黑板上,学生现场就打,打了以后有一个人说他是刷小广告的,他说不是他。就现场嘛,怎么不是他呢!我的想法是他受委托的,或受人雇用的。”[49]此外,焦国标博士的新着、杂文集《良知龙骧》,以及另一部学术专着《回望农民》,本来已经进入出版程序,但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国内外议论和关注后,出版社忽然决定停止出版他的这两部书。学校方面也给焦国标博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据焦国标自己的回忆: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我带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在那儿军训的时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我觉得挺紧张,非常紧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惧的自由,那时如果不恐惧我会感到挺幸福,那个时候确实挺恐惧的。第二天学校花了六百块钱打计程车把我从那接了回来。回来后,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找我开会,院里的头都在。会议的两点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时评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还是不见外国记者。当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让我再写一篇保证书——形诸文字,将来如果我言而无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证明。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但是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不写时政——我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这个东西二十七日我交给他们。到九月二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九月十七日的时候另一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2001年九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就三年缘分,感到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什么事做,或者做个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就这样把灰暗期转过去了。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之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听说是副部长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香港《成报》就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给我打电话印证,我说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事,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50]
焦国标博士被停课,其硕士生导师资格也被强行中止,其原因只是他的一篇文章。而且作为教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副教授,《讨伐中宣部》一文所讨论的问题本来就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更令人感到无法接受的是,整个处理过程没有任何遵循程序的表示,随意性的处理透出大学本身作为权力附庸的霸气与专横。这件事充分表达了中国大学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可言,也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不过焦国标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讨伐中宣部》一文中已经提到: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焦国标已经想到了写这篇文章可能遭致的最坏的后果:失去生命。此后,学校方面又提出,将焦国标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调到北大古代文献研究中心,或者建议他自动辞职,否则不排除将其强行除名。这些莫名其妙的要求都被焦国标拒绝了。在压力之下,焦国标多次上书北大校长,均无回音。
2005年3月,焦国标发表了著名的《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信中说:一则我并不想离开北大,二则我也不认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学教授,古今教授的风度并无同一的款式,所以我决定不再作辞职之想。如果学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后快,我等着被“踢出”北大,并等待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一天。当年我在洛阳师专工作时,校长不让考博士,我说:“校长,你看着,我不会在咱洛阳师专退休。”现在我要说: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学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发誓做北大的终身教授,做北大的百代教授,我誓将以北大最名誉的教授光荣退休。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岁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评价。前贤在此,我不着急。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无论世人怎么看不惯他,他的存在都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人格基因意义。因而,凡是人格上有常人达不到之处的人,杀人犯除外,从屈原到文天祥,从为袁崇焕守墓几百年的家族到前不久背着同伴尸体爬火车从福建回湖南的那位先生,都受到我的尊重。基因单一的物种要灭亡,基因单一的人种也要灭亡。为什么几个日本人就能占领一个中国的县城许多年?为什么几千日军就能杀害南京的三十万人?为什么一千多远征英军就能拿下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的人格基因太单一了。基于此,我认为,北大几千教授只有我一个人“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只说明我的行为具有人格基因意义,而不是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理由。……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有其标志性事件,那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里程碑。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拐点。实际上此后这二十来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收拾知识分子的路数并没有大变,无非是修理动物的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我要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不同于邓小平那一个,那一个是施与,我这一个是争取,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对宪法负责,我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负责,不需要对任何别的负责,就像前面路德说的,已经认识到上帝的意思,就无须再问别人。我想好了,如果我们北大对我不再客气,一定要将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国谋生,也不去欧洲、澳洲,也不去韩国、日本,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大学。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脉,二是那里是中国人,三是那里是开放言禁的地方。在大陆全力打压台湾、诋毁台湾民主政治的时候,我将以微不足道的我,去为民主自由的台湾捧个人场。当今仍然森严的大陆意识形态已经给我办了许多难看,我也要给它办难看。如果我被北大“踢出来”,我还准备向全球各大学的校长们呼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类。闵书记是斯坦福的博士,我将特别向斯坦福的校长求救。我这不是给我们北大摸黑找麻烦,而是为北大解围减压。怎么讲?北大不能只把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压力当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应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当成一个不可怠慢的对象!北大上面不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还有国际社会,还有国际上的大学邻居和大学校长“同僚”们。我将游说那些大学校长们,推行自由、民主、人权不只是伟大的美国政府的使命,文明国家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东方国家大学里发生的那些摧残学朮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你们不能袖手旁观!全球大学要建立联合会,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推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朮自由。当然,我还会在全校四千教授和两万学生中间为我自己发起签名活动。此外,我还可能到中纪委和全国政协去上访。总之我将不顾自己的大学教师身份,用一些“下三烂”的臭招,去改变延续几十年对待知识分子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的落后、僵化、刻薄、残酷的手段。……当初我来北京大学,三位先生都是首肯的人;如果有一位说不,我就不可能进来。常说“疾风知劲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