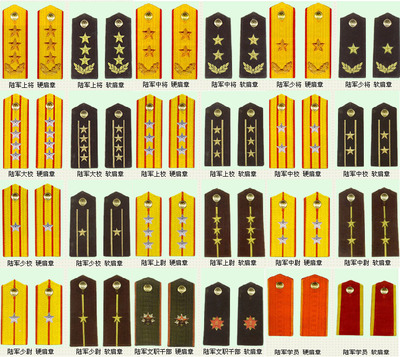尾浪
一 溃败
谁的胸膛里有一头猛兽,谁早晚得引颈嚎叫。
谁的心里有一个毒疮,他总有一天会俯下身来,为自己放血。
我站在一个和命运毫无瓜葛的十字路口,手里只剩下一截缰绳。因为昨夜的恶梦,我的头发变成了灰烬。
这里不是舞台,因为天空严峻。但浓雾仍由一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往我脚下吹送。
一只狗夹着尾巴蹭将过来,此刻它敢于和我眼里的浓霜作个比较。
狗尾草还在摇曳,节气还在拖延,高大健壮的姑娘还在斫伐青柴,她们的脸上既没有热爱,
也没有怜悯。汽车还在来来往往地放屁,它们把美丽的大街,变成了一条肮脏的绷带。
忙碌的人们忙碌着,闲适的人们闲适着。
星球保持着它亘古的转速和它没有人情味的尺度,但是
一根刺扎进我的肝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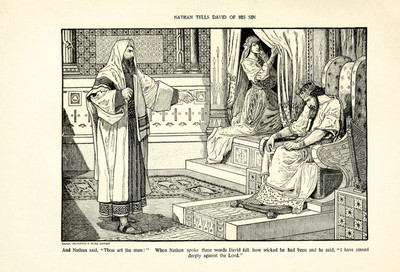
这是灵魂崩溃的时刻。
今夜,月亮将睡在一张不安的松毛之床上。今夜月亮的心里有一块炸药形的红斑病。因为月亮的转辗反侧,世界会在明天早晨听到雷鸣。
更无风声,露珠像一支浩大的军队在边界驻扎。它们拆掉炉灶,支起帐幔,支起明晃晃的罗网。会有一朵潮湿的花,从性格的枝头自我放逐。
更无凄艳的蝉鸣。月光以更稳定的形态挽留青草之上的夏末,让炎热之梦在石案上更长久地
思考自己的过错。
点起来,点起来,为亡灵通风报信的烟火。点起来,点起来,那芬芳松枝和呛人的蒿草。
家家门前都有拱起脊背的苦楝树根。
为了尊重传说,我们被迫从火堆上跳过去,反反复复,如同施了魔法。我们的脚带起串串火星。
谁是信口胡言却不幸猜出了谜语的人?谁的眼睛瞎了?谁从此离不开草药?谁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腥味里忘记了姓名、出身和种族?谁活着就是做梦,做梦就是发烧?谁攻击了整个世界,反过来又成了世界的牺牲品?
最深沉的往事也敌不过此刻的寒冷。
我说:“那些最纯粹的事物并未能给我引导,一个词语浪费了今生永世。”
我又说:“不要阻挡浓雾在我的窗上驻扎,但请把更灿烂的阳光保留到明天,会有更洁净的婴儿,会有更称职的助产士。”
而为了给大地的温暖提供保证,我命令血液在夜空迟钝地走。和闪电相比,我的血液有更粗野的歌喉和更丑陋的酵素。
一滴殷红打在纱布上,阴影在扩大,令人头晕的阴影在为黎明划定边界。
我知道我从未被打败,但也从未赢得一场人生的战斗。因为我一再成为自己的敌人。
二 流放
如果一个人发誓要去最荒凉的地方,他应该从哪里动身?如果他发誓要医好怀乡病,他应该嚼一块什么草药?
他应该驯服一头什么样的牲口?他应该用哪个朝代的旗帜做成营帐?
或者,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表情,和没有表情的风景觐面?
很少的时候,人会和他的内心和解。
那时,月亮的大提琴哼着无声的歌,仿佛一个腆着大肚皮、正在进行胎教的少妇。
那时,大海会在玻璃器皿的内部激越开花,而她的胸腹间却坚守静默。
更多的日子,一个人自身就是战场,就是猎犬与它悚栗的狐兔,就是箭形的光线和它的活靶。更多的日子,我们的内心尸横遍野,一把雪亮的刀搂着厌倦和悲伤。
的确有这种情形,灵魂离开粗鄙的肉体,独自在空中漫游,他看到那个已被掏空的躯壳一无所知,却继续愚弄自己,亵渎粮食。
继续为污泥般的欲望所在左右,像一条饥饿的黑鱼,只顾填饱下腹和放空精囊。
他看到那躯壳像一艘被遗弃的旧船,风干在船坞上,被拆开龙骨,被打入铁钉,又被日光从容消化;
他看到那躯壳在太阳底下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像一只苍老的鹰隼,只能在四个被打乱次序的季节里盲目盘旋。
他摇摇头,差点笑出声来。
世界的血像骤雨汇成河流,在天空的拐弯处摔成匹练。
有毒的云雾笼罩在原野,沉甸甸地压在祖先的坟上。没有风,没有蜜,没有钻石和黄玉,没有狂泻的雨水。
还是向神灵求助吧,诗人啊,跪在汉字垒成的祭台上是无用的,掩盖内心的伤口是耻辱。还是向神灵祈求吧:想象应该更宽阔,给抽空的心灵灌注烈酒。远方的波浪应该越卷越近,逼视我们沾满尘土的双脚。天空应该更高,更洁净,太阳应该更锋利,群山应该叠叠升高,拉起灵魂的床单。
的确有这种情形,肉体模仿灵魂的姿式在大地飘然行走,它也渴望翅膀,渴望凌空高蹈,渴望与来去的大风结缘。
肉体依靠它的脚,依靠物质的红柳拐棍,
从城市到城市,从喧闹到喧闹,从贫瘠之所到贫瘠之所。
肉体用它有限度的物质之眼,远眺群山的庄严与寂静,远眺神明的云朵,远眺诸神在大草原上的篝火狂欢。它只能浑身涂满泥浆,站在久久没有风来的槐树底下,承受着庞大无垠的天空。
是啊,那个蹲在路边喘息的人,有他奇特的梦。
三 盲歌者
千年之前,我也曾是个盲歌者,在希腊咸涩的海水里,咏叹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瞬间就是千年,那同一道波浪把你的背影打湿,同一道波浪把你心头的咸盐卷起,把你膝盖上的伤口泡得发白。
同一道波浪席卷着所有的圣哲,倒提着他们的双脚,把他们高贵的头颅泡在叫嚣的黑水里。
像一株对星象一无所知的海藻,我被同一道波浪拍向城市,拍向楼群,鲨鱼在铝合金门窗里进出,珊瑚虫在文明的塔尖构筑它们的繁衍梦。
在地铁口行乞的盲歌者,你也是一条鱼,你也是被时光流放到此的大师与圣人!盲歌者,你的眼睛比天堂更黑,你的心比挖煤的风钻更暗,你疾挥的手指在琴弦上追逐一颗蓝色的太阳。
习惯了死亡,习惯了假笑、敷衍以及前面加“老”或后面加“长”的无聊称谓,习惯了疲倦的苟合。激动,成为我们打到世界桌面上的一张主牌,人们把哭泣制作成通行证,把财富铸作路标。
而都市的金枪鱼被汛期和月亮的光芒所驱赶,正欲进入大地的内心。初冬的风像一把扬谷子的木铲,把越来越多的尘土扬到人的脸上,鳞光闪闪,盔甲闪闪。鱼的眼睛里反射着人类一样狡诈的光芒。
而盲歌者,你的光芒隐居内心,你的歌声像三月田野上的野油菜!
……昨夜的风让我染上疾病。人们啊,你的怜悯像火一样灼痛我的眼皮,你的施舍像一根沾着花粉的蜂刺。
我是瞎了,为了保持内心的洁净,我不敢睁眼看这大千世界的色空交织,不愿看见你们被哲学和小人书装点的表情,不愿看到你嘴角那一丝残忍的皱纹,不愿看到你们因讨好重要人物而变得衰老的笑容。
让一个遁世者看到这一切是残忍的。让最纤柔的虹膜接触这些景象是残忍的。
我只愿潜入你们内心的蝉穴。我把守着大地的入口,只是为了领受人性的真诚。
我是瞎了,我的半个身子没在海水里,海水比黑夜更黑。从前有个跛脚的诗人也曾这样浸泡在海水里,用血的灰烬为朋友献祭,直到人子的身体被海神托出波浪。
人们啊,同一道波浪也裹挟着你、戏弄着你,同你正人君子的自尊心开着玩笑。
而我愿意你们是一枝芦苇,越过万劫波浪,凌虚而去。
而我祈求你们不是一块顽石,为俗务和劳作所牵累,沉入昏庸的水底。
这就是我,一个瞎子,一个丝弦上的国王,唱给你们的诗篇。
四 酒
爱酒的人为酒所伤。
跟我走吧,兄弟,走到镜子里,和满腹狐疑的自我下一局漫长的围棋。
跟我走吧,兄弟,到泉水里泡一泡,把老于世故的表情擦洗干净,你看我们多像一场来自高天的雨水,淌下屋檐,跌进河谷,本想爱抚两个世界,却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兄弟,你照照这面镜子,你看这张五千年的老脸,像泡在酒里的人参。
容颜苍老啊,一只鹰在眼角缓缓飞行。秋蝉的背部,夏天死了。春天改嫁,一个孤儿守着破败家园。
那个生我养我的人在我胃里放置了一根不生锈的铁钉。多少年了,血液与爱情一遍遍冲刷,它不肯有丝毫退让。
我的胃里有一股饥饿的火焰,在时光里抽搐。别撒下黄色的沙,别撤走无用的水。
那么祈祷酒!
祈祷这迷醉的神!
祈祷这攀着我的理智迅速窜高的葡萄藤!
祈祷这无边的狂语,无边的落花,无边的呼喊,无边的呕吐与昏迷!
祈祷胃壁的碾磨与挤压!祈祷血管里狼群的利爪,手足的风化!泪水像少女初潮一样惊恐的泛滥!
父亲和酒,两个同义词,一对挛生兄弟。一棵竹子在我记忆的深处摇晃,一片竹林在我记忆的深处摇晃,我开始觉得,这一切怀想并非没有意义。
你的手摸过棉桃,摸过粗糙的石磨,又摸过彩虹的喷雾器。你结实的牙咬过树皮。
你的双腿跨坐在屋梁上,汗水打湿了我的屋顶。
你在日光下狠狠地磨刀,你把一顶旧帽子掼进我的眼眶里,你信手一挥,打断了桃木门栓。
你哭,强烈的反光把我击倒在地。然后你吐啊、吐啊,从我的童年一直吐到如今。
我也愿意放开缰绳,任马儿驮我到山穷水尽之处。
我也愿意把祖宗的训诫高高挂起。
我也愿意放鹿归山,荷着铁锄,在随便哪一座青山之腹,为自己掘好坟穴。
我也愿意扛着葫芦,或被葫芦所扛。我也愿意这苦命的肉体,成为烈酒的康庄大道。
我也愿意以头发点火,把表情焚烧,在无人的荒野放声歌唱。
我也愿意有一双芒鞋,踩在帝王的坟头,踢翻了座座神庙。
我也愿意与你寂然对坐。你痛苦,也有人为你痛苦;你哭泣,也有人为你潸然落泪。
让那短暂的迷狂成为没有见证的事物。
轻微的晕眩。一枚嫩叶的狂想。系着红发带的女人向自己的骨肉发动的进攻。
一排排书橱土崩瓦解。
让理性成为无用的东西。让性灵露出来,露出来。
让无遮无拦的河流浪费掉一生的轻狂。
让老实的人原形毕露。
让无耻的恶棍喷着恶梦与粗气,像一列没有方向的火车。
让神圣的孩子赤裸。
五 两封信
1
远方你好,从风中解放出来的云朵你好!
我已到达青色的城,在肮脏的马背上我度过了无数个世纪,阅历了众多黝黑的面孔。我忧伤的葫芦磨出了一个个窟窿。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叫卖的声音。
租车的人,守着满筐酸李的人,出售书籍的人,把一柄铁剑吞进喉咙的人,牵猴的人,在脖子上绕钢丝的人,当街念经的人,挎着海鸥相机揽活儿的人,被昨夜的一个恶梦蜇得说不出话的剃头匠,在掌心画着阴阳鱼的算命先生,旅馆的拉客者,半跨在摩托车上的二流子,在秤盘上种植葡萄的人,蹲在地上吃西瓜的人,为过往少女迎风抖开花裙的人
是这青色的城。
允许我在此歇脚。
我居住的旅馆对面,有一座富华酒家,从七楼的窗户下瞰,正好可以看见。
我要去的地方,我在梦里依稀游历过的地方,唯一的道路被大雨切断。草原遥不可及,地平线在心底拉成了弓,而回忆却象饿犬一样把我围困。
心底有一根线愈抽愈紧,你的手并没有动。
允许我像蛹一样睡去,像蝴蝶一样醒来,允许我感到无边的空虚,允许我对你说:“不知是真是幻,是去是留。”
允许我把内心的杂货铺腾空,允许我为你保留最高的星辰。
允许我呼啸成一阵悲哀的风,允许我成为惊骇的发源地。
允许我把极度的欢乐强劲地压入你的身体,允许我为你戴上火辣辣的荆棘之冠。
允许我养育洪水,允许我落下无边的细雨。
允许我……间歇地疯狂!
2
你好,远方,你好,枯萎的船帆。
今天,八月十三日,我在呼和浩特,青色的城,所有的城市都令我厌倦。
所有的街道都有它的走向。所有列车都有始发站和终点。所有的旅人都有真实的目的地。
晒硬的大道上有两道车辙,兔子有三窟,桌上旁边有四个圆凳,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价目
表——我面对一个过度真实的世界。琐屑,平庸,规则齐整,逼人就范。
我的脚在两个车站之间轮回。“买一本列车时刻表!买一张地图!买一份通往快乐与遗忘的护照!”
挑战意味着失败,有何胜利可言?我还能到哪里去?
我所爱的人,爱我的人,一切一切的幻影,引我走入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对抗、没有名称、没有差别的世界。
我渴望突围,反被淤泥陷住了双足;我渴望缺席,反而遭到审判!
仿佛梦魇!
“……我买了一把锋利的刀。”
必须走,必须永远在走。
离开旅店、梦、露水与睡眠。
六 云
不应该为云再唱任何赞歌,不应该再把花粉和阳光倾泻在云的胸脯上,不应该再仰望、咏叹、着迷于这不羁的精灵,
因为有人来过,有人用她致命的柔情,提到过云的名字。
但是……
1
不安的羊群,在我整个童年的上空骚动,用它们骤雨般的蹄脚,为我纯洁的视觉播种鲜花。
那是只用几片白云便能覆盖无遗的年龄,那是用经卷、打手板和罚跪无法埋葬的辽阔年龄。
与洒满了金粉的云朵一道起床,与镶着银边的云朵一道沉入大海的眠床,与弹弓和金龟子恋爱,与杨树上的知了誓不两立,与雷电情同手足,与深入平原的山麂同病相怜。
只要有一道山岗可供幻想栖息。
只要有一双松树之翼扇风点火。
只要在青瓦屋顶有一道不断上升的白烟。
……仰望云朵,练习智力,想象的大门洞开。
“为我们进述云的故事,为我们描画神仙和他们的座骑,为我们邀请各种各样未曾见过的精灵,为我们降神和驱魔,为我们摘下无穷无尽的水果……。”最贞洁的目光在祈求。
宛如白璧的心为天空投射霞光,最简洁的词汇挥动绳鞭,把童年时代的白云,
驱赶到年龄的深处。
2
暴怒的云,不祥的云,敏感成病的云呀,此刻你们要挤裂天空的陶瓮。
从你们自身情感的暴力中,闪电狂泻出来,雷霆迸发出来,没完没了的毫雨倾注下来。
你们就像肿胀的手臂在锅里搅动。
你们就像两盘刚被錾好的石磨,扣在了一起,要吞吃普天下无言而忧伤的玫瑰。
你们的眼睛潮湿,好像哭过,又好像要哭,你们发烧的脚趾像树根一样,紧扣住岩石的裂缝
。
这必是一些要把棋局搅乱的云。这必是肉体深处的魔鬼装扮了,来拷打我们的心灵。
这必是涵育宁静的狂躁,这必是养育美德的污泥
3
这样的冷漠,这样的骄傲,这样的不同凡响。
这样的绝艳,这样的飘忽,这样的无所顾忌。
这样的不可捉摸,这样的为整个天空所宠爱。
这样的骄纵任性,这样的蹙着蛾眉,这样的噘起点点残红。
……这样不安分,不居留,不让任何透明的丝缰驾驭。
这样的疾驰,这样的藏匿。
这样的无可比拟!这样令修辞学无能为力!
这样轻而易举就逃出述说的罗网!
这样的伤害,这样的欺凌与玷污,这样的说黑就黑,说红就红。
这样的自筑樊篱,这样的划地为牢,这样的双重囚禁。
这样的干涸,这样的枯萎,这样的坐以待毙。
这样的狂热冲撞,这样的洗刷,这样与死亡对抗。
这样宽恕,这样寂静,这样的飘忽,这样的不同凡响。
4
风说:
“我来自事物的核心,天空是我的庭院。
“从大海的隐秘之处,我的力量聚集起来。
我因为慷慨而享有盛誉,又因为狂暴背上恶名。
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世细细思量过了,我不能像烟一样活着,像冬天的白色哈气一样短暂,不能像衰老的狗一样恋爱,像窃国贼一样高冠博带、道貌岸然。别问我什么时候会平息,会宁静安详,会歇息在潮湿的从林洼地里。我的欲望会再一次被狠狠唤醒。
“我打算一辈子就这样放纵,我持有阴阳两界的特别通行证。我的心在每一片国土上都有代言人。
小巧而优美的车辙对我是不适宜的,苹果园旁的高龄长椅对我是不适宜的,爱情围裙下恭顺的小公鸡对我是不适宜的,我习惯于在浩茫太空
大步疾行,
像一个醉汉,一个袒着肚皮的盲诗人,一个被废黜的流氓王者。我习惯于骑着阳光的马,或者踩着月亮的甲板,我是我自己的战舰,我是我自己的六龙车。
“……多么孤独!如果没有云朵与我嬉戏,如果没有云的挑逗、婉拒、逃匿和耳鬓厮魔。
……多么暴戾!如果仅仅是掀翻屋顶,把万吨巨轮扣入海底,如果只是玩着掷骰子的游戏。
如果不去驱赶长云,撕扯云团,揉搓云丝,拉长云阵,拆散云的情侣,如果不在云里渗沙,不让云天落泪,不拦腰击中云彩的骄矜,如果不给云中龙虎套上透明的丝缰,那该是多么
遗憾和孤独!”
5
一种幸存的美
让我无缘无故地愤怒。
未和这个世界取得任何谅解,你躺在群山之上,你就这样躺在群山之上,你向大地上的人们
诠释一种惊世骇俗的美艳。
西去的阳光太匆匆、太苍老、太衰弱,却把你胸脯上的红痣点得更红,你就这样,像一个人似的敞开了自己,你微弯的双膝更加放荡,仿佛等候着什么。
天空是空虚的,你的美和你的焦渴
未取得任何谅解。
6
在我有限的生涯里,我还从未见过
像此刻的你
这般温柔的事物。
一眉新目为你洒上淡淡的银光,你的存在仿佛并不存在,你的脸庞如在牛乳中洗过,你的思绪透明,而你的神情仿佛只是要和五月的清愁
做一对短暂的恋人。
月光的河在树梢上,在树梢之上的无边虚空里。
你的河流在我颈项间流转。
万籁轻吹,像水波晃动水草一样轻轻摇你入梦。你的眉宇间笼罩着天国的沉静。
让风带着合欢花的气息平伏下来,让一滴露水落地时更加轻盈,让一朵素荷在无限星光的水池边独放,让蒲公英的绒伞随着呼吸翩翩起舞。
让梦因为梦自身而被原谅。
这是无人看管的雪国。
只好听任你在清寒的高处美着,温柔着,
笼罩着我们那一颗潮湿的心。
7
海洋翻腾,普天之下,唯一的海洋在翻腾。从群山之上,又有新的龙族翔舞。
穿云裂石的骄傲!天空也没法囚禁的骄傲!令人瞠目结舌的骄傲!
更有力的手臂筑起一个祭坛。太阳之下是自身,诸神之下是自身。疯狂的创造混淆了自然力。
更有力,更年轻的种族在天空奔跑,叫啸。
从阴暗的心中,诞生出无边的快乐,无边的傲慢。
七 谈论孤独
有时大地在枯死的树桩上沉寂下来,天空变得灰暗,湖面像水银一样散发着懊丧的气味,死者的灵魂,一件破旧的旗帜,在晚风中扑扑吹动。
整个世界的光亮拧在一起,也只能照顾一朵恍惚的睡莲。
于是经常有人怔怔走来,跟你谈到孤独。
“……一个人在大海上航行,和自己的内心对话,那滋味多像在嘴里衔着一口生锈的铁钉;”
“一只白鹤被残霞染得血红,在着霜的湖边盘旋,那滋味多像抽空了灵魂的芦苇。”
然而,孤独并不是荒凉山坡上的一棵柏树,也不是无星之夜的一轮圆月,孤独有时是一股强劲的泉水,霎那间迸涌而出,引发欲望的灼痛。
孤独是一朵旷世奇花,在语言罕至的地方独自盛开。它的脚下是喧嚣,它的头顶是虚空,
无人到此,更无蜂蝶。一旦语言前来抚弄,它便会倏然凋萎。
所以,谈论孤独是可耻的。
在我的朝圣生涯中,我遇到过很多和我面色相同的人。
那是些得罪了帝王的人,穿草鞋的人,远谪的人,脸上烙着火印的人。
他们的妻子困守诗歌的木匣,困守泪水之城;他们的马匹在没有水草的宫廷里放牧。
他们或戴着红柳编织的马嚼,或背着腥味的鱼筐。
我们彼此点点头,眼睛里露出剥了皮的胡杨树一样的颜色。
这样的行程无疑是孤独的,独自守望着窗外变幻的风景,汹涌的风景。
那被水流推动的白色巨石,那被时光抻长的远山,那苍凉凝重的暮云,那既无欣喜也不悲哀的田野,那些在铁路旁干活的麻木不仁的人,那些极易被忽视的长毛牲口,那些不断被种植又不断收割的可怜的攸麦。
那汹涌的风景啊。
只能听凭眼睛在纷至沓来的撞击中失明,任耳膜结满初春的薄冰,任天空蓝得彻骨,任大地绿得无聊。
这样的行程无疑是孤独的——不断向内心进发,执着近乎残忍,越过火焰之沼和高寒山谷,直至抵达那混乱而又疼痛的内核。
是的,这样的行程无疑是孤独的。
但是,让孤独成为有用的东西,当水藻在九月的寒流中开花,不要给寂默的水面增加更多的负担,不要再渴望放出心中的狼群。
不要让这些话语成为教诲,成为花尾喜鹊在高大刺槐上的布道词。
当晚风带来远方的骚味,公牛会不由自主地伸长脖子,在荞麦地边叫出声来。
但做一个人意味着在舌根压上陨石。
像那个扛着一段原木涉过齐腰深的浊水的人,那个迈着播种者的步伐丈量他的河滩的农夫,那个在列车上唱歌取暖的蒙古汉子(他“要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他的噪子像玻璃一样明晃晃)
甚至像那头临近生产却无人照看,胯上的花纹不停抽动的母牛。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向他们学习,忍受真正的孤独。
八 刀
终其一生,我们不过是在刀上行走,把刀锋对准自己,把刀柄递给别人,或者相反。
终其一生,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一把刀。那些淬过火的,一生寒光烁烁,剖开整个世界,也剖开了心中的那枚鸟卵。那不曾开刃的,永生永世都活在一个不曾兑现的允诺之中。
未被完成的洁白啊,未长出羽翼的梦,在霜降前未及抽出新芽的风。
放弃一本书,选择一把刀。
藏刀于腹,冰冷的铁镇压内心的火种。藏刀于行囊,欲望使神器昼夜嗡鸣。
灵魂还要忍受多久?那被思想淬砺的锋芒还要克制多久?那个伟大的、敏感的、潮湿的、藏着个马蜂窝的神圣禁区还要空虚多久?
火焰啊,饥饿的火焰。
而语言也是刀。你看多少人自以为聪明得计,在刀刃上耕种,直至双手血流如注,直至面目全非,直到姓氏被磨损、消蚀了光芒,直至门环与铜锁都不堪敲响!
你看多少人佝偻着,和刀睡成了一对恋人。
这一夜也是一把刀,镀银的小刀敲响瓷盘。纤手破新橙,闪电的刀整夜都在暴风雨的床上辗转反侧。一只船在侧卧的刀面上平滑前行,花香切开了记忆,鲁莽切开了心上的厚茧。直到一声尖利的叫,亢奋的叫,把夜空一撕两半!直到你微眯的双眼间,一缕寒芒将我的魂魄洞穿。
把刀交给你就是把自己交给空虚。从此时间是我的君王,我的父亲,我的不通人性的轮毂。
谁将从此判定我的生死存亡?谁将大权在握,划定耻辱与尊严的边界?谁来殡葬,谁来超渡?
谁还能那样冷,那样坚硬,那样势如破竹,为我的软弱划一个庄严的句号?
我手里握住什么,才能得到安慰?
但是刀!
不一定非要插入掌心。
但是刀!
不一定非要饮血为生。
有的刀静若处子,却伤人无数。有的刀一生英明,却终于把自己送往炼狱。真的,刀不一定非要运动着,才能分配死亡。
因为我看到你也是一把刀,长在思想的荒野上。你渴望成为犁,却终于成了树。而且没有别的树作你的朋友,而且没有水流来洗濯你的泥足,而且鸟群在你的身体上洒上点点粪便。
你的速度在沉睡。你只是在虎头刀柄上
憋出了一根尖刺。
多少个夜晚我这样凝视月亮,这恼人的刀、易损的刀啊,云彩把你拭了又拭,你的霜刃依旧沉寂。
多少个白昼我这样面对河流,你温柔、凶猛地切开大地之肤的河流,你的刀锋始终不曾迟钝。
什么时候把我这把愤怒的刀、缺损的刀、老迈的刀、胡言乱语的刀、花纹斑驳的刀、绝望的刀、苦恼的刀、欲望的刀
重新收回炉中?
我梦见饥饿的火焰,吱吱叫的火焰,垂涎欲滴的火焰。
我感到自己像一块冰,在大地之腹溶化。
九 大水
被一场大雨激怒的人,会不会被一场大水冲走?
一年一度,这样的季风会吹进田园,掀翻诗人的茅屋,倒伏庄稼,把青涩的果子打落满地。
这样的霹雳会像一朵花一样,开在我简陋的餐桌旁边,让女人和孩子哭泣。一年一度,这样的大水像饿疯了的狼群席卷而过,踩平了高坎深沟,动摇氏族和村庄,吞没千百头牲畜,只留下狂暴的泥沙。
一年一度,数不清的庄稼弯下腰去、弯下腰去,在大地的胸膛上哭泣。庄稼和庄稼哭泣着,搂在一起。
那些被大水的利爪刨挖出的巨石,安然卧在迟缓的荒野,无动于衷,棱角依早。命运对于它们是个谜,时间对于它们是个谜。
而它们坚硬的内心,对于世界则是一个谜。
把自己修炼成石头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做一棵庄稼。
我们甚至不能像庄稼一样拥有一块真实的泥土,我们只能是一枚草芥。
我们甚至不能像草芥一样拥有飞翔,我们只能跌跌撞撞在岁月的大水里。
我们只能是自己。
听我讲讲童年时代的大水吧。童年时代的屋顶在大自然的手指间摇晃。
粗大的砂砾是不是也曾这样抽打过你的脸庞?狂野的旋风是不是也曾那样让你躲在课桌底下?
你是不是也用一把锄头引发过暴风雨?你是不是也有一个老朋友这样坦然地迎接大自然的暴虐,面朝死亡?
谈水色变。童年时代的河堤是脆弱的,随着大水不断地扭动,像两条谄媚的蛇。
丢失了亲人的人沿着河堤哭泣,沿着掌心的命运大道凶猛呼嚎。丢失了亲人的人让河流的两岸从此不得安宁。
而一个少年独自走上了沙岸。他像一支狂热的蜡烛,站在危险的奶油上,火苗在他的瞳仁里摇晃。这个孩子,他安详地寻找什么?谁知道他在寻找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到底谁弄清楚了,他在寻找什么?
只有母亲的呼喊
落在时间的后头。
就像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黑夜一样,每个人也都拥有自己的大水。每个人都曾用他的前额迎接过粗野的风,每个人都曾让自己的花朵长久地泡在雨里,每个人都曾像骄傲的大理石柱一样迎接过激流。
人性的伟大在哪里?人性的伟大在哪里?人性的伟大在哪里?
我的兄弟啊!我的亲人啊,我的素昧平生的亲人哪!掩埋的掩埋,放荡的放荡,随波逐流的
随波逐流!
把我留下来!
把我交给大水!让我做泥沙的主人!
让我和奔流的时光做一对玩伴!让我在恶如狮虎的恶浪中进退自如!
不要把一只鹰的死亡归咎于我。不要把天空的枯萎归咎于我。不要把田野上花朵的荣枯归咎于我,不要让我在黑夜的通知书上签名!
不要磨快了刀,砍伐我的树枝,不要用黑色油漆涂抹我的名字,不要剥夺我风火的年轮。
不要抽干我肉体深处的太阳,不要把木楔打入我的掌心,不要用轻薄的口吻把我称作人民。
世界,世界,让我的双膝一跪到底!让我张开浩大的风的双臂,像宽阔的梧桐树叶一样伸展自己,让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
因为我整个也是一场大水,不肯听命的水,不愿居留的水,无法安慰的水。我整个也是一场浩茫的奔流,向着一个盲目的高度。
我整个也是一匹不驯服的马,我是你的逆子,我的豹尾在你身上留下鞭痕。
世界 ,世界!为我倾覆大海,为我保留逆子的尊严,为我发放一张人的证明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