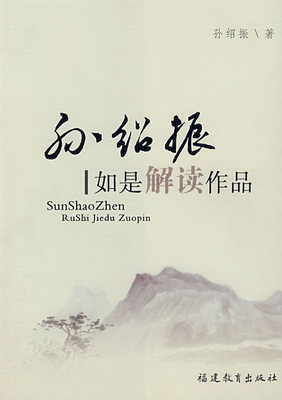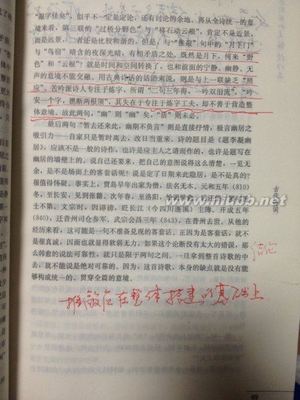读李商隐《锦瑟》
孙绍振
编者按:李商隐《锦瑟》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但很多老师反映这首诗晦涩、难懂难教。孙绍振先生《读李商隐〈锦瑟〉》首先对历代诗评家的众多说法作了归纳和评析,然后直面文本进行第一手的直接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里,我们不仅能了解孙先生关于这首诗的独特看法、丰富的文献资料,还能学到行之有效的文本解读方法。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的《锦瑟》属于唐诗中的朦胧诗。虽然题曰“锦瑟”,然而实际上取其首词为是,等于“无题”。和他的以“无题”为名的组诗相比,其主旨之飘忽,全面把握之艰难,在李诗中是位于前列的。但,这并未使读者望而却步,相反,自宋元以来诗评家们众说纷纭,所持相当悬殊。归纳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来,大致有如下几种:第一,“咏物”诗,也就是歌咏“锦瑟”。代表人物苏东坡这样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引自《缃素杂记》,见陈伯海《唐诗汇评》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0页)这个说法得到一些诗评家的认同,然亦有困惑不已者:“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此诗之难也。”(王世贞《艺苑卮言》)这个怀疑很深刻:用语言去图解乐曲,还有什么诗意呢?以苏东坡这样的高才,居然忽略了诗与乐曲的不同,足见此诗解读之难。
第二,推测其为“感国祚兴衰而作”,(《桐城吴先生评点唐诗鼓吹》)今人岑仲勉在《隋唐史》中也“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两说虽不尽相同,然而着眼客观之物或社会生活,回避从作者生平索解,则异曲同工。岑仲勉甚至明确指出此诗“与恋爱无关”。(《唐诗汇评》下,第2412页)和上述思路相反,从作者生平中寻求理解的线索,则产生了第三种说法:“细味此诗,起句说‘无端’,结句说‘惘然’分明是义山自悔其少年场中,风流摇荡,到今始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也。”(《龙性堂诗话》,见《唐诗汇评》下,第2411页)持这种“色空”佛家说法的比较少。一些诗评家联系到李商隐的婚姻生活,于是又有了第四种说法——“闺情”。还有人将此诗的迷离恍惚与妻子的早亡联系起来,又产生了第五种说法,认定其是“悼亡诗”。朱彝尊说:“意亡者善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华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殁也。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葬之也,犹言埋香瘗玉也。此情岂待今日‘追忆’乎?只是当时生存之日,已常忧其至此,而预为之‘惘然’,意其人必然婉然多病,故云然也。”(《唐诗汇评》下,第2410页)这个说法虽然比较系统,但其间牵强附会之处很明显。断定其妻年二十五早殁没有多少论证。“玉生烟”为什么是埋葬?也没有任何阐释,穿凿无疑过甚。其实如果是妻子,根本不用这么吞吞吐吐。第六种说法则强调,所以隐晦如此,有具体所指女性,且是令狐楚家的“青衣”。虽然这不无可能,但仅仅是猜测而已。
第七种读法是,“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庄生’句言付之梦寐,‘望帝’句言待之来世;‘沧海’‘蓝田’言埋而不得自见;‘月明’‘日暖’则清时而独为不遇之人,尤为可悲也”。(《唐诗汇评》下,第2410~2411页)对于同一首诗解读如此之纷纭,如果按照西方读者主体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则皆有合理性。但事实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有同样的毛病,那就是只是论者的印象,并未对全诗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未揭示出这首在内涵上扑朔迷离的诗为什么直到千余年之后,仍然脍炙人口,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历史文献虽不乏学术资源,但并不能解开这个谜底。剩下来的办法就只能是直面文本进行第一手的直接的分析。撇开古人所有的猜测,从文本出发,理解此诗似乎并不太难。对于“五十弦”,许多注家多有误会。周汝昌先生清醒地指出,据此“判明此篇作时,诗人已‘行年五十’或‘年近五十’,故尔云云。其实不然。‘无端’,犹言‘没来由地’‘平白无故地’。此诗人之痴语也。锦瑟本来就有那么多弦,这并无‘不是’或‘过错’;诗人却硬来埋怨它:锦瑟呀,你干什么要有这么多条弦?瑟,到底原有多少条弦,到李商隐时代又实有多少条弦,其实都不必‘考证’,诗人不过借以遣词见意而已。据记载,古瑟五十弦,所以玉谿写瑟,常用‘五十’之数,如‘雨打湘灵五十弦’‘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都可证明,此在诗人原无特殊用意”。(《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7页)周汝昌先生此说颇为精辟。琴瑟本来是美的,饰锦的琴瑟更美,繁复的曲调也是美的,美好的乐曲令人想起美好的“华年”,不是双倍的美好吗?然而,美好的乐曲却引出了相反的心情,这就提示了原因:美好的年华一去不复返。沉淀在内心的郁闷本是平静的,可是一经锦瑟撩拨起当年的回忆,就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了。这里抒情逻辑的深邃在于:第一,当年和如今的曲调相同,心情却截然相反;第二,本来奏乐逗引郁闷,应该怪弹奏的人,可是,不,却怪琴瑟“无端”,没有道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弦,要有这么丰富的曲调呢?美好的记忆,不堪回首。弦、柱越多越是伤心。第三,如果年华光是一去不复返,也还罢了,李商隐所强调的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往日像庄子的梦见蝴蝶一样,不知道是蝴蝶梦见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蝴蝶。也就是,不知是真是假。这意味着往日的欢乐如果是真的,和今天对比起来是令人伤心的;美好的年华如果是假的,往事如烟之虚幻,更是令人伤心的。这样的哀伤如何与“望帝春心托杜鹃”在意脉上贯通呢?一般来说,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蜀国君主望帝让帝位于臣子,死去化为杜鹃鸟。这和“一弦一柱思华年”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注解是:杜鹃鸟暮春啼鸣,其声哀凄,伤感春去(有的语文教科书就持这个看法)。用在这里,可以说,悲悼青春年华的逝去,从而将回忆的凄凉加以美化。
沧海月明,鲛人织丝,泣泪成珠;将珠泪置于沧海明月之下,以几近透明的背景显示悲凄的纯净。周汝昌先生分析前句与此句的关系说:“看来,玉谿的‘春心托杜鹃’,以冤禽托写恨怀”“海月、泪珠和锦瑟是否也有什么关联可以寻味呢?钱起的咏瑟名句不是早就说‘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吗?所以,瑟宜月夜,清怨尤深。如此,沧海月明之境,与瑟之关联,不是可以窥探的吗?”(《唐诗鉴赏辞典》,第1127页)周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望帝春心的性质是一种“清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复杂难言的怅惘之怀”。周先生的说法还有发挥的余地:这种“清怨”的特点就是:第一,隐藏得很密,是说不出来的。从性质上来说,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样的。藏得密就是因为恨得深。这里的恨不是仇恨,而是憾恨,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种“恨”。第二,隐含着不可挽回,不能改变的憾恨。第三,为什么要藏得那么密?就是因为不能说,说不出。用“蓝田日暖玉生烟”来形容,一来是从字面上讲,日照玉器而生气,气之暖遇玉之寒乃生雾气,如烟如缕。二来,这个比喻在诗学上有名:语出诗歌理论家司空图《与极浦书》:“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实际上就是可以远观,却不可近察,也就是朦朦胧胧的感觉,它确乎存在,然而细致观察,却无可探寻。这种境界,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似乎失落了什么,而又不知道失落了什么,似乎在寻找什么,又不在乎找到没有的境界是相似的。最后一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潜在话语是很矛盾的。先是说,“此情可待”,可以等待,就是眼下不行,日后有希望,但是,又说“成追忆”,那就是只有追忆的份儿。长期以为可待,而等待的结果变成了回忆。等待越久,希望越虚。虽然如此,应该还有“当时”,但是,“当时”就已经知道是“惘然”的。没有希望的希望,一直希望了很久,最后剩下的只有“追忆”。把感情(其实是恋情,详见下文)写得这样绝望,在唐诗中,可能是李商隐独有的境界。李商隐显然善于把这种绝望概括成格言式的诗句: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马嵬》)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无题》)
不论是他生还是此生,不论是相见还是相别,不论是来还是去,都是绝望的。把情感放在两个极端的对立之中,这就使得李商隐这些诗句有了某种哲理的色彩,但是,这种对立引出的并不是二者统一于希望,而是绝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而生命就是在希望中消耗、发光、燃烧,直到熄灭: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春心如花,结果是所有相思都化为灰烬。这样极端的概括,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的,故李商隐的哲理还是抒情的哲理。这样的绝望,不是太窒息了吗?李商隐把它放在回忆中去,拉开时间空间的距离,拉开实用理性的距离,让情感获得更大的自由,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拿手好戏,李商隐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是什么样的感情达到这样刻骨铭心的状态呢?不能不令人想到恋情。前面提到不少论者把“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春心”,解释为“伤春归去”。当然不无道理。但在唐诗中,“春心”只有描述自然景观时才与春天有关。在描述心情时,则是特指男女感情。“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李白《江夏行》);“镜里红颜不自禁,陌头香骑动春心”(权德舆《妾薄命》)……都是与恋情有关的。正是因为这样,许多诗评家读《锦瑟》时才不约而同地联想到私情,甚至具体到“令狐楚家青衣”。“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典故有许多版本,被许多注家忽略了的是扬雄《蜀王本纪》:“蜀王望帝,淫其相臣鼈靈妻,亡去,一说以惭死”,化为子规鸟,滴血为杜鹃花。(《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通雅·卷四十五》)杜鹃啼血染花隐含着的不仅是绝望而且是不能明言的恋情。“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春心”应该是秘密的恋情【】的悲痛。只有这样,下面的“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清怨”和“蓝田日暖玉生烟”的可望而不即在意脉上才能贯通。特别是最后一联,以为此情可待,而反复落空,只留下回忆,眼下、过去和当时都是绝望,只有一点惘然的回忆值得反复体悟,而在体悟中,又无端怪罪锦瑟的多弦,弦弦柱柱都逗引起“思年华”的清怨。清怨从何而来呢?以为此情可待,其实当时已经感到“惘然”。当中两联的“庄生晓梦”之虚、“望帝春心”之悲、“月明珠泪”之怨、“蓝田玉烟”之净,所写的就是这个明知“惘然”偏偏要说“可待”的悲痛。自己这种痴情,在逻辑上,明明是很“无端”的,可是又偏偏怪罪锦瑟“无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有两个“无端”:一个“无端”是用直接抒情的逻辑写出来的,是对锦瑟的无端的责难;另一个“无端”是明知不可待而待。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越是不合逻辑,情感就越是痴迷。但是如果光有这样的直接抒发,作为诗来说,形象的感性是不够丰满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甚至可以说是单薄的。原因在于,“此情”的“情”读者没有感觉,因而当中两联的任务就是把形象的内涵充实起来,从感知上丰满起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里的庄生和望帝,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典故,李商隐借助对仗,不但在形式上整齐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且使它们在意脉上连续起来,上承“思华年”的弦柱,下开“珠有泪”的清怨,在大幅度的逻辑空白中隐没其内涵,造成扑朔迷离的甚至晦涩的美感,在唐诗中,可谓开辟了新风。提高阅读的难度,在这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联的手法和首尾两联不同,不是直抒胸臆,而是“立象尽意”,所立意象之间隐含着和谐的联系。蝴蝶和杜鹃,庄生和望帝,通过“晓梦”“春心”深化到梦中和心中,就不是一般的画图,而是心灵的画图。同样,沧海月明、蓝田日暖,在时间上是一晚一早,在空间上是一海一陆,在色彩上冷暖交融,而在情调上则是珠泪之悲,如遇寒雾,在联想上高度和谐统一。而且此联表面上与前联不相属,实则在意脉上渗入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性质,照应了首联的“思华年”,又为“成追忆”作了铺垫。这样,就以静态的画图,沟通了首尾两联意脉的律动,使得全诗不但在情绪上有机统一,而且意象和抒情、视象和心象、静态和动态丰富交融,统一于严密的律诗的规范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