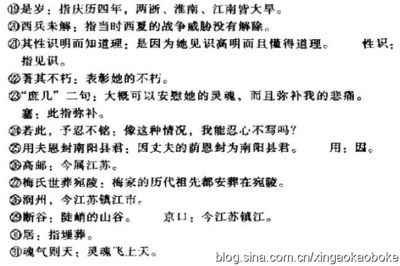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频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乡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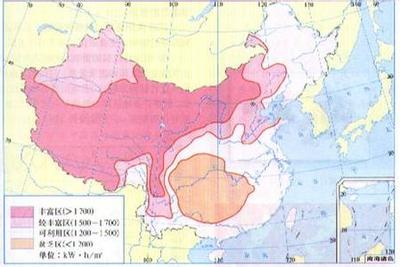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译文]
二十一日,柳宗元向您表白如下:
承蒙来信说要拜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不深,学业也很浅薄,从各方面衡量自己,看不到可以做老师的地方。虽然我经常喜欢发议论、写文章,但从来不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超人之处。想不到您从京师长安来到这偏远的地方,竟然认为我尚有可取之处。我认为自己确实没有可取之处,即使还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我做一般人的老师尚且不敢,难道还敢做您的老师吗?
孟子说:“人的弊病就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从魏、晋以后,人们更加不敬重老师。当今时代,没听说还有什么人敢做别人的老师。如果有敢于做别人老师的人,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讥笑他,认为他是狂妄之人。只有韩愈勇敢,不顾社会上的坏风气,敢于冒着别人的讥笑和轻侮,招收后生学子为徒,还写了一篇《师说》,从而郑重而不屈地当起老师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果真把这当作怪事,群起而责怪谩骂,他们挤眉弄眼,拉扯示意,给韩愈身上增添诽谤的言辞。韩愈因此得到了狂人的名声,居住在京城长安,连饭都来不及煮熟,又匆匆忙忙东去,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有过多次了。
屈原在他的赋中说:“城里的狗成群结队地狂吠不止,是看到了它们不常见的东西。”我以往听说庸国蜀国的南边,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大阳,有一天太阳出来了,狗就对太阳狂吠,我当时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的永州,第二年冬天恰逢下了大雪,越过五岭,覆盖南越(今两广)的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失措又叫又咬,到处狂奔,一连好几天,直到雪化尽了才停止,从此以后,我才相信以前听到的蜀犬吠日的传闻。现在韩愈既然已经使自己成为蜀地之日,您又想让我成为南越之雪,这样不是让人认为我有毛病吗?人们不仅认为我有毛病,也会因此认为您有毛病。然而白雪与太阳难道有什么错误吗?只是狗狂吠不止啊!推测如今世上见怪不吠的人能有几个,那么又有谁敢以不同凡响的行动招引众人的侧目而视,招来大家取笑,惹来别人恼怒?
我自从遭贬谪以来,更加志短,没有什么打算,在南方居住了九年,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热闹,哪里经受得了喧闹的声音早晚在耳边聒噪,骚扰我的思想?如果这样,本来无聊烦闷的日子就更加无法过下去了。平时在这里,意外遭到别人非难的事已经不少,惟独就缺少好为人师这一件事了。
我又听说,古代很看重成人加冠仪式,表示将要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他,这是圣人所特别认真思考的问题。近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成人仪式了,近来有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为儿子举行了成人礼仪。仪式完毕后,第二天上朝去,来到等候朝见的地方时,把笏板插在衣带中,对在等候朝见的同僚们说:“我的儿子举行完加冠仪式了。”跟他交谈的人都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京兆尹郑叔则生气地倒提着笏板退后一步,站定了说:“这关我什么事啊?”在场的人都哄然大笑。世上的人没有人认为郑尹则行动不对,不没有人把孙昌胤的做法为快事,这是为什么?因为孙昌胤独自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自认为是老师的人跟这事非常相似。
您品行纯厚,文辞修养很深,所有的作品恢弘博大,有古人作品的形态面貌,即使我敢于当你的老师,对你又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因为我比你年长几岁,闻道著书的时间比你早一些,真的想来往彼此交谈读书写作的心得体会,那么我一定愿意把我心中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你。您可以任意自行选择,决定取舍哪些就可以了。如果要我来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能不够,而且又怕前边所说的那些难以为师的情况,所以我不敢为师的主意已下定。您以前说想看我的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经全部陈列到您的面前,这不是用来在您面前夸耀自己,只是姑且想借此观察您的表情态度,来鉴别我的文章的好坏。如今您来信,对我和我的文章的赞誉实在大过分了。我知道您确实不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一类人,只是过分看重我才说了这样一些话。
起初我年轻幼稚,写文章,把讲究辞藻当作巧妙。及至长大以后,才明白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的学说的,本来就不该一味地追求漂亮的外表:致力于华丽的辞藻、炫耀声韵的悠扬,把这认为是自己的才能。所有我所陈列在您面前的文章,都是我认为接近圣人之道的,然而又不真正明白这些离圣人之道究竟是近还是远。您熟悉圣人之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我的那些文章离圣人之道不远了。因此,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掉以轻心,担心太轻率而不深刻;从不敢以懈怠的态度来进行写作,担心文章结构松散不严密;从不敢糊里糊涂写出来,担心内容不明,条理不清;从不敢以高傲的态度写出来,担心文章盛气凌人,不平易。我写文章,不任意挥洒的地方,是想要文章表现得深刻;尽情发挥的地方,是想要文章显得明快;理顺语气,是想要文章通畅;严格遣词造句,是想要文章精练有力;反复修改,剔除陈言旧语,是想要使文章清新,不落俗套;凝聚保存文章的气势,是想要使文章凝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来阐明圣人之道的写作态度。效法《尚书》来追求文章质朴,效法《诗经》来追求永恒的艺术感染力,效法《礼记》来追求分寸适宜,效法《春秋》来追求观点明确,效法《易经》来追求文章的变化发展,这些就是我用来学习圣人之道的源泉。参考《谷梁传》来磨砺文气通畅;参考《孟子》、《荀子》来使文章条理、畅达;参考《老子》、《庄子》来开拓思路;参考《国语》来扩大文章的意趣;参考《离骚》来使文章达到含义幽深;参考《史记》来使文章的语言简洁。这就是我广泛推崇吸取并融会贯通,从而来写文章的准则。
所有这些做法,果真是对还是不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希望您看后作出抉择,抽空把您的选择告诉我。希望您常来信与我交流,使我的这些写文章的方法和态度得到推广,这样,您虽然没有什么收获,我却很有收获,还说什么拜我为师一类的话呢?我们取交流写文章之道的实质,去掉拜师的虚名,不要招来越犬吠雪、蜀犬吠日的事而被朝廷的人所讥笑,那么实在万幸!柳宗元禀告。
(本译文参考王力《古代汉语》1981年版注解)
注:韦中立,史无传。《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孙。不书爵位。观其求师好学之志,公答以数千言,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必当时佳士也。书中谓“余居南中九年”,此书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韦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录于有司,当在此书后作。中立于元和四年中第。
导读——
柳宗元(773~819)山西永济人,曾做过柳州刺史,所以人称“柳柳州”。他当时参加了比较进步的王叔文集团,想改革时政。后来王叔文集团在旧官僚和宦官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被一些人说成是小人集团,柳宗元因此长期被某些人看成是品德上有欠缺的人。
柳宗元 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加以遭到沉重的政治迫害,被贬到边远地区,这就使得他有机会深入社会,接触下层人民。他的很多作品都暴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唐代古文家文论中的双璧,谈的主要都是自己的创作经验。但韩愈的文章谈得比较笼统,侧重描摹了学文的进展过程,柳宗元的文章则触及了具体师承和取法所在。正因为如此,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更可金针度人,使后学者有法门可入。
柳宗元这封信,只有日期而未署年月,根据其中“居南中九年”一语,可知是元和八年(813)在永州所作。全书虽大谈其“不敢为师”之语,而却愿陈所得,说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从信末所说的“取其实而去其名”这句话,实可知其微意之所在。
这封信宜分做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说在世风日下,人不事师、不闻有师之现实,自己之所以不敢为师、不欲为师与不能为师之的缘故。其中又可分做五段:
第一段是自谦不敢为师之意。
第二段是说世人不肯事师,并举韩愈抗颜为师而受诬事作证。
第三段用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二个喻对世俗的蒙昧表示愤懑。
第四段说自己的处境本已不堪讪詈,更不敢因作人师而雪上添霜。
第五段又以成人冠礼被废为例,衬托师道被世人所弃。抒发心中的慨叹,重师道而偏不欲作师,其用意可知。
这一部分的文字,充满着抑郁牢骚、愤世嫉俗之情,这当然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而发,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被贬谪以后后的“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发泄,因此措辞就未免有些支离拉杂。后人或说他“繁称琐引,子家修辞之一累”,或说他“词无涵蓄至此”,或说他“尖薄”,这些评价虽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又未免有不近人情之嫌。透过文章,我们从中能感觉到,在这些转折的词句和穿插的议论中,在作者的左顾右盼之际,文章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而对于尊重师道的传统,作者作了充分地肯定。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自道了为文的甘苦与心得,这是全文的重心;一方面说不敢以师名自居,文章末尾又申明取实去名之理来呼应上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言不敢为师而愿陈所得之故,文多转折。
第二段总说自己对于为文之道的认识过程,乃是从工辞而走向明道,即由对形式美的重视转到对思想性的追求。柳宗元学文,原自骈体入手,后来专攻古文,故字里行间,仍留有骈语的痕迹。但总的说来,还是以散体为主的。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创作道路的改变。
第三段论其如何“羽翼夫道”的方法,这也就是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表现内容的问题。前八句,以“心”、“气”言之,指下笔前的事先考虑,是就消极方面的防范来说的。后六句,指下笔时的具体运用,是就积极方面的努力来说的。为什么不敢以“轻心掉之”呢?后人对此的解释说:“文章不欲过快,快则单。”对付的办法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陈衍语)陈衍说:“奥者不欲其太浅显,明者不欲其太晦涩。”为什么不敢“以怠心易之”呢?陈衍说:“不欲过慢,慢则散。”对付的办法就是“疏之欲其通,嫌之欲其节”。陈衍说:“疏之指接笔言,廉之指转笔言。”的确,接笔以疏之,转笔使廉之,自然文字就不致散漫了。为什么不敢“以昏气出之”呢?陈衍说:“不可无持择”。对付的办法就是“激而发之欲其清”。陈衍说:“指开笔。”文章开拓一步,若用此法,自可去其昏气。又为什么不敢“以矜气作之”呢?陈衍说:“不可近妆做。”对付的办法就是“固而存之欲其重”。陈衍说:“指顿笔。”按,清袁枚《续诗品》有《固存》一则,引用柳宗元的话说:“固而存之,骨欲其重。”点出一个“骨”字,似比陈衍解释得更加深切圆满。陈衍又说:“发、存二句,谓炼格也。”按,矜气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客气虚张”,浮而不实,故不唯要以顿笔取重,兼宜以骨力镇之。
第四段是谈取道之原,这是本诸儒家的传统哲学观和美学观来说明的。《唐宋文醇》卷十三评《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这些话“犹有罅漏”;陈衍也说它“未见包括的当”。不过,一部书只用一个字来取用,自然难于完全妥帖,何况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也必然会有所分歧的。何焯的诠释是最为得体的。他认为:“求其质”是“言实事也;质为道德之本,言其大体”。“求其恒”是“言常理也;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细微”。“求其宜”是“节文之
中“,也就是“止乎礼义”的适度性。“求其断”是“是非之辨”,“求其动”是,“变通之道”。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就为文之取径为法而论,却也的确是能得其要领的。
第五段是说如何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关于这一段,有许多争议。如清梁章炬《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一则就说:“此数语分贴处实未能深切著明。”陈衍更指出:“《糓梁》焉得有气?《孟》、《荀》岂能并论?”“《国语》无甚趣。”的确,姑以文论,《孟》可言“畅”,《荀》不可以“畅”概之。“肆其端”者,《庄子》可以这么说,《老子》不过是连类及之而已。至于《糓梁》,由于柳宗元学《春秋》于陆质,质之学本于啖助;唤助之学,不喜《左传》而宗《糓梁》。或者宗元于此,别有会心也末可知。后人所论,也不过是凭一己之领会,各说其是罢了,谁又能确切知道柳宗元当初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而概括出这些一字精义的呢!
第六段是总收全文,回结前意。何焯批评“此等收法亦有迹”。然而诚如金人瑞《古文评注补正》卷七所说“此为恣意恣笔之文。恣意恣笔之文最忌直”,故自不妨多用转折以尽其恣,多用回环照顾以达其圆。若仅能方而少圆意,那就末免太刻板了。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表明了自己文学主张“文者以明道”。
阐释了为文的本源:“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判断力),本之《易》以求其动(变化),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子)、《荀》(子)以畅其文,参之《庄》(子)、《老》(子)以肆(放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司马迁)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可见,他认为必需善于吸取古代各种名著不同的特点和长处,加以融会贯通,才能自创一体。
申明了作文的态度:“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反映了他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韩、柳”并称,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确实与韩愈很相近,他们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少共同点:社会内容丰富,艺术技巧成熟,语言精炼。但是,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他们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还是有着不同的。至少,文章风格各异:韩愈擅长议论,文章雄浑奇崛,浩瀚奔放,具有“阳刚”之美。柳宗元擅长山水游记,文章峭洁精炼,笔锋细腻,幽深典雅,具有“阴柔”之美。这一点,大家在阅读时,不妨细细品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