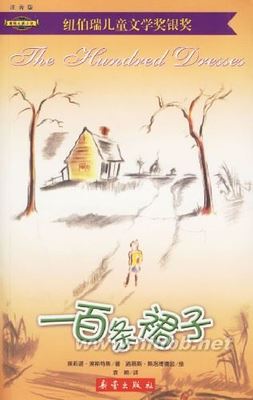《在酒楼上》新解
梁伟峰
从《呐喊·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铁屋子”的“万难破毁”报有“确信”,绝望于“铁屋”中人的前途;他又从自身经验范围的有限性出发,认识到他之必无希望的证明不能折服别人之所谓可有,至少逻辑上不能抹杀希望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听将令”“遵命”呐喊的动力。待到他的“彷徨”时期,新文化运动已经退潮,阵营已经分化,原初的启蒙者的“将令”已无形中被消解,再加上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婚姻方面的压抑、兄弟失和等因素,使得此时鲁迅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惑和思想痛苦之中。比之《呐喊》,《彷徨》淡化了“听将令”的色彩,而走向启蒙话语的边缘。《呐喊》中受到挤压的作者的“确信”和绝望,虽显得黑暗和虚无,但作为鲁迅此时期心理真实的一面终于在《彷徨》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与此相映照的是,鲁迅又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在否定希望的同时,又和绝望抗争。“反抗绝望”①是此时期鲁迅思想探索的依归。鲁迅最终超越了希望和绝望,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我们可以在《彷徨》中摸索到一条“反抗绝望”的思想斗争、探索的脉络,而《彷徨》本身就可视为鲁迅的“绝望”和“反抗绝望”两种意向和选择进行搏杀的战场。《野草》和《彷徨》一样,都映射出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内心矛盾和斗争,前者作为象征世界更清楚完整地熔炼进了鲁迅此时期的人格心理状态。作为基本上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野草》和《彷徨》具有生命体验上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我们进行彼此间的往返映证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样的往返映证,无疑对深入理解两者具体篇章大有裨益。以上认识,构成了解读《彷徨》中《在酒楼上》的两把钥匙。研究者们在分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时,对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确,大多认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时代反封建激进的战士”或民国初年的一位对辛亥革命失望的颓唐者。关于吕纬甫颓唐情绪的由来,有不能抵挡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和“对辛亥革命失望”两种解释。与此相应,在小说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问题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不同意见。两种结论虽相距甚远,却都不免有脱离作品实际之嫌——它们并不能从对小说的文本解读中得出。实际上,《在酒楼上》中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说文本并未向我们透露任何导致吕纬甫消沉、颓唐的具体历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异的两种结论,症结在于对外部社会印证式解读模式进行的粗糙操作。
把这些结论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作下确定不二的“解释”,不仅有胶柱鼓瑟之嫌,也大违作者本意。而这种粗糙的社会印证,只能妨碍对吕纬甫形象的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吕纬甫无疑曾扮演过中国近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又从感情炽热、斗志昂扬的改革中国的激进者变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沉静的颓唐者。他表面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下面,包容着一颗绝望而以虚无为实有的心灵。这种绝望、虚无的精神状态,被烙下深凹的鲁迅的人格印记,维系着鲁迅个体独特而充满悲剧性的精神体验。吕纬甫形象实际涵盖了此时期鲁迅思想态度的一个侧面。众所周知,“新生”杂志的流产曾给青年鲁迅以巨大的打击,使其感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无可措手;在寂寞、悲哀中他又自省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②他摆脱不了铁屋中人的身份,而只能在清醒中与别人一起等待死灭命运的到来。此种给定性使鲁迅顿感自己的启蒙意志和行为的无意义,在幽暗的现实生存的映衬下,他的理想和报负显出了虚无。这样,在对自身存在和行动的无意义进行的观照当中,“虚无”在鲁迅的个体经验中显得异常真实而可把握,它是对现实和自身感到绝望的必然产物。“新生”事件后的所见所闻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复辟事件等更只能加重鲁迅这种“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③的感觉。虽然“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④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绝望、虚无始终是他生存实感中的重要一面。它构成了吕纬甫形象的精神底蕴。“我”所遇见的吕纬甫,已不复“敏捷精悍”,不再有昂扬奋发的勇猛意气,其精神世界是取消了是非爱憎的意义和界限的虚无的荒原。“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的话正是对存在和行动意义的“无”之认识的表达。吕纬甫详细叙述的迁葬和送绒花两件“无聊的事”,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了其以“无”为“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孝敬、顺从父母是无条件的、不可选择的道德义务。蜷伏在母亲的爱和意志之下仍是吕纬甫不可改变的道德生存方式,但他的孝敬、顺从已经转化为“骗骗”母亲的意向。他遵母命迁葬、送花的行为实质便是以“无”为“有”。去迁连模样都记不清楚的小兄弟的坟时,他决然发出“掘开来”的命令,结果是:
……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踪影全无!
这既是小兄弟尸体的“无”,同时也象征着吕纬甫的行为意义的“无”、虚空,充满荒谬、讽刺的意味。虽则如此,他仍以虚无为实有,郑重完成迁葬的一切程序,以便“足够”去“骗骗”母亲。他又依母命买了剪绒花要送给阿顺,辗转来到故乡,而阿顺早已死去,送花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亦即是“无”。他还是将剪绒花托人塞给了阿顺的妹妹,虽然并不愿将花送她。“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吕纬甫又将虚空装饰成实有。同小兄弟尸体的“踪影全无”一样,阿顺的死也具有象征意义,指向和对应着对存在和行动意义的否定——虚无。鲁迅是有意以迁葬和送花两个事例来象征吕纬甫以虚无为实有的精神状态的。为小兄弟迁葬是鲁迅1919年实有经历;送花一节的后半也有生活中“事实的根据”,⑤而小说中它们又包含了虚构的成份,同生活原型有了距离。鲁迅四弟椿寿夭于6岁,鲁迅把这个细节在小说中处理成3岁,用意正如周作人所言“是为的说坟里什么也没有了的便利”;⑥是为以小兄弟尸体的“踪影全无”作为吕纬甫虚无、绝望的内心真实的象征标识设定依据。鲁迅又通过两朵剪绒花把吕纬甫和生活中一点“事实的根据”嫁结起来,属于“事实”的邻家少女的死在小说中同样象征了存在和行动意义的“无”。
小说中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离开故乡,到济南、太原,又辗转到故乡,这段历程被比作蜂子蝇子之类绕了个“小圈子”。“小圈子”还有另一重意义,它是吕纬甫怀着希望追寻人生理想和存在意义而又在绝望、虚无中回绕的心灵历程的象征。“小圈子”是一个从寻“梦”到心死的过程。关于作为“改革中国”的寻梦者、激进者的吕纬甫,研究者们往往引称他的“敏捷精悍”、“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三者,而很少对小说中吕纬甫自述的“旧日的梦的痕迹”加以注意。而这旧梦痕迹,却能使我们更贴近地窥察做事还未“敷敷衍衍”时的吕纬甫的精神世界。接到送绒花“差使”的时候,吕纬甫“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他对阿顺“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对这“意思”他说得很明白,就是甘以自己的苦痛来慰安顺姑对自己的希望;“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他的祈愿又何尝只向顺姑而发!这“意思”是启蒙者应有的意思,没有虚无、绝望的气味而焕发出炽热的生命热情。说明他具有人生理想和关怀;表现出不愿放弃理想,充满自信和希望而希求光明到来的心态。相对于此后的“敷敷衍衍”,这是迥异的另一种人生评价。正是凭借希望的力量,吕纬甫才有“敏捷精悍”的表现和行动。然而对于与“我”重逢时的吕纬甫而言,这些都已是“旧日的梦的痕迹”,因而“即刻”就“自笑”和“忘却”了它,将旧梦的一缕亮色驱出了虚无的荒原。不难看出,吕纬甫从寻梦到“忘却”,与鲁迅自己从青年的“慷慨激昂”到此后的“寂寞”⑦的心态转变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有鲁迅的那段苦涩的寻觅希望而不得的生命体验的折光。小说中吕纬甫的自述、自评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隽和清醒,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的自省自知的能力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鲁迅那一贯严于、善于自剖的精神特色。吕纬甫对自己心态和行为实质的清醒认识,正印证了“彷徨”时期鲁迅对一度存在其灵魂中的“黑暗与虚无”的体认是多么深透。吕纬甫虽对自己在虚无感中的沉沦拥有自觉,却又是甘于、安于他的以虚无为实有、“敷敷衍衍”的生存状态的。他承受着绝望,肯定着虚无。“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这便是他的态度,既有几丝无奈,更透露出精神获得的安宁。如何面对绝望和虚无可以说是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思想矛盾斗争的核心内容,也是鲁迅和笔下的吕纬甫形象的思想内涵上最根本的差异所在。鲁迅始终没有坠入绝望、虚无的深渊,他选择的是“反抗绝望”。作为鲁迅经过炼狱般的心灵痛苦后认定的生存方式和战斗方向,“反抗绝望”成为二十年代中期鲁迅许多散文、小说的话语[]的中心指向。
在《在酒楼上》中,“反抗绝望”的精神、意向主要通过“我”这个形象表现出来。“我”是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小说的叙述者。“我”的存在和叙述,使其与吕纬甫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张力。“我”是作为吕纬甫精神状态和思想道路的审视者、批评者存在的,这个形象较多地体现了鲁迅此时期精神世界中“反抗绝望”的一面,不仅带有某些鲁迅的影像,还被赋予了鲁迅的一种自我超越的意向。“我”与吕纬甫一样,也曾是个寻梦的激进的启蒙战斗者。他是吕纬甫的旧同事、旧同窗,曾一同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为救国救民而积极努力。但与吕纬甫重逢时,“我”的心绪却变得“懒散”、“索然”、消沉了,其意态泛出了灰色。他于深冬雪后,从北地到故乡,去寻访故旧,结果却使其意兴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徒增了身在故乡、却为“生客”的失落感受。“我”的叙述便在这种消沉、黯淡的情绪氛围中展开,也为下文表现心情颓唐、行动“迂缓”的吕纬甫作了铺垫。
与魏连殳的甘于、安于“敷敷衍衍”的生存状态不同,“我”虽缺少了原先那种昂扬的战斗意气,受着消沉情绪的侵袭,但始终对自己的“懒散”、消沉怀着不满与不安。当他看到废园中斗雪而开的茶花时,感觉它“愤怒而且傲慢”;逼视自己“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已对自己隐约感到不满和可鄙。与吕纬甫重逢,他的第一反应是:“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他是怀着愧怍和自责的心理的。吕纬甫虽也想到先前的朋友“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并无愧怍自责之意。吕纬甫预料自己“终于辜负”老朋友的希望,也想不到振作,已不是原先那个从慰安别人的希望的行动中自己也得到快乐的吕纬甫了。如果说“我”和吕纬甫这一对曾为希望而战的启蒙战士都产生了消沉、颓唐情绪,因而精神上具有了契合点的话,那么随着两人对话的展开,小说表现出的是两人的精神之间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张力;临窗共饮的老友彼此间距离愈来愈大。“我”心怀愧疚邀吕纬甫同坐,他踌躇之后方坐下来,“我”以为“奇”,感觉“悲伤”而“不快”,意识到彼此间已有了距离;一对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毫不客气”,点菜时却推让起来,彼此心中都横亘着距离感。吕纬甫充满自嘲地说自己如蜂子蝇子般绕了个小圈子,接着又对“我”说:“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此语颇具同病相怜的意味,他把“我”的从北地“甘心于远行”到故乡的行为实质也归纳为蜂蝇之类“绕了一点小圈子”。“我”却没有对此表示认同: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
我也似笑非笑的说。
如前所述,“小圈子”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在这里,承认自己绕圈子就等于把自己也归入了吕纬甫一类;承认战斗的意气已在自己身上彻底消泯;承认虚无、绝望对自己的占有。正如鲁迅究竟不能“肯定”“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样,落寞、消沉的“我”对自己是否像吕纬甫一样绕圈子的态度究意是不敢肯定。这已经在暗示“我”与吕纬甫在精神状态、自我评价上的差异。又如《彷徨》中《孤独者》中的“我”始终和魏连殳这样的“独头茧”中“孤独者”保持距离一样,“我”在这里也隐约透露了拒斥“小圈子”的精神历程、反抗虚无和绝望的意向。通过对吕纬甫的聆听与观察,“我”也以他为参照不停地反观自身,“反抗绝望”的意向逐渐显凸。他静静地听完最能反映吕纬甫精神内核的二件“无聊的事”的始末后,对吕纬甫的态度已有了变化,由起初面对他时的愧疚自责趋于责备和冷淡。“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两句问语透露出来的是责备而不是同情。“我”既如此,自然就不会和吕纬甫“同病相怜”或“相对唏嘘”。话已到此,看着吕纬甫的眼光“又消沉下去”,“我”对其便“没有话可说”,只有分手。我要卸去初时的懒散、自责的情绪负载,作出行动者的姿态。他主动结束谈话,“准备走”时问及吕纬甫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打算,这种一般性询问得到的是一切都模模胡胡,“什么也不知道”的回答,这应该说更坚定了“我”“走”——远离吕纬甫及其精神世界的心志。有些分析认为“我”始终对吕纬甫报有重新奋起的希冀,其实小说结尾“我”的“走”便能说明此时“我”对他已不存希冀。“我”的情绪在二人对话过程中消长变化,最后自信代替了自责,行动——“走”代替了“懒散”。而吕纬甫对此也报有理解:
堂馆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他表现得不再“谦虚”,不是因为彼此间消除了隔阂和距离,而是隔阂和距离已经太大的缘故。吕纬甫明了“我”从他身上看出了什么,因而明了“我”的“走”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而“我”对绝望虚无的否定正是从对吕纬甫的思想道路的思考和峻拒中得出的。“我”超越绝望、虚无的意向十分坚定,“走”——远离吕纬甫的行动已无可阻拦,沉沦在虚无绝望世界中的吕纬甫也便毋庸“谦虚”也无可“谦虚”。“我”终于和他相别,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解读《在酒楼上》,理解小说人物尤其是“我”,还离不开对小说中北方的“干雪”和南方故乡的“柔雪”象征意蕴的把握。
言及鲁迅笔下对雪的描写,我们不能不想起《野草》中的名篇《雪》,《雪》运用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其中“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都是象征物;鲁迅描绘的北雪的壮美和南雪的优美,寄寓了自己的不同情怀。1924年12月末北京接连两日下雪;12月31日的鲁迅日记里有“晴,大风吹雪盈空际”之语。研究者们往往据此认为对这次下雪情形的现实感受引发了鲁迅创作《雪》的冲动,孕育了《雪》中“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的意象描写。而常被忽略的是:《雪》的基本意象和意蕴都已被包含在作于11个月前的小说《在酒楼上》中了。无论是对“滋润”、“晶莹”的南雪和“粉一般干”“纷飞”的朔雪的描写,还是对南方雪野中山茶和梅树的描写,都与《雪》中出于一辙。重要的是,《在酒楼上》中对北雪和南雪的描写并非“不是什么象征的描写”,⑧相反,其承载着和《雪》中一致的象征意蕴,甚至获得了主题性象征的意义。它们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达八九次之多,“我”和吕纬甫的叙述中都反复出现对北地和南地、北雪和南雪的感觉、印象描述。纷飞的干雪和滋润的柔雪的对比、论争贯穿了小说始终。北雪和南雪的意象在小说中逐渐积累、展开其象征意义。《在酒楼上》中雪的意象反复出现,使我们明白它终有所指;它们的象征意义是直接指向小说反抗虚无、绝望的主题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小说的主题性的意象。小说叙述展开的过程,也就是“我”逐渐抖落心头“积雪”,远离吕纬甫的过程。一般认为,《雪》中“滋润美艳”的南雪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憧憬;“蓬勃奋飞”的北雪表现了作者在肃杀环境中战斗的情怀。需要强调的是,鲁迅对南雪的描写,是以带有梦幻色彩的故乡回忆的面目呈现的,它既是回忆,也是心象和幻影,是虚幻的真实,是对适于生存的童年生活的想象性回忆,寄寓了理想和希望。记忆的乌托邦注定找不到现实依据,“滋润美艳”的南雪堆成的雪人终于融化得“不知道算什么”,这样幻灭感便接踵而来。除《雪》而外,鲁迅其他一些取材于童年记忆的小说、散文如《故乡》、《社戏》、《好的故事》等都强烈流露出相同的幻灭情绪。这种幻灭既针对故乡,也针对理想、希望。幻灭的结果又并不等于绝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故乡》结尾的独白道出了“我”对此种幻灭的释然和由此作出的选择,即无所谓希望不希望,从而也无所谓幻想和绝望,只要有人走,自然就会有路。南雪虽滋润美艳却不能使人长久依恋而化去。在冬日无边的旷野上,仍是“永远如粉,如沙”的北雪在旋转升腾,显示生命力量。这里鲁迅没有止于幻灭,而是转向对北雪象征的孤独而不屈地战斗的品格的充满激情的歌颂;否定希望后,没有坠入绝望和无所为,而是选择了对黑暗进行韧性抗争的道路。
《雪》中是如此,《在酒楼上》中也是如此。如果说北地象征着严酷肃杀的现实环境,而南地是理想中的美好生存空间的象征物,那么,《在酒楼上》开首第一句“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就具有了象征性。“我”规避了北地严酷肃杀的氛围,向地处东南的故乡寻求美好而虚幻的故土记忆的影子,来取得情感的慰藉。但故乡的美好故事连碎影也未有留存,“我”感觉是一个“客子”。一人甫在楼头落座时,“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袒露出一种彷徨犹疑的心态——既想逃避对于黑暗现实进行的必然是孤独而艰辛的战斗,又感到作为理想和希望寄托的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和依恋之情在现实故乡中已找不到依归。《在酒楼上》中的“我”已在体验如前所述的那种渗透了作者悲剧性心理体验的对故乡和理想的双重幻灭,却还未获得重返战场、反抗绝望的勇气,带有虚无情绪。“我”通过与吕纬甫的交谈,认清吕纬甫的精神面目的同时,也以其为参照愈发不满、不安于自己的彷徨意态。同样是从北地回到故乡的吕纬甫的叙述中也有对故乡雪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的描述,但绝不含明显的感情色彩,因为甘于、安于虚无的精神状态必然取消了他对此的褒贬爱憎之意。正在吕纬甫絮絮讲述其送绒花的始末时,“我”却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这山茶树是“我”眼中的景象,也是反抗绝望、韧性的战斗人格的象征。花朵“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树已使初时的“我”感到了对自己的“蔑视”,此时又抖落性喜“依恋”、“著物不去”的南雪,傲然斗雪而立。山茶树抖落积雪,便换得了“树枝笔挺的伸直”的轻松,释然傲然地对抗那肃杀的铅色天空,它使人联想到《野草·秋夜》中“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枣树。它和《秋夜》中的枣树都是抖落希望,而又超越绝望,自信、洒脱、坚韧地抗争黑暗环境的战士的象征性写照。不难看出,小说插入的“我”对山茶树的这段描写与此时“我”的精神意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存在内在的契合关系。正如那株山茶对显露铮铮战士本色一般,“我”也抖落了心头的“积雪”,否定和超越了希望、绝望,以实际战斗行动“走”迎向寒风和雪片,隐没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注释:
①鲁迅《致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
②⑦鲁迅《呐喊·自序》。
③鲁迅《两地书·四》。
④鲁迅《野草·希望》。
⑤⑥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第297、2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⑧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关于〈雪〉》注释⑤,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5期。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