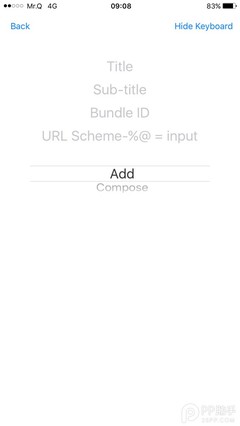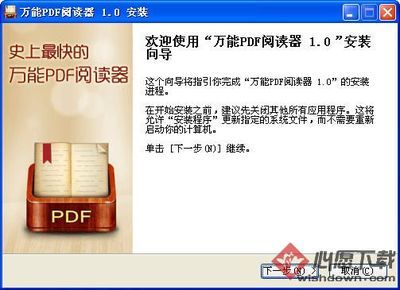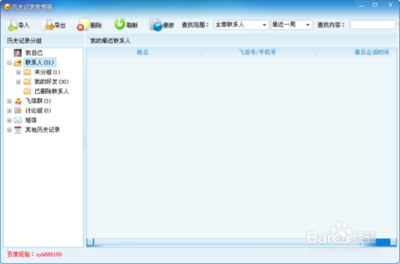阅读倒生根
一棵树,可不可以阅读?若可以,可不可以像阅读一本书?先三页五页地翻,再一页一页地搓;先一目十行地走,再一句一字地抠;先从后往前阅,再从前往后读……
比如,那棵榕树。普洱市。思茅区。振兴中路的倒生根公园。成林的独木。
貌似平静的泥土里:有多少根须四方穿越?只有树自己知道。
不知多高多远的天空中:巨大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能给起起落落的岁月多少呈堂的证词?只有树自己知道;无数御风往地面方向扎下的气根,有多少已被时间的风刀霜剑斩没?只有树自己知道;眼前几根擎天巨柱,经受了多少疼痛的折磨,经受了多少生死的考验,长成于哪一年?只有树自己知道……
也许,连树自己也没记下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
站在远处的楼头,遥望这棵盘在小土墩上的大榕树,就像隔着朦胧的玻璃窗,看见自家客厅里精致的盆景:美焕美伦,欲语还休……
不同的是,盆景不会有如此丰富,盆里的生命不会如此地蓬勃、强大。毕竟,盆景只是那些取巧的匠人,残削自然之足,去迎合那些背离了祖祖辈辈栖居的土地后,又附庸自然的风雅的人的履,换取自己所贪求的金钱。履,美其名曰“审美观”的三寸金莲,是美其名曰“贵族”的精神病人残酷工艺,为的是砍削自以为非的枝节。自家客厅里盆景,可任意看:翻来覆去、前后左右、远近上下……可以看清盆里所有的细节,甚至是匠人所有用心:梦幻与执着、多情与冷漠、付出与贪婪……
看这棵榕树,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榕树庞大生命里种种妙漫的细节,不是被距离模糊,就是被光线迷惑。每一个观察的角度,都只能见其微不足道的远离真实的点点滴滴。高了,脚下多了切不到实际的恐惧;低了,抵不住榕树身上那种霸掠肃杀之气的压迫;近了,只见独木成林的蓬勃,不见树相的仪态万方;远了,距离朦胧了渴望中应有的真切,只剩下命运中渺茫的感动和无由的悲伤……
遥望大榕树,遥想传说中的刘皇叔的小帝国。
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的诸葛孔明,率领蜀地精兵,像今天的美国大哥率领维和部队一样,来到这个今天叫普洱的地方,为普洱人的始祖主持四川先人的正义,传播四川先人的价值观。因为思念家乡的茅草和草房里的亲人,才有了这座城市曾经的名字——思茅;因为心怀千秋大业,才有这个土墩上枝繁叶茂、根茎横空的郁郁葱葱——成了林的独木。
遥望大榕树,像诵读八十年代的一首朦胧诗。感伤禁不住的梦,怨恨里游丝软系的感恩,顾爱左右而言他……无法准确地诠释诗里每个词语。无法界定每句话的主、谓、宾,定、状、补。无法想象诗人当年吟咏的颜容……说不出因为,不知道所以。读着几段分行的文字,自顾自地涕泪淋淋。手握一卷斑驳的诗篇,就可以把自己放逐到找不着北的暗夜里。
遥望大榕树,就像默读李清照的“生当为人杰”。企图忘掉项王的种种不是,为鲜血渲染的霸王别姬的美,感动得错天暗地。无缘无故:自己把自己美得乱七八糟;自己把自己伤得一塌糊涂;自己把自己牵挂得无所牵挂……多少年后才知道,那只是,歌者心里一个伤得不轻的春梦!
车流人流中。倒生根公园的路口。三路公交车近门的座位上。我把自己慌忙地溢出,气喘吁吁地拍上公园的石栏:
一棵树拉扯成的一片森林,就铺天盖地地展现在我头顶的天空。匆匆爬到树下,横看是一景、侧看也是一景,高看是一景、低看也是一景……
有了在思茅学习一个月的机会,就有了像读一本书一样读这棵树的计划。想反反复复地翻阅这棵树,想读懂这棵树:生命的成长与疼痛,理想的变异与坚守……
到一个月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做不到了!
我猜不出:一千八百多年以前,一粒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种子,是怎样萌发自己的生机?诸葛孔明和他的属下,又是怎样在荒山野林里寻寻觅觅?怎样在这个土墩上挖坑、扶苗、培土、浇水……
一千八百多年来,一棵势必长大的树。是怎样抵御了来往的寒暑?是怎样搏过风霜的刀剑?是怎样将生命勇敢地插入天空?多少的高度和深度?多少的过去和未来?多少的放弃和坚守?
无数随东风飘、被西风摇的须,是怎样在高空的树杆上破皮而出?又是怎样天女散花一样,在自己无所傍依的空中追寻别人的土地?几根须,最终怎样认他乡作故乡,凭空长成擎天巨柱?眼前无数的白须,哪一根会御风长成千年后擎天巨柱?
天空中欢呼状的枝叶:说过什么?说着什么?会说什么?
……一个匆匆的过客,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哪里我能开始?
九百多年以前,苏东坡在庐山“横看成林侧成峰”。我不知道:他是眼见为实,还是耳听为虚?眼见的,哪个方向射来的光亮?我不知道。耳,又是听着哪个方向吹来的风?我不知道。一棵树苗,是如何用一千八百多年的时间,长成一片原始的森林?我不知道。
树干上的伤:深深浅浅,像失了眸子的眼眶,是诗神缪斯断臂后愈合不了的疤痕么?是榕树多少年来的疼痛,多少年来的挣扎呵?树下,石桌上,几片落叶。黄黄的,明明暗暗的叶脉,是不是传说中的藏宝图?经纬交错的叶脉呵,谁能捋顺:那些参天的理想和归根的情结交织成的,暗含浅愁的生命流?
……巨大的树干上,数不清的根须间,缠绕着很多电线。树枝上,挂着钢筋焊成鸟笼,鸟笼上涂着暗红色的油漆。鸟笼里不关鸟,放养着城市的霓虹灯……这些,是我阅读中不愿意经历的章节。 一个过客,医治不了她的伤势,消除不了她的疼痛,就连选择忽略也是一种妄想!
人呵,人事呵,人生呵,常常,想弄巧,却成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呵,喧嚣的夜里,没有这些五颜六色的光线折射出的蜃楼,会不快乐吗?
我暗自喘了一口气。
原来,自认为是懂得一点东坡先生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在独木拉扯成的原始森林里,才知道,自己的阅读计划是登峰造极的虚妄。就这样吧,只能这样了——摸一摸树身上凹凸不平的皮肤,感受一下古树的生命——奋争与颓废、追寻与回忆、恩爱与怨恨、美丽与哀愁……
慢慢走下土墩,走在细细的流水之上,小小的桥,斜依回廊,倦收风物:小树;绿草;叠石;小小的湖;湖面上一朵若隐若现的睡莲,绿树、白楼、蓝天、彩云与荷的合影……
一个月来,对倒生根的第n遍阅读,草草收场。
……明天,就得回到我讨生活的山上,别人的土地上。
不服气!不服气……
中午,给春天打电话:“搭我课(去)补习一下倒生根,给得?”春天无私地支持,还提供了他最新的“百度”成果:榕树,有些地方又叫龙树,是龙上天必就的弯腰树。我突然想起,我出生的寨子也有龙树,也叫龙树。那个只有一姓人的寨子,已经连续七代无人登龙了……
我下课,春天下班。我挎上我家的一半家当,买了不久的单反相机,和春天一起奔赴倒生根。
榕树下,邂逅普洱学院驻校诗人泉溪一家。
一家三口正在演绎着,妙曼普洱养生天堂里的小甜蜜。悄悄一看,知道作为诗人的泉溪,正沉浸在家庭幸福的气氛中。这种气氛,由妻子的温柔贤淑和孩子的天真无邪复合而成。妻子抱着儿子,他正在逗儿子高兴。他那些云南一样的诗经,暂时退避三舍。
我打了招呼,说明来意。泉溪说:“妙!”就从家庭生活的庸常里,跳到诗歌的激昂和澎湃中。
他从包里翻出刚从作协取回的新杂志,放在石桌上。诗当酒茶。他的大学文学讲座,就在林里奔腾:从他的散文《倒生根记》到我正在阅读的倒生根,从生命的卑微到精神的追问,从生存的挣扎到诗意的人生,从普洱的妙漫到思茅的宜居,从养生的天堂到养心的佳苑……都与这棵榕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诗人的声音高着、低着、长着、短着……透过那些跳跃的词句的缝隙,我看见诗人的眼角,绽放着闪闪的泪花……
“……激动!激动!……打开文字的内核,让诗的意味徜徉进每颗爱心的海洋……”
用大芦山普通话,春天朗诵了我的《致泉溪》:
“当爱如涌泉
上天就注定了
你诗人的命运
华之西,云之南
茶之山,稻之水
那些辛苦的爱
成春风,成秋雨
成淡淡的雾,成浓浓的露
落了地,生了根
全是草儿花儿树儿的
血脉
“当泉汇成溪
吟咏就收获了
你辽阔的怀抱
云之雨,流之域
诗之经,爱之曲
那些望远的心
成花瓣,成轻舟
成孤独的旅人,成遥远的想念
用追寻来回忆
化苦恨为欢爱
寄希望于失望”
……
夕阳不解人意,不再光照我们的欢聚,不再光照我们路漫漫其修远的诗歌,不再光照我们止不住谈论的梦想,独自滑向西边的山顶。
诗人的儿子哭了几回,诗人的妻子说了几回,由轻而重:“儿子饿了。”
在附近的一家牛菜馆里,我们简单地打发了晚饭。顺便还喝了几瓶啤酒。差不多的时候,诗人的妻子说:“在城里混了很久很久,不敢想过,会有自己的房子。现在终于稳定了一些,按揭了一套小房子。虽然,小得害羞,但毕竟是自己的。给了我们多一些的家的感觉。以后你上思茅,就可以在我家里挤一挤了。接下来的酒,回家喝吧!”
那天晚上,我和春天,一起去了泉溪的家。对他的乔迁之喜,道了那声迟迟的贺:以诗歌做客思茅二十多年后,终于不再思茅,
不——
再——
思——
茅——
终于成了思茅的居民!
思茅的倒生根公园。那棵拉扯成原始森林的独木。那棵别名龙树的榕树。
会给我们更强大的力量:让普洱更加妙曼!
会给我们更高超的智慧,让思茅更加宜居!
会!一定会!
我相信。坚信!
(《一棵树的森林》修改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