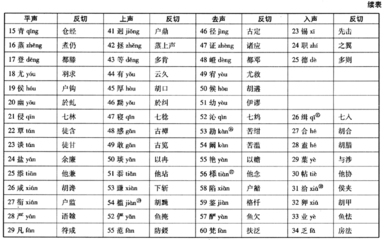笔法记
五代·荆浩
一原文
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钲山四望,回迹入大岩扉,苔径露水,怪石祥烟,疾进其处,皆古松也。中独围大者,皮老苍藓,翔鳞乘空,蟠虬之势,欲附云汉。成林者爽气重荣,不能者抱节自屈,或回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盘溪,披苔裂石。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明年春,来于石鼓岩间,遇一叟,因问,具以其来所由而答之。
叟曰:“子知笔法乎?”曰:“叟仪形野人也,岂知笔法耶?”叟曰:“子岂知我所怀耶?”闻而惭骇。曰:“少年好学,终可成也。”“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谢曰:“故知书画者,名贤之所学也。耕生知其非本,玩笔取与,终无所成,惭惠受要,定画不能。”
叟曰:“嗜欲者,生之贼也。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子既亲善,但期终始所学,勿为进退。图画之要,与子备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复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妙者,思经天地,万类性情,文理合仪,品物流笔。奇者,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乖异,致其理偏,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
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故知墨大质者失其体,色微者败正气,筋死者无肉,迹断者无筋,苟媚者无骨。
夫病者二:一曰无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时,屋小人大,或树高于山,桥不登于岸,可度形之类也。是如此之病,不可改图。无形之病,气韵俱泯,物象全乖,笔墨虽行,类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删修。
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为生,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势既独高,枝低复偃,倒挂未坠于地下,分层似叠于林间,如君子之德风也。有画如飞龙蟠虬,狂生枝叶者,非松之气韵也。柏之生也,动而多屈,繁而不华,捧节有章,文转随日,叶如结线,枝似衣麻。有画如蛇如素,心虚逆转,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栎榆柳桑槐,形质皆异,其如远思即合一一分明也。
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顶,圆曰峦,相连曰岭,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间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夹水曰涧。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掩映林泉,依希远近。夫画山水无此象,亦非也。有画流水,下笔多狂,文如断线,无片浪高低者,亦非也。夫雾云烟霭,轻重有时,势或因风,象皆不定。须去其繁章,采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然后受其笔法。”
曰:“自古学人,孰为备矣?”叟曰:“得之者少。谢赫品陆之为胜,今已难遇亲踪。张僧繇所遗之图,甚亏其理。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吾唐代。故张璪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麯庭与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虽巧而华,大亏墨彩。项容山人树石顽涩,稜角无踪,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然于放逸不失元真气象,元大创巧媚。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树不言图,亦恨无墨。陈员外及僧道芬以下,粗升凡格,作用无奇,笔墨之行,甚有形迹。今示子之径,不能备词。”
遂取前写者异松图呈之。叟曰:“肉笔无法,筋骨皆不相转,异松何之能用?我既教子笔法。”乃赍素数幅,命对而写之。叟曰:“尔之手,我之心,吾闻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为吾言咏之乎?”谢曰:“乃知教化,圣贤之职也,禄与不禄,而不能去,善恶之迹,感而应之。诱进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赞曰:
“不凋不容,惟彼贞松。势高而险,屈节以恭。叶张翠盖,枝盘赤龙。下有蔓草,幽阴蒙茸。如何得生,势近云峰。仰其擢干,偃举千重。巍巍溪中,翠晕烟笼。奇枝倒挂,徘徊变通。下接凡木,和而不同。以贵诗赋,君子之风。风清匪歇,幽音凝空。”
叟嗟异久之,曰:“愿子勤之,可忘笔墨而有真景。吾之所居,即石鼓岩间,所字曰石鼓岩子也。”曰:“愿从侍之。”叟曰:“不必然也。”遂亟辞而去。别日访之而无踪。后习其笔术,尝重所传,今遂修集,以为图画之轨辙耳。
二 全译
太行山有个叫洪谷的地方,其间有田数亩,我曾经在此耕而食之。一天,登上神钲山四下观望,迂回曲折的山路通入大岩山口,长满苔藓的石径全是露水,怪异的石头与祥瑞的雾霭,我快速走了进去,到处都是古松。中间有一株数围(两臂合抱的长度单位)那么大的,老皮上长满青色苔藓,松鳞飞翔凌空,枝干盘曲而上之势,想要攀附云霄。成林的,气象明朗,欣欣向荣;不能成林的,环抱树节自行屈曲。有的根回旋着露出地面,有的偃卧截断巨流,悬挂在崖岸,盘曲在溪上,披着苔藓,挤裂顽石。我对它们的奇特感到惊异,因而四面仔细观赏之。第二天带上画笔又靠近它们描绘,共计画了数万幅,才画得与他们的自然形貌相像。第二年春天,我再次来到石鼓岩间(作画),遇到一位老者,因为他问,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
老者问:“您知道绘画的用笔方法吗?”我说:“老人家,您仪容形貌看起来像个野人,难道也知道笔法呀?”老者说:“您哪里知道我的胸怀呢?”我一听这话,感到惭愧震惊。老者宽慰我说:“少年只要好学,终究是可以成功的。绘画有六个要点:一叫气,二叫韵,三叫思,四叫景,五叫笔,六叫墨。”我说:“画就是华丽,无非要画得像与真实,哪有这么多的名堂呢?”老者说:“不是这样,画是描绘出来,即测度物象而描绘出它的真实。物象华丽,就描绘出它的华丽,物象质朴,就描绘出它的质朴,(各归其类),而不能把华丽当作质朴。如果不知道描绘技巧,只能勉强得到形似,不可能描绘出物象的真实。”我问:“如何为似,如何为真?”老者答:“似就是只得到了物象的形质,而遗失了它的神气;真就是神气与形质均旺盛。但凡神气只传达到物象的表面,而没有传到物象内部,物象就是死的。”我道谢说:“书画本来是名流贤达所学的,我知道的不是根本,只不过玩玩笔墨而已,终究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不是因惭愧而承蒙您指授要领,一定不能画出好画来。”
老者说:“欲望是人生的祸患,名流贤达即便爱好琴书图画,也只不过是用它们去除杂欲。您既然有亲近良善之心,只希望能自始至终坚持学习,不要犹豫徘徊。图画的要领,与您详说吧:‘气’就是笔要顺随心的运行,摄取物象不犹豫迷惑。‘韵’就是不露笔墨痕迹地塑造形象,具备高雅不俗的仪容。‘思’就是要提炼、取舍,概括要点,凝神遐想形状、物象。‘景’就是要根据季节、气候变化来剪裁、忖度景物,搜罗美妙素材,创作出真实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笔’就是虽然应依照一定的法则,但运转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不拘泥于物象形质,而如飞如动。‘墨’就是要根据物象的高低(凸凹)晕染墨色,根据品味到的物象(色相浅深)来傅以不同浅深的墨色,使画面物象的纹理、色彩自然而真实,仿佛不是用画笔描绘出来的。”又说:“神、妙、奇、巧,‘神’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任由笔墨运行,塑造出艺术形象。‘妙’就是心思经天纬地,表现出万物各自的性情,纹理合乎物象的自然生长规律,将品味到的物象以流畅的笔墨表现出来。‘奇’就是纵放的笔迹难以揣测、忖度,有时与真实景致或许有乖离、差异,以至在画理上讲不通,画成这样也就是有笔迹无构思了。‘巧’就是雕琢装饰小的妩媚,表面上看起来合乎常规,勉强描绘物象纹理,无谓增加与描摹物象气度。这就叫做质朴不足而华丽有余。
大凡笔有四势,叫做筋、肉、骨、势。笔迹断绝而笔意不断的叫做‘筋’,笔迹起伏力量充实富有弹性的叫做‘肉’,笔迹方正刚直的叫做‘骨’,笔迹流畅利落而没有败笔的叫做‘气’。因而知道运笔时墨太质实了就会丧失物象之形体(按:“大”一本作“太”),色微弱了就会败坏物象之神气(按:“正”疑为“其”之误),筋脉僵死肌肉就会没有生机,笔意断绝就会没有筋脉,苟且谄媚就会没有骨力。
“毛病有两种:一是无形的,二是有形的。有形的毛病,花木不合时节,屋舍比人还大,或者树比山高,桥没搭在岸上,都是可以从形象上看出来的毛病,如果是这些毛病,还可以修改(按:“不”当为“尚”)。无形的毛病,气韵全没有,物象都乖异,笔墨虽在运行,却像是死物,格调如此拙劣,不可删削修改。
“您既然喜欢描绘云烟、林木、山水,就一定要明白物象的根源。林木之所以生长,是因为禀受了它自己的本性。松树的生长,不屈服于所遇到的枉滥,或密集或稀疏,既青绿又翠蓝,从小就自然端直,开始萌芽时就志在凌云。气势独立高昂时,枝条却压低而偃卧,呈倒挂而未坠于地之势,层叠在林木之间,道德风范犹如彬彬君子。如果把松画得像飞龙般虬曲盘旋,枝叶胡乱生长,便不是松的气韵了。柏树的生长,动辄多屈曲,繁密而不华丽,托举树节有条理,纹理顺随太阳扭转。叶如连结的线,枝像披着的麻。如果把柏树画得如蛟龙像绳索(按:“素”疑为“索”之误),中心虚弱而逆着太阳旋转,也是不对的。林木中的楸、桐、椿、栎、榆、柳、桑、槐,形质都不一样,如能从深远处思考它们的本性,就能够将它们一一分明地描绘出来。
山水的景象,气势互相生发。因而山顶尖的叫峰,平的叫顶,圆的叫峦,山与山相连的叫岭,有洞穴的叫岫,壁立峻峭的叫崖,崖间崖下叫岩。有路通到山中的叫谷,不通的叫峪,峪中有水流的叫溪,两山夹水的叫涧。山的上半部分峰峦虽不相同,山的下半部分却冈岭相连。林泉掩映,隐约显出远近。如果画山水没有这种景象,也就不对了。如果画流水,下笔狂乱,画水纹如断线,没有一片浪花表现出高低起伏,也是不对的。雾云烟霭,轻重因时节而变化,形势有时因风向而不同,景象皆不固定。必须去掉繁复的表面纹彩,撷取主旨要点。先要明白这些道理是非,再落墨作画。”
我问:“自古以来的学画者,谁为完备呢?”老者说:“得到这些的少。谢赫品评陆探微为优胜,今已难见到他的真迹。张僧繇遗留下来的画作,画理甚为亏欠。根据不同物类而傅以相应色彩,自古以来,能者不绝。而水墨画是在我们唐代兴盛起来的,所以张璪员外所画树石气韵都很旺盛,笔墨从细微处积累起来,思虑真切而卓越,不以五彩为贵,旷古绝今,从未有过。麯庭和白云尊师气度幽深微妙,均得到了水墨画理之本源,作画动辄超逸常规,深不可测。王右丞(维)笔墨宛转清丽,气韵高雅清秀,描写物象巧妙,思虑也很真切。李将军(思训)画理深微思虑悠远,笔迹很是精妙,虽巧妙华丽,却大亏墨彩。项容山人所画树石枯硬呆滞,多棱角而不着迹象,用墨独得玄妙法门,用笔全无骨力,然而在豪放纵逸中却不失玄妙气象,开始大大地创新了巧媚一路画风。吴道子笔法胜过物象,骨法气韵自然而高妙,描绘树木谈不上好,也遗憾没有墨法。陈员外及僧人道芬以下,虽粗略算起来也能达到一般水平,但没有新奇作为,笔墨运行甚着痕迹。今天只能指示您作画路径,不能详细阐述。”
于是我取出以前画的《异松图》呈献给他。老者说:“用笔肥而无力,没有法度,骨力气脉均不能相互起承转合,这样的笔法怎么能用来表现异松呢?我即教您笔法。”于是拿出随身带着的绢素数幅,令我对着松树作画。老者说:“你的手,我的心,我听说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谈就能知道他的操守品行’,您能与我言谈吟唱它吗?”我答谢道:“现在终于明白了教育感化是圣贤的职业,做不做官都不应该丢开,(只要给予了合适的教化),画迹无论好坏都会有所感应。您对我诱导如此,我怎敢不恭敬顺从?”因而作成《古松赞》道:
不凋谢不容饰,惟有贞洁之松。气势高耸而险峻,降低身分敬相从。针叶张开如翠绿华盖,枝桠盘曲似赤色蛟龙。树下生有蔓草,幽静阴凉蓬松。如何得生长?气势近云端。仰望挺拔树干,举起千重枝桠。巍峨倒映溪流中,翠色晕染如烟笼。奇异枝条倒挂着,回环屈伸富变通。下与寻常林木接,和睦相处不附和。诗赋以你为贵,因有君子之风。清风吹拂不停,幽音凝集空中。
老者感叹惊异了很久,说:“愿您勤奋学习,可以达到忘掉笔墨而有真景的极致境界。我居住的地方,即石鼓岩间,我的字号就叫石鼓岩子。”我说:“愿意跟随侍奉您。”老者说:“不必这样了。”于是急忙辞别而去。他日再来寻访却找不到踪迹了。后来学习他教的笔法技巧,曾经重视他所传授的,如今将之编纂成集,以作为图画的规范。
三解读
荆浩,五代后梁画家,约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约卒于梁乾化二年(912)至梁龙德三年(923)间,河东道泽州府沁水县(今山西晋城市沁水县)人(袁有根《解读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荆浩》),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博雅好古。遇五季多故,遂退藏不仕,乃隐于太行山之洪谷,耕而食之,自号洪谷子。善画佛像、人物、山水、树石,以山水树石专门名家。强调师古而化,尝语人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曾于京师双林院画《宝陁落伽山观自在菩萨》一壁;北宋宣和御府所藏荆浩《秋景渔父图》三、《山阴燕兰亭图》三、《写楚襄王遇神女图》四共十幅(《宣和画谱》)当为人物画或人物兼山水画,惜荆浩人物画今已不存。荆浩隐居后,多以画山水树石自适,颇得趣向。邺都青莲寺沙门大愚曾乞画于浩,寄诗以达其意云:“六幅故牢建,知君瓷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后浩亦画《山水图》以贻大愚,仍以诗答之曰:“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荆浩与友人诗画酬唱、诗文与水墨山水画境界由此不难概见。北宋绘画史论家刘道醇曾在供奉李公家见过荆浩《山水》一轴,评云:“虽前辈未易过也”;郭若虚见过荆浩《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等山水图;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1002-1060)见过荆浩《山水图》;宣和御府则藏有荆浩十二幅山水画。荆浩山水画现存《匡庐图》轴(袁有根认为图名当为《太行山居图》,绢本水墨,纵185.8厘米、横106.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另有(传)荆浩《雪景山水图》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钟离仿道图》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秋山瑞霭图》轴(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藏)、《渔乐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存世。
荆浩山水画成就与影响均极大,后世尊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跱,百代标程。”而关仝师事荆浩,李成师法荆、关,范宽师法李成、荆、关,梅尧臣有诗赞曰:“范宽到老学未足,李成但得平远工。”其后“翟(院深)学李,刘(永)学关,纪(真)学范。……复有王士元、王端、燕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讷之流,或有一体,或具体而微,或预造堂室,或各开户牖,皆可称尚。”郭熙虽对当时齐鲁、关陕州州县县蹈袭曾师法荆浩的李成、范宽甚为不满:“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一己之学犹为蹈袭,况齐鲁、关陕幅员数千里,州州县县人人学之哉!”(《林泉高致·山水训》)自己却要学李成。荆、关、李、范、许、郭在南宋、金代的影响仍不小,“南宋四家”(李、刘、马、夏)虽多所突破,但源出荆浩,如元倪云林说:“盖李唐者,其源出于范、荆之间,夏珪、马远辈又法李唐,故其形模如此”;金代元好问《元遗山集》云:“余家所藏……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熙笔老而不衰……(刘)尊师爱画山水,晚得郭熙平远四幅,爱而学之,自是画笔大进。”元代山水画以承接发扬董、巨一系的“元四家”(黄、王、倪、吴)为著,自不待言,但即便如此,李、郭一系在元中后期也不乏传人,如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姚彦卿、刘伯希等均为佼佼者。如此等等,难以遍举。
荆浩善于山水画理论思考,撰有《笔法记》(一名《山水笔法记》,又名《山水受笔法》、《山水诀》、《画山水录》)一卷等,当时即知名,为友人表进,藏之书府(或秘阁),流传至今。阅读《笔法记》时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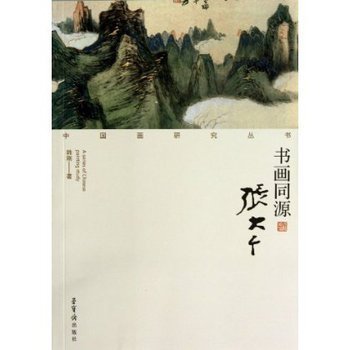
其一,《笔法记》曾一度被认为属后世伪托或真伪掺杂,如《四库提要》云:“依托为之,非其本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九《伪托类》云:“似非全部伪托,疑原书残帜,后人附益为之者。”但后来学者基本上颠覆了上述观点,如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说:“岂可直断为伪书?”王伯敏《笔法记译注》亦认为非伪托;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说:“现可断言,是篇确实为荆浩所撰”;等等,因而,非伪托论点逐渐成了主流,学界开始重视此书,绘画史、美术史论著述、论文、教材开始研究、引用、讲授此书。可近年来,韦宾却在《唐朝画论考释》中再次论证《笔法记》当属伪托,“把一潭本来已经澄清了的水又搅浑了”,韦宾的观点随即遭到了袁有根《解读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荆浩》的驳难,维持了非伪托论点。笔者认为荆浩《笔法记》非伪托。
其二,《笔法记》著录于北宋《崇文总目》卷三、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郑樵《通志·文艺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元代脱脱等《宋史·艺文志》卷六等处,“所记书名虽略有不同,但确为一书,无可置疑。”(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该书现存较早完整版本是明代翻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刻本(上海画院藏),宋元以后,各种刊刻本层出不穷,如《王氏书画苑》本、《四库全书》本、《美术丛书》本、《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本等。
其三,荆浩“业儒,博通经史”,所以《笔法记》思想主旨归宗儒家,如:“乃知教化圣贤之职也,禄与不禄而不能去,善恶之迹感而应之”;以“贞松”拟“君子之德风”等。
其四,《笔法记》是承接并发扬盛唐王维《山水诀》,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逸品三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卷十王维与张璪小传等处水墨山水画论而来的,实际上是一篇水墨山水画专论。如王维云“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朱景玄述论王墨“泼墨”,张彦远论“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与“破墨”等,而荆浩在《笔法记》中不但提出“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按:有论者认为“笔墨积微”即积墨法),而且对王维、张璪等唐代实践水墨山水画者进行了一一评论。
其五,《笔法记》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新性的水墨山水画理论,如“六要”、“四品”、“图真”、“二病”、“笔有四势”、“须明物象之原”、“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水晕墨章,兴吾唐代”、“忘笔墨而有真景”等,此外,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画论术语,如“理”、“迹”、“病”等,显示了荆浩卓绝的理论概括能力与素养,对后世山水画论(如宋郭熙《林泉高致》、韩拙《山水纯全集》、明唐志契《绘事微言》等)影响巨大。今择其要者述于下:
(一)、荆浩《笔法记》提出“六要”(即一气、二韵、三思、四景、五笔、六墨)并一一作了阐释,这既有得于谢赫“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之启发,又是对它合乎时宜的创新性转化,即将主要论画人物的“六法”转化成了论画水墨山水的“六要”,功莫大焉!其中“气”大致相当于“气韵生动”,“思”相当于“经营位置”,“景”相当于“应物象形”,“笔”相当于“骨法用笔”。荆浩汰除了谢赫第六法“传移模写”,原因大概如《历代名画记》所云:“至于传移模写,乃画家末事”;增加了第二要“韵”(按:此“韵”与“水晕墨章”之“晕”通,主要指画法上用水破墨晕染,以营造立体空间与渐远渐淡意象,属于“形而下者”,而谢赫“气韵”之“韵”则当属“形而上者”,两者大不相同,需要注意);而以第六要“墨”置换谢赫“六法”之四“随类赋彩”,凸显了晚唐五代水墨山水之特点及理论述求。顺便提一句,荆浩对“气”的解释“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需要注意,韩拙《山水纯全集》、韦宾《唐朝画论考释》、袁有根《解读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荆浩》对此的引用与解释均有不同。笔者更倾向于赞同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所说:“若易之为‘笔随心运’似更妥。”
(二)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了“二病”(有形、无形)说。“无形病”大多涉及山水画比例透视问题,而这是自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以来一直强调,至盛唐王维时代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晚唐五代如果有画家还在这上面出错,当然就是“病”了,因为这种“病”前人已经积累了医治的办法,所以“尚可改图”。而“无形病”之所以“不可删修”是因为自古及今从来就没有找到具有普适性、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虽然后来的董其昌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大千提出了“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等解决“无形病”之道,但用之于他人,效果却并不一定理想,因为除了他们本人之外,很少听说有哪位画家因为实践这些办法而成功的,或许这就是非人力可为的人类艺术之宿命吧!
(三)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四品”(即神、妙、奇、巧)并一一阐释,这应是直接针对朱景玄两系“四品”论(神、妙、能,逸)的创新性转化,就朱景玄对“逸”与荆浩对“奇”的解释来看,二者是相通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朱景玄放在“神、妙、能”一系之外的“逸”(或“奇”)被荆浩纳入此系之内,排在第三位,组成了“神、妙、奇(即逸)、巧”序列。凸显出五代荆浩时代与晚唐朱景玄时代相比,“逸”(或“奇”)品绘画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宋初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更进一步,直接将“逸”排在了最前面,而成“逸”、“神”、“妙”、“能”序列。
(四)荆浩《笔法记》提出水墨山水画笔法“四势”(即筋、肉、骨、气),也是对前此人物画用笔法的承接与改造,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顾陆张吴用笔》有云:“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巨壮诡怪,肤脉连结”,“笔不周而意周”,荆浩则把它概括发扬为:“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筋死者无肉,迹断者无筋,苟媚者无骨。”
(五)荆浩《笔法记》提出“须明物象之原”论,实际上是对盛唐王维《山水论》、《山水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等阐述的画山水树石实践的理论概括、发扬与深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描绘林木等物象应遵循其内部的自然生长规律,如《山水论》所云“有叶者枝嫩柔,无叶者枝硬劲。松皮如鳞,柏皮缠身。生土上者根长而茎直,生石上者拳曲伶仃。古木节多而半死,寒林扶疏而萧森”等仅止于描绘现象,而《笔法记》则先是进一步以“夫木之为生,为受其性”指出现象之后的本体,尔后以松、柏为例详细阐释;二是云林山水等物象会随环境、季节、气候等外部条件之改变而形态不同,描绘方法也应该随之改变等,如《山水论》云:“有风无雨,只看树枝。有雨无风,树头低压”等,《笔法记》则云:“夫雾云烟霭,轻重有时,势或因风,象皆不定。”如此之类,不难见出,王维与荆浩相比,后者所论更具理论思辨的深刻性,而这又是与人类从现象描述到理论概括的认知规律一致的。
(六)荆浩《笔法记》在“山水之象,气势相生”论中述及的山水画构件(如峰、顶、峦、岭、岫、崖、岩、谷、峪、溪、涧等)承接自盛唐王维《山水论》等而有变化,表现在汰除(如巅、川、壑、陵、坂等)、新增(如顶、峪、溪等)等方面,之所以有这些变化,盖因为王维所居之终南山、辋川一带与荆浩隐居的太行山洪谷等处自然山川地貌的不同,比如《笔法记》中所谓“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掩映林泉,依希远近”云云,如果没到过太行山是很难理解的,而一到太行山就什么都明白啦。(该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2013年1月23日、26日第5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