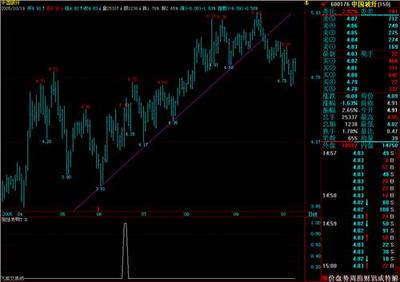家父的短文一篇,留存
忆老苏头
文/汤永文
老汉我今年69岁。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大家人在伙里一起过,没有分家,家里共有十多口人。我们家对面屋,住着一对从山东家过来的夫妻。我习惯性叫男的为老苏头,女的叫老苏太,尽管那时候他们还不是老人。他们夫妻操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听着不太习惯。因为是外乡人,他们和街坊很少来往。与我们家相对来往多一点,一来住的近,二来毕竟我家祖上也是山东的。亲不亲,故乡人嘛。
老苏头夫妻二人生活非常简朴。记得一天晚饭后,我去他们家玩耍。当时天已经很黑了,没有月亮。在外屋地,我听见从他们的堂屋发出一种奇怪的、吸溜吸溜声音,却啥也看不见。因为屋子里没有点灯。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电,家家都用火油灯。我吓得转身要跑,老苏头听出来是我,就喊,永文,进来耍,并点了灯。原来他们是在吃饭,喝苞米稀粥,也没有菜。我说吃饭怎么不点灯,能看见吗?老苏头说,都吃到嘴里了,一口也没吃到鼻子里。
关于吃饭,老苏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一次,一个亲属不远千里来看他们夫妻。亲属来了,吃点好的吧。吃啥?面条。那时候面金贵啊。面条下好了,端上桌。老苏太没有上桌,这是老礼。老苏头陪客。老苏头急三火四把一碗面条扒拉到肚子里去,连汤汁也喝得一滴不剩,把筷子碗上”啪“一搁,摸摸肚皮对客人说,你慢用,我饱了。客人说,才吃一碗就饱了?老苏头大声回话说,吃一碗还不饱,那不成了饭桶了?客人无言以对,吃完一碗面条,只得放下筷子,也说饱了。面条总共就三碗,剩下一碗,被老苏太吃了。
还记得一年除夕,放完鞭炮发完纸后,我到他们家拜年。在他们家门口,还没进屋,我听见老苏头说,老伴,你过年好哇。又听到老苏太回话,老伴,你过年好哇。夫妻互相拜年,我是第一次见。
关于老苏头为何从山东来到我们这地方,我问过奶奶。奶奶说,老苏头,本名苏来恩,在山东时,不务正业,不种地,他们两口子以讨饭为生。大概在解放前十几年,才流窜到辽南,还是讨饭为生。后来在咱们屯落脚。你爷爷见他们可怜,把两间旧屋腾空给他们住。可是老苏头不定性,住了不长时间,决意要到外地讨饭,并做出一个不合常理的决定,要把老苏太卖给本屯的张大为妻。老苏太百般不肯,老苏头就打她。众人劝阻也不好使。山东人倔啊。老苏太见老苏头如此绝情,就停止哭闹,问老苏头,你真不要我了吗?老苏头说,嗯。老苏太说,那么你张口,我吐一口痰到你口里,你吃了,咱们就恩 断义绝。老苏头说好。老苏太一口痰吐到老苏头嘴里,老苏头吞了,拿着卖妻的钱,头也不回地向北走了。老苏太大哭,背过气去。老苏太后来跟张大一起过。张大有个弟弟张二,也没有媳妇。第二年,老苏太生下一女,叫张程程。程程三岁那年,张大得暴病死了。经人撮合,迫于生计,老苏太又嫁给了张二。和张二结婚两年后,张二也病死。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苦不堪言,只能讨饭活命。解放后,老苏头从北方回来了,要求与老苏太复合。老苏太开始不肯,经不住老苏头一根筋地磨,还是同意复合。
合作社以后,老苏太就去世了。程程成年后,嫁到邻村赫家沟。由于老苏头没人照顾,程程和丈夫隔年又回来和老苏头一起过。可惜,几年后程程也因病而去,程程的丈夫抱孩子回了老家。于是老苏头就成了孤家寡人。
老苏头后来成了村里的五保户,为生产队看苹果场。由于以前的关系,我经常去他在果场里的小屋坐坐。他的小屋矮小逼仄,墙上全是泛黄的旧报纸,一股老朽的味道和苹果的香味混杂在一起。我刚学会拉胡琴,老苏头就说,永文,你拉一个,我唱两句。我就拉,他就唱:“悔不该,当初错斩了郑贤弟......”唱得沙哑而凄凉。偶尔,老苏头也能吃上一盘炒鸡蛋,吃不完就倒掉,从来不给别人吃,说是剩菜给人不礼貌。那时候谁家能吃上小葱炒鸡蛋,全屯子都闻得到香味。馋人啊,直流吃水(哈喇子)。我看见就说大爷的生活不错啊。老苏头说,永文,饭菜再好,没有滋味啊。
文革期间,一个冬天,苹果场空了。老苏头死在自己的小屋里,三天后才被人发现。一大群麻雀从敞开的门呼啦啦飞出去,消失于灰蒙蒙的的天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