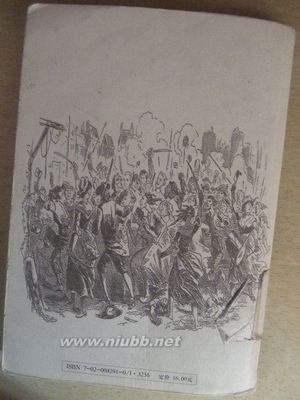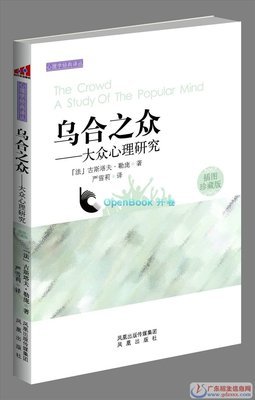看完《2666》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很不幸,这不是一本看完就把它为忘在脑后的书,按照以往的习惯,看完一本书总要写出点什么东西来。《2666》这本书早就如雷贯耳,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各种你能想到的赞美之词,书腰上甚至打出了“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虽然这上面的话不能真信,但是至少可以说波拉尼奥是和马尔克斯同一个级别的作家,新一代的大师。
在这么多赞美的铺垫下去看这本书,就像去看梵高的画,当时被很多人看成垃圾一般的东西,现在人人都想跑去看一眼。征服观众不是那幅画本身,而是关于那幅画的评论。当看完《2666》的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时,开始怀疑难道这就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叙事方式确实很独特,很多段落把他一行一行的写下来就像一首诗。语言不是衡量一部小说重要标准,你可以用很华丽的语句写,你可以用很粗俗的话来写,你可以用白话文来写,你可以用文言文来写,你可以用诗一样的句子来写。看完《文学评论家》,让人摸不到头脑,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像是讽刺,但又不像,看不到作者明确的态度,只是写一写文学评论家的生活,你怎么看那是你的事。你可以认为他们虚伪,道德败坏,你也可以认为他们做的也没什么错的。像是在替人调查报告一样,只负责给上级报告他做了什么事。
而到了《罪行》这一部分,甚至将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你甚至都替作者担心。好像你拿在手上的不是小说,而是警察局里面调出来的档案。随便列举一段“1月15日又发现一具女尸,她名字叫克劳迪亚.佩雷斯.米阳。发现尸体的地点是萨化丽托斯大街。死者身穿黑色毛衫,每只手上都戴着人造宝石戒指,此外还带着结婚戒指。没有裙子,没穿内裤;但脚上有人造革红色平底鞋。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尸体裹着红色摊子,好像凶手移尸外地,而突然决定(也许是环境所迫)把尸体仍在了萨化丽托斯大街的垃圾桶里。”作者就把这样的报告一段一段的重复了几百次,中间偶尔穿插一些当地警察的故事,竟然写了三百多页。当地警察对这样的事见怪不怪,每个月都有几个女人被奸杀,警察也不尽力破案,偶尔抓到个替死鬼,把所有责任都向他身上推。但是,你发现好像连你自己也不能对那些麻木的警察进行什么道德评价,骂他们混蛋。麻木的不只是当地警察,当你看了几百段这样的描述后你也麻木了,甚至懒得仔细把它看完。 如果说你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描写,第一反应是:太残忍了,一定要严惩凶手。但是当你一连看了几百段这样的描写后你的反应是:哦,又死了一个。作者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告诉你,在那些该千刀万剐家伙的身上的肮脏的东西,其实你身上都有。不是几个混蛋就能让世界陷入混沌,堕落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虽然有一个警察一心想着要破案,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群麻木的警察里面几乎是个怪胎。他的存在并不能带来什么转机,该怎样还是怎样。就像你身边的人都腐败堕落时你一个人严格要求自己,你得到的不是赞美,而是排挤。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坚持而变得更好,它会一直腐败下去。正义战胜邪恶?那是美好的设想。邪恶战胜正义,那是这个世界的潮流!
鲁迅说,他知道前面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希望,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一直走下去。波拉尼奥在书中这样说:“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完美的习作。或者同时也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我认为鲁迅之所以成为大师不是因为他有意无意的帮共产党痛骂了国民党和旧社会。而是他敢于和那些脏东西搏斗,即便他已经看出那些脏东西是不可战胜的。当我们现在庆祝美好的时代时,去看看鲁迅的书,那些东西依然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的来了。也许并没有什么民族性,那些东西可能是人性。那些东西到处都是,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种族。那些丧心病狂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生活中可能并不是什么混蛋,只要给你适当引导,每个人都能成为纳粹,或者纳粹的帮凶。
《2666》是一本不可能被剧透的小说,因为你找不到一条主线,谁都不能把它概括一段简短的话。这正是一开始让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你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讲一个怎样的故事。你看不到小说里面五篇东西有连续性,这五篇几乎毫不相干的东西被放在一本书里,竟然成了一本小说。当你读完整本书后,你发现了各个篇幅的联系。不是情节的连续,不是任务的连续,也不是那个在五篇都提到的圣特莱沙,而是一种氛围,它像大气层一样笼罩在整本书的上空,挥之不去。
只会歌颂和赞美的人永远成不了大师。真正的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