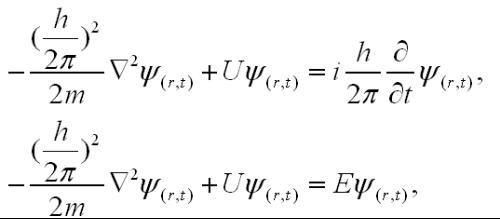窦一虎的出现,常常是在一张摆在戏场子中间的八仙桌上,桌子四脚上分别捆绑着从山上砍来的满是冬青叶的冬青树枝,每当出现这一道具摆设,于是魏官屯上或周围四村八寨的人们都会互相转告的涌来观看,他们就是喜欢这窦一虎从八仙桌上大吼一声跳将下来的威武之势。这八仙桌其实就是窦一虎盘踞生活的绿野山寨,他占山为王,堵住了薛丁山征西的通途,故而两方在此便有一番的撕杀,其结果窦仙童嫁给了薛丁山做了老婆,窦一虎则成了他的小舅子,心甘情愿地跟着一道征西去了。
场坝上的八仙桌竟然会被大人们称为是“山寨”,这是小孩子们想也无法想像出来的,但是窦一虎的那张脸谱却是“碧绿色”的,仅这碧绿色就是一奇,加之其出现的气氛渲染,使得窦一虎一角在人们的心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
窦一虎的扮演者洪山伯伯,本就是生活中的酷似窦一虎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大伙便干脆以“窦一虎”称呼他了。既已约定俗成,便无可争辨和质疑。
洪山伯伯初学跳地戏,其经历一路顺当而简单。其他与他一起学戏的人,都先后跳过小军老二、小白毛、笑兮兮、小老歪等配角,而洪山伯伯进了戏班子里,跳了两次小白毛之后,就尝试着戴起了窦一虎的脸子来。当然也有其特殊原因,一是原先跳窦一虎的张三公年纪大了,再让他从八仙桌上大吼一声跳将下来,恐怕是要骨折的,洪山伯伯的出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他别的角色唱词可以不用心记,只管记住他所要演的窦一虎出场的这一段内容就够了。自从刚刚解放以来,他就这样的每年都配戴着窦一虎的脸子,从地戏场中高高的八仙桌上大吼一声跳将下来,吓住了戏中的好多人物,却不断地给魏官屯上的男女老幼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窦一虎的快乐,是洪山伯伯的快乐,更是知道洪山伯伯的人们的骄傲。
为什么在谈到什么快乐事情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会产生那些始终挥之不去的关于生产队的记忆呢?生产队于我,于洪山伯伯,于窦一虎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呢?
窦一虎没有从八仙桌上跳下来已经有好多年了,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寨中的那群冒失的小伙子们冲上天乙山后,将装着地戏脸谱和刀枪之类的所谓“世旧”,抬到场坝中间原先为戏班子们跳地戏的地方焚烧化灰了,窦一虎同样不能幸免于难。窦一虎虽然化成灰烬,也不能将其与洪山伯伯的关系隔离开来。人们依旧暗地里叫洪山伯伯为“窦一虎”,哪怕是在那个“破世旧”的年代,只是洪山伯伯的喉咙和手脚不免要忍不住发痒起来。这发痒日子的结束,正好就是生产队结束的日子。
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人们一字儿排开,有手握锄头把在埋头劳动的,有手柱着锄头把说着家常聊着“王光二”的话题。不仅大伙儿闲得手脚发慌,心里也开始生着荒草。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没有能够束缚住洪山伯伯,他与几个魏官屯上的号称“闲人”的人要外出了,因为这时候不断地有来自四川的各种手艺人如缝纫匠、棉花匠、木匠、泥瓦匠等来到魏官屯,这给洪山伯伯的外出找到了根据和理由。
洪山伯伯终于走出去了,家里人拦也没拦住,生产队长老顺伯伯连哄带吓的也无济于事,洪山伯伯说这工分没法抢了,人都快要饿死了!他的出走,是不是像窦一虎离开了他原先的山寨“棋盘山”而去征西呢?大伙都会不约而同地把两者连在一起来想。
不要去管洪山伯伯在外到底干了些什么,因为你想打听也打听不到。一年半载过去了,洪山伯伯他们终于回家来了,除了同去的一个光棍带回了一个外地媳妇外,看不出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变化。还不能用“闯江湖”这样的字眼来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江湖充其量也只仅限于周围的两三个邻县。那个说话带着邻县浓烈口音的媳妇的嘴巴在日后才把他们的行踪不经意的漏了出来。
他们在外买牛卖马、贩运木材,当然还不仅要参与赌钱、诈骗、偷盗等团伙,只是数量不大,没犯下多大的事,方才免于公安部门的追捕。说起来也有些令人提心吊胆,骗个女人带回家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要从别人的兜里把钱骗到手,却是难上加难,强抢不行,只能智取,这是完全符合地戏人物窦一虎的性格的。洪山伯伯出于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跟着干了,以至于当年犯下的好多麻烦事情,待土地下放到户以后的好些年里,也不断的有人打听着洪山伯伯的名字找到家里来催钱。每每这个时候,洪山老伯娘都会边流着眼泪边数落着洪山伯伯,然后仍然不免要热情地招呼来者坐定下来,好茶好饭好酒地招待,这时的洪山伯伯却是一言不发地闷坐在一边,一个劲地抽着他的“朝阳桥”牌香烟。
催债的人来多了,魏官屯人便开始对洪山伯伯产生了质疑,他到底在外面怎么了?在外面的那几年里都干了些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穷,多想找些钱,本是天经地义,只是方法错了。借钱(其实是诈骗)不还,害得人家从老远的邻县赶来,破费不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应该说,来者与洪山伯伯当年还算得上是铁杆的兄弟。
土地承包到手后,洪山伯伯的心也收了,回到家里来,然而催债的人还是接二连三的来到家里,家人也因此不平和了起来。这是一段极度难熬的日子,所幸的是,正如堂屋中间神龛上和土地牌位上所说的:“土能生万物,地可产千祥”。有了土地后一切都好说,债还得慢慢的来还,日子也得轻松的过下去。
洪山伯伯平素里早晚都吆着水母牛和小牛儿,背上一个装满青草的竹箩筐,怀里揣上半斤盐水瓶装的散米酒,就算是打发他的日子了,当然嘴里还会哼着他的“窦一虎”的唱段。
那年,魏官屯的街道路面要扩宽各六米,说是小城镇要加快建设步伐,把临街的人家都下了拆迁令,后退三米。洪山伯伯响应政府和村委的号召,率先带头拆了老祖屋,但拆迁后的房屋低矮破旧,与宽大的街道极不相称,洪山伯伯干脆来个瓦屋变平房,还贴上了白生生的耀眼瓷砖。看到新平房的落成,街坊上的人们才把洪山伯伯从还债人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以前,看到平日里烟酒不断的洪山伯伯,不断有人在背地里说他:“欠了满屁股两肋巴的债,还整天的到小铺子里去打酒喝”。这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洪山伯伯,不仅不满足于整天的半斤小酒,还对原先的矮旧房屋产生了厌倦情绪呢。然而他的喜新厌旧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洪山伯伯的喜新厌旧,还反映在他如今对所配戴的重新请匠人雕刻的《薛丁山征西》脸子上,好多人又说,原来的那堂脸子古香古色。但他说再好也不存在了,必须要立足现实才能求得更大的发展,何况现在的“窦一虎”脸子所上的碧绿色,确实要比原先的好看得多。
重新站到了八仙桌上的洪山伯伯,这时才微微地感到了两脚的确有些发颤了,八仙桌也变得似乎要高了许多,窄了许多。毕竟年岁不饶人了,要从那八仙桌上猛然跳将下来,而且还要大吼一声,比划着些姿势,真是力不从心,看来不服输是不行了。于是,他开始考虑到下一任窦一虎的扮演人选了,选谁好呢?自己的儿子,恐怕是不要去想了,光看他那个样子,就够生气的了,从来不挨跳戏边的,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怕是要反倒叫他声“爹”也不管用的。
到底该选谁呢?这真是让洪山伯伯伤透了脑筋。窦一虎还能不能继续跳下去,这关乎着魏官屯上整个《薛丁山征西》的一堂大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