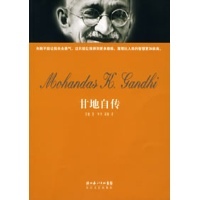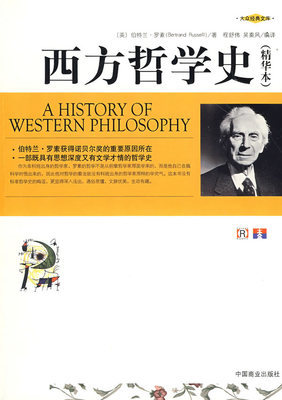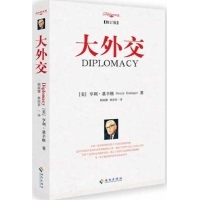最近又开始读第二遍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有一些记录和反思,与大家分享。觉得在这个时代好好读一下这本书,以及多读点历史书,会是一件很好的事。
——————————————————————
1、
嚼碎了食物口对口喂牙口很好的孩子,无时不刻都盯着孩子,中国老人们这样做是为什么?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的一番话可以解答: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家族事务表现出炽热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中国农村,譬如我老家河北农村的生活,是一个乏味的轮回: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为孩子盖房子,为孩子结婚;孩子做了父母,同样的轮回
在这个轮回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就是抚养出同样没有意义感的后代来。
2、
如果一个人生了病,无法发挥身体功能,甚或是肠子痛⋯⋯他就会动念去改革——改革世界。
——梭罗(Thoreau)
3、
要唤醒民众,一个关键因素是给他们一种真实或虚幻的权力感。
例如,咱们工人有力量!
否则,“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
因为,“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象:不可预测性(即命运)已为我们所驯服。”
“会不假思索就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
4、
唤醒群众的两个要素:
a:权力感
b:许诺未来
根本上是——你是有用的,你可以左右世界,虽然,你不能左右自己。
5、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入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穷无尽的。
6、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别人认可自己,别人的认可就成了自己生存意义的证明。
有时候,这个认可像是自己挣来的,你真的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人,你真的是一个好人。然而,问题是,如果拿掉成就或“好人”,你是否能看到你存在的证明。
太多时候,我们会掠夺别人的认可,胁迫别人的认可,为了得到这个,甚至不惜把别人毁掉。
你没有义务配合这种掠夺或胁迫。
7、
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掉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尽管,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8、
希特勒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员和工会领袖绝不会成为纳粹党员,但共产党员却常常会。”纳粹党青年部主任罗姆曾自夸能够在4星期内把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变成狂热的纳粹分子。相似的,共产主义宣传家拉狄克也把纳粹的褐衫队员视为共产党生力军的人才库。
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
9、
1792年(法国大革命)立法议会下令要各地建立圣坛,刻上下列铭文:凡属公民,均应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活,为祖国而死。
10、
要遏制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在日本,捻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怒火的,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
(即将对内部的不满与怒火转移到外部——帝国主义上,这一点我们是很熟悉的。)
11、
有证据显示,日耳曼蛮族的人数相对较少,但一旦他们侵入一个国家,原来的被压迫者和不满者就会群起而加入他们,“那是一场由外国征服引发和遮掩着的社会革命。”
(又如清兵入关,被屠杀者数千万甚至上亿,将这个罪业单纯归到清兵身上就是算了一笔糊涂账,其实屠杀者中,李自成和张献忠要占首罪,且明军自己罪业也很大。)
11、
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乡间务农的正 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会另一端的个人,包括失败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从未侧身其间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号把这两者加以毁弃。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亿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己: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种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运动之中。
这些被抛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换言之,本来为建筑师鄙弃的石材会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奠基石。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欧洲的弃民竟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是历史开的玩笑——唯独他们能够成就此事业。

(最近看了多本历史书,如《逐陆记》、《别笑,这是大清正史》和《民国就是这么生猛》,可以看到埃里克-霍弗的论述是何等精彩。最典型的如李自成和张献忠,他们两个做什么都不成功,唯独“革别人的命”很厉害,流氓在推动着所谓的历史,我们甚至美其名曰叫进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