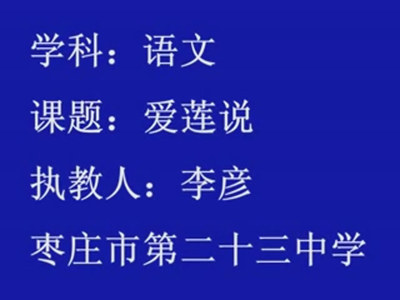陈寅恪简介(转载)
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1890年--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健东),三联书店,1995年。
陳寅恪傳 作者:夏双刃
陳寅恪者,字鶴壽,江西義寧州人也。祖寶箴、父三立,皆一代名士;兄弟五人,亦一時瑜亮也。寅恪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生於長沙周氏蛻園,唐劉蛻故宅地也。因肖虎,故名寅恪。幼好讀書,過目不忘。侍坐凝聽,復述無遺。齔齡,即涉獵《說文》、《天官》、《貨殖》、《通典》、《通考》,五經廿史,聯詩興對,天才之資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隨長兄衡恪赴日本留學,就讀於巢鴨弘文學院初中。兩年後回金陵考取官費留日,就讀于日本弘文學院高中部,始以梵文漢文互證之法研習佛經。不久患腳氣病,回金陵治療,頗遊歷前明遺迹。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上海復旦公學,好縱論子史佛乘。宣統元年(1909年)畢業,赴柏林大學。三年,轉赴瑞士蘇黎士大學,讀《資本論》。遊歷挪威,吊易蔔生墓,賦詩云:“東海何期通寤寐,北歐今始有文章。”
民國元年(1912年),以資用不給回國,與父寓居上海,曾謁父執夏曾佑。次年,赴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就讀,由王國維介紹,結識伯希和,頗聞其教。是年,聞袁世凱獨裁,乃賦詩諷之云:“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鴃喚東風。花王那用輕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
民國三年(1914年),一戰爆發,回國居金陵散原別墅,自修文史。京師圖書館欲聘之主持館務,固辭之。次年,嘗赴北京爲蔡鍔秘書,時蔡鍔爲經界局局長也。繼而侍母居滬就醫。秋,爲江西教育司閱留德學生考卷,因患痢疾,返南京休養。次年,複侍父母至上海。次年,居南京、長沙間。
民國八年(1919年)初,至哈佛大學,從?#123;門教授研習梵文、巴利文。與涇陽吳宓深相交?#123;,嘗與論中西之學云:“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爲遜於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其長處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短處是於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適相同。”
民國十一年(1922年),赴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師從獸鬥、繆勒教授,研習東方古文字,於史實中求史識。時留德學生風氣孳亂,惟寅恪、傅斯年、俞大維能出淤泥而不染。觀寅恪當時之筆記,有藏、蒙、突厥、回鶻、吐火羅、西夏、滿、朝鮮、梵、俄暨中亞、新疆、去盧、巴利、耆那教、摩尼教、印地安、伊朗、希伯萊、東土耳其諸文字。次年,母俞淑 人、長兄衡恪相繼卒。
民國十四年(1925年),因吳宓、梁啓超力薦,受聘爲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吳宓爲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即歸國,因父病請假一年。十月,葬母、兄于杭州牌坊山。次年,哈佛大學遣趙元任聘寅恪往任教,婉拒之,云:“餘對美國之留戀,惟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之對蝦耳。”
是年,赴清華園任教,與吳宓比鄰而居。時國學研究院方建不久,仿歐美設導師制,先寅恪受聘者,惟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三人而已,遂與並稱清華四大導師,亦稱四大才子。教授佛經“翻譯文學”、“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咧芯俊钡日n程,多開前所未有之先河。次年五月,王國維自沈,寅恪爲作《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其辭曰:“海甯王靜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羅振玉與寅恪道:“忠愨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
民國十七年(1928年)七月,赴上海探父,並與唐篔結婚,時年三十九歲。居一月乃返。是年夏,國民黨入北京,改北京爲北平。次年元月,梁任公病逝。二十二年(1933年),迎父散原北上,寓西城西四牌樓姚家胡同。
民國十九年(1930年),教育部易清華園內學校爲清華大學,寅恪轉爲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因其高才卓見,發前人所未道,故燕京等外校生皆來旁聽,縱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等亦然,故有“太老師”之尊稱也。次年始,兼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理事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組長,又兼故事博物院理事並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等,故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時國人好往日本研究中國文化,寅恪憤云:“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嘗激勵學生詩雲:“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數年後,有日本史學大家白鳥庫吉請教有關中亞史問題,遂爲解惑,彼五體投地,因當世無人可解,唯寅恪可也。
至盧溝橋事變,概于清華園中精研深教,著述宏富,涵蓋中北亞民族史、隋唐及中古史、中古佛教史、中古語言音韻學、敦煌學等諸多方面,有《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緣曲跋》、《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敦煌本十頌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元代漢人譯名考》、《大乘義章書後》、《敦煌劫餘錄序》、《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吐蕃彜泰贊普名號年代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國志曹沖華佗與印度故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幾何原本滿文譯文跋》、《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測》、《禪宗六祖傳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考釋序》、《斯坦因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殘卷跋》、《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試題書》、《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支湣度學說考》、《讀連昌宮詞質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易解釋》、《李唐氏族支推測後記》、《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四聲三問》、《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李太白氏族之疑問》、《陳垣西域人華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懷之原題及其次序》、《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武瞾與佛教》、《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論韓愈與唐代小說》、《桃花源記旁證》、《東晉南北朝之吳語》、《讀秦婦吟》、《府兵制試釋》、《李唐武周先世事迹雜考》等文。
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城破,散原憂憤絕藥而死。寅恪守孝滿七,悲慟過度,致右眼失明。于十一月攜眷南逃,經天津、青島、徐州、鄭州、漢口、長沙、衡州、零陵、桂林至梧州,晤廣西大學校長李運華,複順江而下,經虎門抵香港。在港期間,多得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幫助。寅恪於次年初隻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聯大,夫人因有心臟病,遂攜三女留港休養。經越南海防時遭竊,手稿遺失甚多,加之逃難以來書籍失散太多,兼染瘧疾,精神幾近崩潰。病瘳,方赴蒙自,著授之餘,留心時局,慷慨多哀,嘗有“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次年,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教授“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佛經翻譯文學”等科。此期著有《逍遙遊向郭義及支遁義探原》、《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狐臭與胡臭》、《論李懷光之叛》、《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蹟詩》、《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讀洛陽伽?#123;記書後》諸文,又有《讀通志柳元景沈攸之傳書後》一篇未成。
二十八年(1939年)夏,應牛津大學之聘,取道香港赴英,以圖英倫典章文卷之盛也。遂與妻女團聚。而歐戰蹙起,大學疏散,遂別妻女,複返昆明。是年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並有《劉複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讀哀江南賦》、《敦煌本心王頭陀及法句經跋尾》、《劉叔雅莊子補正序》諸文。
二十九年(1940年),增開“白居易研究”一科。三月,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逝世,寅恪往重慶參加評議會,推選新院長。時當局欲以顧孟餘繼之,寅恪則薦胡適或李四光,並雲蔣先生之秘書不宜當選,學術焉容政客污染云云。衆遂推舉翁文灝、朱家驊、胡適爲候選人,顧孟餘落選。當局遂擱置良久,至十月方任命朱家驊爲院長。寅恪感茲事,爲賦詩雲:“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是年夏,爲赴英再至香港,因歐戰滯港兩年。時許地山爲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聘寅恪爲客座教授。嘗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而已,竟能綿延兩月,足見廣博。次年八月,許地山逝世,寅恪作挽詞,並繼爲中文系主任。十二月,日軍寇港,覬覦寅恪所居之樓房,勒令搬遷,寅恪以日語斥之,乃止。日僞複標記其宅,饋米,禁擾,利誘官職,寅恪皆不受,惟典當衣物爲繼。是年,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並有《讀東城老父傳》、《讀鶯鶯傳》、《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諸文。
三十一年(1942年),汪僞遣人邀寅恪北上,籌建東方文化學院。寅恪乃攜妻女逃離香港,經湛江、赤坎、廉江、郁林、貴縣、桂平、柳州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來迎。遂于廣西大學任教,居良豐之雁山別墅。次年夏,日軍逼近,乃契眷北上,經柳州、宜山、都勻、貴陽,輾轉抵渝,夫妻俱病,寄俞大維處休養,弟子蔣天樞、燕文徵來謁。十二月,赴成都之燕京大學。次年元月,遊杜工部祠。此期,撰《元白詩?#123;證稿》一書,並有《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陳述遼史補注序》、《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梁譯大乘起信論僞智愷序中之真史料》諸文。
三十四年(1945年)正月,左眼亦失明,于成都存仁醫院手術失敗。遂於是年生日作詩雲:“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爲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是年八月,日本投降。初,聞將以天皇爲戰犯,寅恪憂慮雲:“此事絕不可作,日本軍人視天皇如神,如此則必拼死抵抗,以保護天皇;若保留天皇,爭取其議和,日軍則不敢違抗。如此則我方犧牲益小,而彼方投降亦易。”
是年九月,赴英倫治眼疾。因耽擱太久,不得治。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學講演東方漢學,彼時全歐漢學家如雲而集,然除卻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數人外,皆難明曉。次年春,經美國歸國。十月返清華爲教授,開“隋唐史”、“元白詩證史”諸科。兼燕京大學導師,且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時事日非,又目盲不見,遂名書齋爲“不見爲淨之室”。又次年,冬寒甚,清華經費絀,無力供暖氣,寅恪乃鬻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言各書與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以購煤置爐。此期有《讀吳起昌撰梁啓超傳書後》、《徐高阮重刊洛陽伽?#123;記序》、《楊樹達論語疏證序》、《從史實論切韻》諸文。
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五日,共軍迫近北平,傅斯年電話敦請寅恪南下,乃舉家乘飛機至南京,胡適夫婦與俱焉。次日赴滬。次年元月十九日,抵穗,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攜文學院師生列隊迎之,王力、容庚、冼玉清等在焉。傅斯年數促請寅恪赴台,終不往。爲嶺南大學中文、歷史系教授,開“白居易詩研究”、“唐史研究”諸科。初,助教爲黃如文,皆以粵語,難盡通解。及次年,程曦至穗替之。居一年,有以講師誘程者,程遂去,夫人親爲助教焉。一九五二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轉爲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劉節,寅恪故清華弟子也。次年,國務院欲以寅恪爲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邀其入京。固辭之,薦陳垣代己。此期有《崔浩c寇謙之》、《魏志司馬芝轉跋》、《書唐才子傳康洽傳後》、《秦婦吟校?#123;舊稿補正》、《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論韓愈》、《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諸文。又有《論再生緣》一篇,以《再生緣》可與印度、希臘之史詩相儔。且始作《錢柳因緣詩釋證》一書,即後《柳如是別傳》也。
一九五六年,陳毅副總理于穗拜謁,談敘歡洽,寅恪歎曰:“不意共產黨內,有此通學問者。”是年,陶鑄爲中南局書記,重寅恪學行,多來訪談,倍極照顧,嘗命人于陳宅庭院修白色甬道,因寅恪雙目僅可見微光也。其專力學術,亦好往聽京劇、昆曲,如《論再生緣》,即此時之事也。八月,章士釗爲國共密談事赴香港,經穗拜謁寅恪,乃攜《論再生緣》赴港,於海外翻印流傳,而國內卻無人知曉也。
一九五七年,全國反右,定寅恪爲“中右”。是年,猶有《書魏書蕭衍傳後》一文。次年,文化界“厚今薄古”運動,指寅恪爲封建主義立場之種族文化論者,郭沫若又發表《關於厚今薄古問題》,雲:“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産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遂有人攻擊寅恪散步資產階級思想毒素,誤人子弟,寅恪乃憤而退休。學生則多半下鄉去矣。
一九五九年,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欲來拜謁,婉拒之,反復爭取乃得晤。寅恪質問雲:“去年初,新華社聲稱學生教學強于老師,而半年後又雲學生應向老師學習,何以前後矛盾若此?”周答曰:“凡新事物皆須實驗,社會主義亦然。”寅恪道:“甯有以舉國實驗如是之謬哉?”賓主一時僵持。一九六一年三月,郭沫若來謁,與討論《再生緣》等,時寅恪著意柳如是,而匱乏資料,郭乃爲影印科學院有關藏書,且於媒體介紹寅恪之研究課題。次年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來謁,與論大躍進之事。胡喬木者,原清華學子也。當年未曾聽寅恪課,今日得教,欣欣然而去。然寅恪所見者,皆有所可見者也,尤以外籍人士皆謝絕。口不臧否,若忘時事,以避是非。學術則摒棄諸說,惟傾力于錢柳因緣研究也。
一九六一年八月,吳宓由重慶來訪,俱雙袖龍鍾,惘然如隔世,寅恪與雲錢柳因緣之事云云:“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以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也。”臨別愴然,寅恪爲賦詩云云:“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一九六二年溽暑,滑倒於浴盆內,摔折右股,雖有陶鑄爲延請良醫,亦難接複。從此長期臥榻,陶鑄遣三名護士輪番照料。待疼痛稍退,即複致力於錢柳之事,時助手爲黃萱也。越明年,《錢柳詩?#123;證》初成,寅恪借項鴻祚語雲:“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又一年,此書定稿。凡歷時十載,涉獵文獻六百餘,融會貫通,詳究前後,以殘者之身,成此鴻著,或以寅恪爲當代之左丘明也。而寅恪視柳如是爲千秋知己,尤愛其《金明館詠寒柳詞》之詩,遂命書齋曰金明館,曰寒柳堂,是年遂更名爲《柳如是別傳》,書後偈云云:“奇女氣銷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鬧學臯比決舍。無事轉忙然脂暝寫。成廿(廿)萬言如瓶水瀉。怒駡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文革期間,陶鑄爲國務院副總理,特指示廣東省委善待寅恪,然紅衛兵置之不理,反逼寅恪交待與陶鑄之關係,欲以此整跨陶鑄也。彼等佔據陳宅對面之辦公樓,終日以高音喇叭往陳宅呼喝口號,又凍結寅恪夫婦工資,艱難潦倒已甚矣。又常攀緣而入,猶攻城然,逐助手黃萱及陶鑄所派三護士,遍處張貼大字報,且搶掠物品、文稿也,如寅恪自傳《寒柳堂紀夢》亦不得免,室內一時蕩然。又欲擡其至禮堂批鬥,唐夫人阻攔遂遭毆打,劉節乃自願代寅恪受批鬥。當其時也,紅衛兵問其有何感想,劉仰面答曰:“無他。惟能代師受批鬥,倍感光榮。”不久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其何以庇護寅恪若此,陶亦正色云云:“爾等若有陳寅恪之水平,我亦如是待爾等。”
一九六九年,中山大學之造反派搶佔其住宅,遷其至別處,環境污濁不堪,夫妻相對垂涕。寅恪憐夫人之淒苦,爲作生挽聯雲:“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五月五日下午,被迫作口頭交代,直云云如在死囚牢中,終至口不能言方休。苟存數月,於十月七日晨五時半,即舊曆己酉年八月廿六日乙卯,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痹逝世,次月二十一日,夫人唐篔亦病逝。
二零零四年六月,骨灰遷往廬山,故散原松門別墅側也,名其岡曰景寅山,時距其逝世已三十四年矣。其學有蔣天樞、周一良、許世瑛、戴家祥、卞伯耕、燕文徵等人繼之傳之。
余嘗聞焉:當中印戰罷,中共密擬以麥克馬洪線爲准談判邊界問題,時無人知其究竟,毛澤東遂指示云云且徵詢陳寅恪。時寅恪已被打倒,然家國之事,略無猶疑,於是以盲者之具,歷數每段每截當在某書某頁,於是得麥克馬洪線也。其博聞強記,前後世鮮有其匹,故中亞曠滅之數十種古語,寅恪皆得而用。又崇尚氣節,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於顛倒之世,獨能直立。惜此仳離之世,磨滅有生之才,其才不能盡展,宵小跳梁,群醜焚書,而責任複誰堪克當?使高樓之客,徒堪遠眺;近世之學,寧不歎歟!
陳夫人唐篔者,字曉瑩,廣西灌陽人也。祖父景崧,同治四年進士,初爲吏部主事,遷臺灣巡撫。甲午戰後,清朝割臺灣與日本,景崧籌劃成立臺灣民主國,當時同道中亦有陳氏親友焉。後因日軍大舉攻台,不得已撤回大陸,嘗著《請纓日記》等,爲世人所敬。父早故,依寡母居天津,後就讀金陵女子學校體育專業,畢業後爲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體育教員,繼而爲主任。移居北京西城,不久母故。
民國十七年(1928年 )七月,與陳寅恪赴滬結婚。爲寅恪生流求、小彭、美延三女。四十年間,除戰亂時曠隔桂、港,餘皆相濡以沫,尤以寅恪于文革中倍遭迫害,夫人以七旬之齡,孱弱之質,行三護士之職,有當熊者之勇,終至力不能堪,垂垂欲去,至寅恪先逝,乃從之而去。思寅恪盲者之具,實可見名花;夫人縛雞之力,足可敵萬夫。誠可羨矣!有《詩集》存世,其中五言《哭從妹婉玉夫人》一首可見其身世。
贊曰:國家何幸,逢斯良姓。國家何辜,邈不如初。國家何以,自毀良史。國家何去,恐不能禦。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作者:张求会
1969年10月、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经历4年折磨,终于俱不能支,相继逝世。此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文革”结束后,两个女儿作了分工:长女流求负责动用一切关系,解决父母骨灰“入土为安”的大事,完成父亲归葬杭州祖墓的遗愿;幼女美延负责追讨浩劫时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遗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缚,三联版《陈寅恪集》已于2002年问世;“入土为安”之事历经20年奔波,却始终无法圆梦。
义宁陈氏杭州祖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25年。这一年12月,陈寅恪之母俞麟诗卜葬杭州牌坊山,于穴左预留陈三立生圹,并附衡恪茔次。1948年夏,陈三立的遗柩在暂厝北平长椿寺11年后,由次女陈新午等人护送至杭入葬。从此以后,归葬杭州,“埙篪鼎足侍,万劫依恃怙”(陈小从诗句)便成了“恪”字辈兄弟的心愿。
解放后不久,驻浙某国防单位拟在牌坊山建疗养院,限令将陈三立墓迁移,否则将被炸毁。此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难,亦即陈寅恪1951年《有感》诗句“岂意青山葬未安”的由来。陈隆恪接此消息后,焦急万分,遂函恳挚友李一平设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联络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层,请求出面制止此非礼举动,后经高层领导批示:陈墓周围若干距离内,不得再建屋舍。嗣后又于1956年定为浙江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复审时被撤销)。
1957年秋,陈隆恪夫妇归葬于杭州杨梅岭。隆恪之女小从原拟遵从父亲遗愿,葬于祖父母茔旁,但格于风景区不得再建新坟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陈隆恪夫妇被迫改葬之举,似乎早已预示了陈寅恪入土之难。
“文革”期间,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园内外的大小建筑物一扫而空,万幸深埋地下的三副灵榇丝毫未损。1986年夏,经李一平奔走呼吁达7年之久,始获重修墓茔之批复,由公家拨款8千元作为经费。因墓地早已辟为茶园,重建需将茶树斫去若干株,当地茶农颇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体裁衣,紧挨着两座坟头,围以砖墙,勉强为“白墓浇常湿”保留最基本的环境。
不数年后,报载西湖风景区开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记者均以无主坟论处。远在成都的陈流求闻讯后,于1991年底专程赴杭,幸亏已由程融钜嘱其学生代办了登记手续。事毕,散居各地的亲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范围之内的祖墓却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惨遭腰斩。陈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旧碑仅存“之墓”二字(原作“诗人陈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于无法重书,遂将旧碑照片放大,摹写勒石,重新竖立在祖父墓前。
数十年间,杭州墓园三历沧桑之劫。有鉴于此,陈氏姐妹决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谋求改葬江西庐山松门别墅。松门别墅原本是民国时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陈寅恪留学款项而赔偿陈家的,陈寅恪本人在诗中也曾将此处视为故宅,因此陈氏姐妹认为归葬庐山并未违背亡父的意愿。此外,庐山既为风景区,游人不断,且海内外知名,众目睽睽之下,远比杭州安全可靠。
二
正当陈氏姐妹为了归葬之事四处奔波时,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识到了迎葬陈寅恪的重大价值。1989年初,江西诗词学会率先上书省政府,建议将松门别墅改建为陈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议又送进了省委统战部。据说,陈寅恪归葬庐山以及松门别墅改建纪念馆等事,并没有明显的反对迹象,似乎只是时运不佳:第一次是因为九江市某工农领导不愿出资18万元合建纪念馆;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应合资经营,偏偏赶上中央下文不准兴建楼堂馆所。
转眼到了1994年,江西学术界在得到义宁陈氏某后裔的赞助下,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之一便是赴庐山参观松门别墅。破败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着会议的东风,又有老先生、小先生们重提旧事。江西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一口答应了迎葬、改建之事。当权者的一番应景之词,自然再次换来了一片颂扬、一片感激。岂知人事难料,随后的若干年内,省长换了,厅长也换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从未提出过,送上去的申请居然连找都找不着了。惊诧之余,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伤感者有之,绝望者有之,惟独是无形的管理“机器”运转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两次的延宕之下,当年一同参预此事的长者,不少人还来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在广东出版,最后一段文字借题发挥,谈及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也是试探着能否再现一线生机。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黄永玉的关注。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之祖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起初他认为归葬是经济上有困难,等到辗转找到我,初步知道内情后,这才觉察到:“迁葬不光是钱的问题”,继而感慨道:“我不知迁葬寅恪先生有这么多阻难,真令人伤怀。其实陈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计较点数过身外细软?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后,黄永玉“随时在找机会,看世上还有没有为这件事出些真力气的人”。(黄永玉致笔者信)
第二年7月,黄永玉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请毛致用在陈氏姐妹致黄永玉的信上签署意见,转交给江西省。江西民政厅遂在省长亲自督促下,联合建设厅和庐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见:
一、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大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骨灰葬于庐山,有利于发挥名山、名人的作用,促进江西旅游的发展。对其后裔要求将陈寅恪夫妇安葬庐山的愿望表示欢迎。
二、将陈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庐山,可以更好地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会影响景区的观瞻。因此,我们赞成将原陈三立先生所住庐山松门别墅定为陈三立先生纪念馆,在靠近“月照松林”景点处修建陈寅恪先生纪念园,在园内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凿洞安放陈寅恪夫妇骨灰,辟陈寅恪先生的诗文石刻组群,并修卵石小道与松门别墅连接,使之成为瞻仰和研究陈三立和陈寅恪先生的场所。
8月初,上附省长批示的《意见》送达毛致用处。“如陈先生的子女认为可行,即可具体商定实施”的郑重承诺,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个月后,黄永玉亲自将《意见》带到广州。陈美延因为摔伤了腿脚,只得在电话中向黄老致谢。永玉老人的答词颇奇妙:“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的!”当时我就想,又没有外宾在场,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时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从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显那句悲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爱的理由”?
三
对于卧病在床的陈美延来说,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断地拨打电话,从省政府到民政厅,到建设厅,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余,不断地寄出《陈寅恪集》聊表谢意,不断地寄出感谢信,不断地陪着小心试探、跟进。惟一庆幸的是,民政厅的当家人在文化厅任过职,中文系毕业,十分熟悉陈家的事情,去过修水陈氏祖居。且爱好书法,正在举办一个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江西名家书法展览,拟进京展出。碰到这样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岂知一个多月后,变故再起。临近年终的某一天,远在成都的陈流求在与民政厅通话时,对方态度忽然有了转变,称陈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陈氏姐妹落款在后”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陈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陈氏姐妹的一点“私心”,无非是鉴于杭州祖墓多次被毁,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威名”加强保护而已。)至于下一步如何办,民政厅让陈家直接与庐山管理局联系。
新年过后,黄永玉自意大利来穗,听闻此事出现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惊,对此事仍颇有信心。他极力反对在墓碑上题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类,认为太俗:“陈先生不需借政府来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陈先生来扬名。”当晚会面时,陈美延仍拄拐杖,因为时时想着不能误了行程,锻炼过度,踝关节反而出了些问题。步出电梯时,女儿许郁葱搀扶着母亲,缓慢迈向会客厅。此情此景,顿时令人联想起1961年9月1日吴宓日记中的片段:“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注: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从底比斯开始流放,直至父亲在雅典附近死去。)
此次见面约定数事:墓碑请黄永玉题写;暂不打搅江西方面,待“两会”后由黄请毛副主席出面,陈氏三姐妹(含武汉的陈小从)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镇,安葬骨灰、建立纪念馆等事一举而成;安葬事毕,黄亲自来穗为陈寅恪塑一铜像,永留庐山。
四
2002年4月,黄永玉亲自出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与省委书记、省长交换了意见,由省里指派专人具体负责,安葬工程终于重新启动。
4月20日下午,民政厅安排小车开赴庐山,我与陈流求夫妇及民政厅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黄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与许郁葱(代表陈美延)会合后再上山。安排停当,由庐山管理局的一位女处长陪同,实地看了看松门别墅的周边情形。管理局没有明说反对入葬松门别墅附近,但反复强调几点困难:庐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原有景观不容破坏;国家风景名胜区内,不能出现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门前巨石上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还存有违反规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坚硬无比,施工难度极大。返回住处途中,女处长执意绕道参观管理局的长青园,建议改在长青园内购置永久墓地,价格可以最优惠。陈流求虽未明言,但显然与对方无法沟通。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刘仁勇(陈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陈二老再上松门别墅。陈流求根据幼时的记忆,特意从不同的路径上山、下山,走走停停,凭空添出不少趣味。下山途中,大家议及民政厅《意见》中的石亭、诗文廊、纪念馆云云,估计不可能一步到位。最为迫切的还是尽快入土为安,归葬骨灰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修筑墓碑,都觉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树一块碑,简简单单几行字,说明墓主是谁,碑石上还不能出现“之墓”一类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联版《陈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于是建议碑文干脆如此处理:右侧书“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中间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侧留给黄永玉题识。陈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议再定。
临近中午,各方车辆陆续到齐。陈流求领着代表陈家第三代的刘仁勇、许郁葱,陪同黄永玉登临松门别墅。一行人在门前一块较为平坦的巨石前驻足,详细地商议了凿洞、封顶、刻字等细节。松门别墅环境之清幽,周围巨石之天生雄伟,颇让黄永玉吃惊,连连让人摄影留念。略显荒凉但气势犹存的方寸之地,经由书画大师的鉴赏,越发令人相信这里正是安葬陈寅恪夫妇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虽然短促,但在黄永玉的一手策划下,惊动了高层,应该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长亲自过问的项目,哪里还用得着担心?这么一想,我便觉得自己应该放下心来,学一学黄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参预此事。回广州后,一晃又是大半年,从偶尔的联系中获悉:陈美延已进京求到了黄永玉的墨宝,仍然采取在庐山时商议的内容。此外的事项则再次陷入僵局,问题仍然卡在九江。黄永玉也已知晓情况,仍然允诺继续管下去。
五
转眼又入新年,正当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复奢望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月中旬前后,经陈美延告知:庐山植物园有意安置陈寅恪骨灰,据说是江西科技厅牵的线。妙就妙在植物园归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辖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体制上的特别之处居然成全了一桩善举。
直到5月22日,我才从陈美延那里得知较为详尽的内容:庐山植物园接触此事后,始终觉得能够迎葬陈寅恪夫妇骨灰是植物园的光荣,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视此事,连退休的老主任们都出来出谋划策。选择基址,安排施工,迎来送往,事无巨细,均做得十分体面周到。从植物园来看,陈寅恪1955年曾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与中科院早有关连;其次,北京植物园前此已经迎葬梁启超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可谓有例可循;再次,义宁陈氏于中国植物园事业贡献良多,陈封怀(即陈衡恪之子)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1993年辞世后,遵从其遗愿,将其骨灰与另一位创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茔两侧,此即今日植物园内的“三老墓”,坐落于松柏区水杉林内,离松门别墅不远。有此三大因缘,庐山植物园自然觉得责无旁贷。从陈氏姐妹来看,山穷水尽之时,谁能料到柳暗花明?此为第一重惊喜;父母身后既有亲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邻近祖居,此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点,游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乐观其成。
虽说去年未能上山,陈美延后来却连着两次登山陟冈。一次是应邀面议选址、安葬等具体事宜,第二次则是护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园在事先征得陈氏姐妹同意后,选择吉时良辰将骨灰入土。入葬当日,天空难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现了日晕,一片吉祥。园方考虑周详,特意录了像,刻制成光盘,分寄成都、广州。至此,实质性的入土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后,安置骨灰的小山冈已被正式命名为“景寅山”,连接“三老墓”与“景寅山”的小路也已开通,地面建筑也在陆续添置。
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七日)这一天,是陈寅恪113岁冥诞。陈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庐山植物园举行的墓碑揭幕仪式。至此,陈寅恪夫妇终于入土为安,一代国学大师的身后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六
书生论事,千人诺诺而一士谔谔,此为长处;不懂“规则”,时时以常情常理度人,此为短处。十有八九,长处无从施展,短处却每每足以误事。于是,在管理“机器”与书生的对抗中,胜败早有定数,一切的努力与挣扎都仿佛“蚍蜉撼大树”一般令人沮丧。千百年来,这一场机器与人的对抗从未间断过,在训练有素、冷漠无情的庞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与情感都变得无济于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机器在侮辱践踏人格的同时,总能将一大批逡巡于门外的高等看客拉扯进门内,收罗在麾下,转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摇旗呐喊、赤膊上阵。威逼利诱当前,读书识字者往往难以自安其道、自守贞节,索性“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注:做广告),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陈寅恪语,存《吴宓日记(1917~1924)》)。
众所周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为陈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实,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看似激昂实则艰涩的10个汉字,原本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标志。在我看来,“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自由”--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还应该扩展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独立”与“自由”从来都似乎只能局限于“精神”或“思想”的层面,而且换取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代价往往又是那么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为“孙志刚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贵与可怕变得那么令人不敢确信。在此基础上,我宁愿相信:一切引导人们朝着真、善、美的境界迈进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高尚”;而那些有助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动,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现实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陈寅恪曾经活着并将继续活着的意义才不至于被“高等流氓”们阉割。这意义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声音,它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天你高尚了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