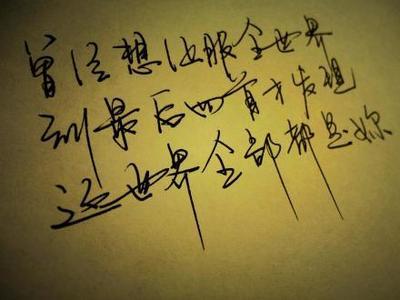回憶章培恆教授
作者:孫乃修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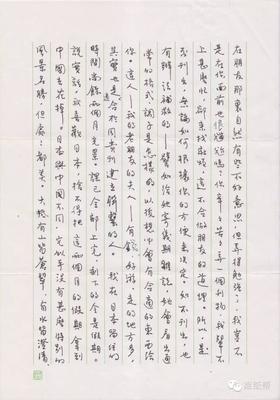
週末深夜瀏覽學術消息,驚悉章培恆教授辭世,頓時往事聯翩,竟至久久難眠。
一九七七年,“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我從北京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專業方向“文學評論”。一九七八年早春入校,玉蘭花含苞欲放。那年,章培恆教授四十四歲,風華正茂。我和他的接觸和交往,不頻繁,卻深刻。心智的理解靠瞬間妙悟,無須頻繁。
本系教授對我盛讚章培恆老師的博學強記,稱他的頭腦是“電子計算機”;講授外國文學史的一位外文系教授對我稱讚“你們中文系的小章培恆老師”的學識才華。初見章先生,在復旦園,他剛從日本講學歸來,西服革履,走路緩慢,話語簡短,字斟句酌,有條不紊,一口帶有紹興鄉音的普通話,笑起來克制,似略帶羞澀,待人踏實,態度誠懇,處世為人內斂而非常低調。
本科讀書期間,同學們考自全國各地,可謂每省選一,幾乎個個雄心勃勃、勤奮努力,彼此競爭激烈卻非常友好,或以發表作品論文、出版書籍為能,或以各科考試高居榜首為喜。大約在第三年,系裡決定重點定向培養文學專業的三位學生,筆者有幸成為其中一位(我是其中唯一的外地人即非上海人)。此後,與幾位著名教授包括朱東潤、蔣孔陽、施昌東、章培恆等教授接觸(復旦中文系教授甚多,為人治學甚佳,我心中永遠感謝他們,這裡恕不一一),但多是富於敬意的簡短交談。那時我以為,最佳途徑是去大量直接閱讀古今各界名家著作,因為文字著作比言談更能系統、完整地表述理論見解。加之,我喜歡讀,而非談;喜歡思,而非爭。
大學期間,心靈孤獨而思維豐富,宿舍、教室、飯廳、圖書館四點一線,完全沉浸在文藝理論、美學、哲學、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中外藝術等等抽象思辨領域和形象思維領域完整構成的精神世界裡。那時,我的最強烈的學術追求,不是死板知識、死記呆讀,不是隨口說出某字某句之出典(像前代博學強記的古典學者和教授那樣能告訴你在哪書哪章甚至哪頁找到出處),而是學術根基的深厚、博大,學術思想的深刻、獨到,使思想能夠激活知識資源,對古典作品精髓的真確理解和對其人文價值的準確揭示。簡言之,就是要有雄厚的學問根基、富於真知灼見的思想智慧,心靈高度自由地超越前代學者之學術藩籬,打破一切畫地為牢的傳統學術觀念和畛域。我以為這才是當今新一代學者的學術性格和學術形象。僅僅成為某一位著名作家的研究專家,是我雅不願意的;僅僅限於五四以來的作家和文學,是我雅不願意的;僅僅限於古典作家和文學而不兼及西方文化和思想家,也是我雅不願意的。最令我痴迷的是各個學術領域的自由馳騁,是理論的快感、心智的愉悅,那是任何死板知識所不能替代的精神快樂。也許正是由於這一精神特點,本科畢業前夕,同學們彼此臨別贈詞,一位同學為我寫下四個字:“君子不器”。斯為知言。
二
讀研究生期間,大約是在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選章培恆教授的課,那是關於晚明小說研究的一門討論課。選這門課的人很少(可能是為研究生開的課)。在講晚明的一篇小說時,章培恆教授的平靜解讀和簡潔評論,使我心中靈光激射、大為振奮。那是對古典文學作品中的人性的價值做的肯定。我以為,稱章培恆先生這種觀點為“當代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人文主義思想”應當更準確、更富理論性。這種觀點在當時剛剛走出階級教條、政治桎梏的早春年代,具有強烈的思想衝擊力和解放性,這與我當時的學術思考和理論方向一拍即合、共 振交鳴。課後,我立刻對章培恆教授熱烈地談了一番我的感想。
一次,章先生在課上點名要我就中外小說中的一些問題發言:“你是研究比較文學的,你能不能談談你的理解和看法?”記得我似乎還與章先生簡短談論過明清之際的文化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歷史問題以及早期資本主義萌芽和社會遲滯性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在大學期間關注和閱讀的領域。大學二年級,我曾一度想棄文治史,報考了明史研究生(洋洋灑灑的各科長篇專業考試中我強烈地感到會被錄取),當某名校一位著名的明史專家要錄取我而到處找我時,我卻身在青島海濱、痴迷於晨光碧波沙灘海風,遂匆匆趕回北京,痛苦地猶豫了一番,終於還是放棄治史。這些歷史和文化問題曾是我那時閱讀和關注的許多課題中的一部分。
那時,復旦大學中文系尚有多位創立理論、開創學科、博學多才、蜚聲海內外的第一流學者教授(用現在國內的流行語就是“大師”,不過那時似乎價碼高、標格嚴,人們使用這個辭態度珍惜而慎重,並不矮中拔矬、濫竽充數),他們講起古典文學如數家珍,在許多學術問題上或知識領域裡有不同凡響的真知灼見和精妙辨析。我讀過他們的學術代表作,惜乎未能一一親炙受教。章培恆先生受教於這些學界名家,他好學深思,讀書精博,思維縝密,立論精審,這些優良學術素質使他深居書齋而多所創獲。
後來在賈植芳教授家中,我亦不時與章培恆教授相見。研究生畢業後,我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新學科研究室(不久改名為比較文學研究室)工作。章培恆先生到北京,我曾去北大招待所看望他。二零零六年,一個偶然機會,我帶領加拿大學生去復旦大學辦一個短暫的暑期班。一天晚上,夜色已濃,章培恆教授由談蓓芳教授陪同,乘出租車來到我下榻的樓前,邀我上車去附近一家漂亮的酒樓小聚。我畢業離開復旦已二十二年。上樓時,章培恆教授說:“你也有白頭髮了。”我說:“是呵。這正是莎翁說的‘歲月鐮刀、誰也不饒’。”(“Timedothtransfixtheflourishsetonyouth/Anddelvestheparallelsinbeauty’sbrow,/Feedsontheraritiesofnature’struth,/Andnothingstandsbutforhisscythetomow”,Sonnet60)他告訴我,他患有前列腺癌,還有糖尿病,一直在治療。看他的氣色,我深信他能夠戰勝疾病。我希望他有機會來北美講學。他說,可能沒有機會了。臨別,兩位教授各送我一桶茶葉嚐嚐新。沒想到,此夜一別,竟成永遠。
三
章培恆教授治學,有兩大特點。第一,博學精深、根基雄厚;第二,思想深刻、見解獨到。簡言之,有學問、有思想。他精通中國古代文史,古典知識廣闊而紮實,學風厚重而不鶩虛誇,全無後世“海派”習氣、叫囂之氣,他沉靜紮實做學問,不圖名、不逐利、不追風、不虛榮,數十年來堅守學者的嚴正學品和道義人格,正如其質樸性格、徐徐談吐、緩緩步履;他治學跨越古今之別,思維開放而有理論眼光,立論精審而獨出機杼,寓獨到見解於多年的廣博讀書和精深研究中。他的治學,是論從史出,而非史從論出。“文革”之後,文化熱興,學風卻日漸澆漓,學品日益低下,學術界亦成名利場,寫文章變成登龍術,人們遠離古典而群集現當代,動輒搖筆為文、建立體系、急於求名、渴望以二兩撥千金者比比皆是。章培恆教授的存在,恰恰是對這種時代頹風的抗擊,是對嚴正學風的堅守。我為中國學術界失去這樣一位真才實學、見識卓越的學者而深感痛惜。
章培恆教授二十八歲完成的學術著作《洪昇年譜》(書稿塵封十七年而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就是這種治學品格的一個明證,顯示他在古典學術研究上的深厚功力和文化視野,其閱讀面的廣闊、材料的宏富、考證的翔實、論斷的精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得出,每一條史料的發現和援引,都凝聚著大量的勞動。正是基於這種堅實的學術根基和嚴謹的學術態度,成就了章培恆先生後來的學術發展和成就。從一個人的文字和著作,可以清楚地讀出這個人的學品性格和智慧特點。當年,從這部著作中,我看出章培恆先生的嚴謹學風和遠大前景。
說來奇妙。我那部動筆於一九九零年初、完稿於一九九一年春的《苦難的超度——賈植芳傳》(一九九四年台灣業強出版社出版),談到賈植芳教授五十年代培養的一批出色的學生,首先提到章培恆教授及其《洪昇年譜》(原文為“古代文學史家章培恆出版了《洪昇年譜》”,見第三五七頁)。我給他的名號是“文學史家”。那時,他僅有《洪昇年譜》,尚無文學史著作,亦不知他是否有志修史。章先生和駱玉明先生主持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本)出版於一九九六年,那時我已身在哈佛大學。我給他“文學史家”名號,出於我對他的學術功力和文史通識的洞悉、期望和預示,這一名號對他後來的學術方向顯然是一種超前性預見或強烈激勵;這部廣受讚譽的《中國文學史》及其十年後新版本之問世,恰恰證實我預先給他的“文學史家”稱號之不虛。這是他晚年身心系之、全力以赴的著作,我稱他為文學史家,誠哉斯言。
“文革”前,即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復旦大學中文系名家薈萃、人才群集、各學科師資力量雄厚、在國內高校獨步一時。無論文學研究領域還是語言學領域,名流大家濟濟一堂。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史更是復旦中文系的傳統長項和學術重鎮。郭紹虞、朱東潤、劉大傑諸教授之史著,開創一代學術史研究之嶄新風氣和個性風格,多年來雄踞文學界首席。章培恆先生一九五二年進入復旦大學讀書,授業於朱東潤教授、蔣天樞教授、賈植芳教授等海內學界名家,歷經“胡風事件”之迫害、“反右運動”之風潮、“文化革命”之動盪,堅忍自強、發憤讀書,遂能於“文革”後撥亂反正之際,繼承傳統文化之精華、高揚復旦學術之墜緒、重振人文思想之光輝,引領復旦新一代人跨入二十一世紀。
四
章培恆教授多年前已看到並憂慮國內各高校中文系江河日下的頹敗趨勢,擔憂本校中文系走下坡路。近十年來各高校的真實境況證實這並非杞憂。事實上,中國整個學術界亦面臨文化退步和學術退化問題。
多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經歷多種干擾,特別是十年“文革”時期,一代年輕學子輟學失學,思想戴上枷鎖,知識成為罪孽,凡此種種對人才的培養、學術的發展以及中國文化界整體素質造成深重的負面影響,導致幾代學人在知識上的先天不足或後天失調。“五四”新人文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名家學者、學術中堅相繼飄零,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面臨人才斷層的苦味現實。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世紀交替之際,學術界缺乏品質優良、學問深厚、領域廣闊、氣質雄健、真正富於學術實積和獨創性的大學者。
我在十餘年前撰寫的《胡適、魯迅兩種文化方向的對立與衝突:中國思想文化現代性轉型之歷史透視》(發表於美國)一文裡曾感慨:“他(胡適)培養的這些文史各界優秀人才,成長於清代滅亡之後、五四新人文運動之中,構成新一代學術群體和燦爛之星,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文化界的棟樑。今日,這些學者已然謝世,環顧中國學界,誰堪學術大任?每思至此,不免黍離之嘆。”
近二十年來,在商業大潮衝擊下,在牟利慾望驅動下,在知識界,在高校,為金錢、為創收、為名利、為地位而不惜以人格為代價的各種喪德敗行時有見聞。學術腐敗和人格腐敗是同一個過程。知識者的墮落與知識的貧困、道德的貧困、良知的泯滅構成一體。傳統的樸學之風、道義之風、人格價值,已成鳳毛麟角。
章培恆教授上承“五四”新人文運動中崛起的一代開山立說的名家學者、下啟“文革”後培養的新一代學人,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學術中堅、同輩中最精博的古典學者,他的存在的意義具有雙重性:堅守學術的優質和純潔、追求學術的精進和發展,以及堅守人格的正直、學者的節操。簡言之,即學術品質和人格素養。這兩點應當成為後輩學者的楷模。大學者的成就,不在量,而在質,不在多,而在精,不在拼湊,而在獨創,不在一時,而在永遠。
真才實學、精進不已、守護精神價值者,永遠是對飛揚浮躁、徒鶩虛名、追求實利之輩的警戒。章培恆教授的學術著作,向知識界述說著當代最卓越學者嚴正治學、精密思維、精審論斷的生動實例。章先生有如此著作,可以安眠矣。
猶如海浪沖向卵石疊疊的海岸,
我們的生命年華轉眼就到盡頭。
Likeasthewavesmaketowardsthepebbledshore,
Sodoourminuteshastentotheirend.(Shakespeare,Sonnet60)
這種生命意識應當煥發我們對人類道義和學術良知的堅執,對人格生命和精神價值的熱愛。當我們登臨生命的高峰時,我們可以豪邁地敞開胸襟、面對大海:我的精神事業必將化成人類大地無數繽紛花朵、融入新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成為新一代學子的精神血脈。
2012年4月22日於多倫多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