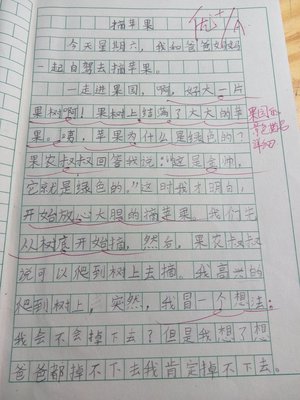十岁的她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独自坐火车到哈尔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群星璀璨的中国女演员中,潘虹无疑是一个另类,无论是在《苦恼人的笑》中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还是在后来令她大红大紫的《人到中年》中扮演辛劳的陆文婷,她一直演着比自己年长的悲苦的女性形象,而生活中的潘虹也比同龄人多了一种忧郁、凝重、内敛,她的一双大眼睛似乎总在诉说着哀怨,这是她生来的“宿命”,还是后天的磨砺?后来,潘虹终于在自己的日记里给出了答案。
当年,潘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后来自杀了,从此,她的身后就少了一双给她力量的男性的大手,她说,自那以后,她一下子就“坚硬”起来,摔跤了,她从来都是立即爬起来就走,因为她知道后面不会有人来扶。
父亲的死,使潘虹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巳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十一点多了,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好的,妈。我去。你别哭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以一种冷静而痛苦的方式“触摸”着自己的父亲,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蚕丝的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镶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母亲把她送上了43路公交车,到了龙华火葬场的门口,潘虹发现全都是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她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
“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进去了很久,出来后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我说带了。‘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我点点头。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在那一瞬间,潘虹的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与其那样活着,还不如这样死了。也是在那一刻,她彻底失去了她的童年,她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给妈妈少添麻烦。
于是,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又替母亲承担了送父亲回老家的任务,她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两夜。
一个遭受白眼的二类右派的女儿,一个在十岁时就不得不接受父亲自杀这种人生“极致教育”的女孩,一个要替突然单身的母亲肩起一些人生负担的青嫩的生命……如果这一切还不能构成她眼睛里的那抹混合着忧郁、坚强、独立的底色,那么,还有什么?
外婆说:你这个小孩,长大了要么做坏事,要么干大事
1973年,19岁的潘虹以自己朴实无华的表演顺利地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潘虹归结为自己从小就不大像一个女孩子,“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孩子,大概也只能当演员了。”
小时候的潘虹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胆子最大,祸也闯得最多。当年,潘虹家的楼下住着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家有一个五斗橱。有一天,潘虹问他们:这五斗橱里面放些什么东西啊?双胞胎回答说:棉花胎呀。潘虹说:不一定。你们拿一盆水从五斗橱的缝隙里浇下去,如果真的是棉花胎,水就会被吸进去。如果不是棉花胎,水就会流下来。这小哥俩居然乖乖地听潘虹的指挥,真的浇了一盆水下去。晚上,双胞胎的爸爸妈妈来潘虹家告状了,结果可想而知。潘虹的外婆无可柰何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个小孩呀,长大了要么是一个做坏事的人,要么就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潘虹至今感激家庭给予她的成长氛围。
“小时候,像我这样极端性格的孩子常常会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然而我家的大人并没有强行改变我,当然他们也不是纵容我,而是在指点我。最值得庆幸的是,我身上的那些为所欲为的东西没有被打击掉,相反,大人们一直在为我身上的这些东西寻找出路。现在看来,当演员就是最好的出路。”
也许是潘虹那耐人寻味的忧郁眼神,也许是她身上那股桀骜不驯的劲儿引起了导演杨延晋的兴趣,潘虹被选中扮演电影《苦恼人的笑》中的女主角———一位在讲真话还是说谎中徘徊的女性,并因此一举成名。此后,电影《杜十娘》进一步开发了潘虹的“悲剧才华”,她开始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
当年,《人到中年》的作者、著名小说家谌容在得知潘虹将出演影片中的陆文婷时,曾当面对潘虹说:“你太漂亮了,不是我想象中的陆文婷。”然而,潘虹却极其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人物,并最终摘得第三届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人到中年》使潘虹一跃成为耀眼的明星。
如果说以前是她以自己本身的外化的忧郁气质去贴近角色,那么当她扮演《股疯》中的小老百姓范莉的时候,就变成了以自己的心灵主动向角色内心靠拢的深刻的悲悯。但这个角色却是她在“赌一把”的心态下的产物。
朋友们是很爱护她的,尤其是在之前《独身女人》、《女人·TAXI·女人》接连遭遇滑铁卢的时候,不过,潘虹更相信“不破不立”的道理,她觉得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其实,促使当年潘虹冒险转型、主演《股疯》的原因,除了中国电影的不景气使她想搏一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刚刚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有种浴火重生的感觉,她迫切地要自己证明给自己看———我还是我,我还要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
最后这样的分手,我不是太狠心,我只是太骄傲
1990年,在潘虹一步步走向成功之时,她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4月的一天,她回到四川成都,与米家山在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离婚手续。潘虹只带了一箱子衣服,回到上海她妈妈那里。这是在拍完《最后的贵族》之后,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回首当年,潘虹感慨万分:“那个时候的我,太年轻气盛了,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比如拍《杜十娘》的时候,我一年半没有回家,而那时我刚结婚没多久。在自己感情的天平上,我觉得事业最重要,出名最重要,而对于自己的家庭,是可以放弃、不做考虑的,当时觉得家嘛,反正回来还是我的家。”
八年的婚姻生活,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有380天。离婚的时候,米家山很有理由地一下子甩出了8本日历,与潘虹共处的日子他都是画了圈儿的……潘虹说她现在要是再有一个家庭的话,一定会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能扛得住吗?
虽然与米家山不存在婚姻关系了,但潘虹每年都会去看他的妈妈,老人和她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不是我的儿媳妇了,但你永远是我的女儿。”
在她的日记体自传《潘虹独语》中有这样的心境———那是1994年的元旦:“从十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我只有自己打点自己。曾经渴望能有一个男人的肩膀,让我靠着憩息。我得到过。可是,这世间总有那么多的不被预料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的琐碎的错误,命运,终于又将我们隔开。”
潘虹与米家山的结合、分手,堪称缘已断情未了。他们依然是最亲密的朋友,中秋的时候,依然会互致问候;遇到事业的沟坎,依然会鼎力相助。正如潘虹所说:那一段姻缘,已经当断则断。这一份亲情,还是藕断丝连,绵绵延延。
“米家山是一个集力量和尊严于一身的男人。过去我这么说,现在我这么说,将来我还会这么说。本来,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美工,我们应该是剧组里最不相关的两个人。可是一部《苦恼人的笑》,给了我一次引起影坛关注的机会,也让我陷入了一段纷飞的流言。你是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的。从南京回成都,在上海转车,一共只有四小时的停留,你执意要我到车站来,你说你要见我,一定要见我……
“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八年,是我已经走过的生命里最棒的八年……杜十娘、陆文婷、曾树生、婉容、徐丽莎,我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被人们誉为成功的形象。但人们不知道,这些剧本的选定,这些角色的塑造,是在你的直接参与和鼓励下完成的。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我想,你值。这八年,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极安全的小窝,这是任何人,无论父母,无论朋友,都无法给予我的。尽管我一直希望我的丈夫像父亲像兄长,娇宠我,呵护我,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过这条人生路,而你的任性你的孩子气,却使我几乎反过来做了你八年的母亲;尽管当我像一只燕子那样衔泥和血把一个窝垒到满意时,家,却在你不经意的游戏间,破碎了。但我还是要为这八年的种种经历感谢你。最后这样的分手,我不是太狠心,我只是太骄傲。”
虽然有着这样奇异的婚配、缱绻的相守、天造的情缘,但潘虹还是可以说出这样的“狠话”:“我一直希望我的名字下面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生。我不希望任何牵扯不清的事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我珍惜我的名誉,也珍惜你的名誉,一如我珍惜我们曾有的爱情,我们曾有的家庭……”
一段似是而非的“感情”,一个完完全全的情人
潘虹曾公开表示她特别崇拜事业有成就的男人,认为一个有所成就的男人给女人的假定性强得不得了。她喜欢男人鞭挞她,一句话把她点破,“因为只有在乎你的男人才会知道你的弱点所在,才会提点你。但你在人格上必须尊重我。”
从小就是男孩子性格的潘虹,身边从来不缺少优秀的男人。这些“哥们儿”给她智慧的启迪,力量的托举,还有相知的感情。被她在书中称为H的那位著名美术家,每次开全国政协会议时都会与她重逢。
“曾有一度,我们的关系被传媒炒得热热的,人们把我们拉得很近。这是大家的好意,是对我们两个人的关心和爱护。可惜,我们俩只彼此看了一眼,就断定我们能做很好的朋友,也只能做很好朋友。H是那种做大事的男人。豁达,有才气,不畏缩。更难得的是他的沉稳里还有一种童心不泯的纯净气质,天生是做艺术家的人。”
而真正被潘虹认可的新“恋情”属于一个叫“赛”的人,被潘虹称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背后托她一把的男人。
“赛永远是这样的,细致、体谅、识情识趣。不像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男人,倒像是受过多年的英国教育,非常的绅士。赛是一个到处走看世界的人。也许是他从事投资咨询工作的关系,他很容易和人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体察别人的想法,使人有信赖感。他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男人,温文、沉着,懂很多东西,但并不夸夸其谈。这种男人会让人觉得有力量,可依靠。我可以毫不避讳地承认,我们是情人。不是男朋友,不是预备丈夫,就是完完全全的情人……
“凡是认识赛的人都说赛待我太好,而我不知珍惜。其实,她们说的赛的所有的好,我都知道,而且比她们知道得更多更清楚。赛是我的第一观众,他是那样地在意我,在意我接的每一个剧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经历的每一种尝试。也许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在意被人呵护,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常演主角的女演员,无论在剧组,在社交场合,还是在朋友圈中,我总是别人注意的中心。我自己都说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可我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心存感激的女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个清晨,赛从冰天雪地的拉卜楞寺打来长途,说:我觉得我是可以为你活着的人。这句话比一句“我爱你”更令我感动。赛当时去拉卜楞寺,是因为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但我们不会有未来不会有结果。他于是去求神的指点,去那人烟稀少之地静静地作一次思考作一次选择。结果,当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就在望见窗外那一片积雪皑皑的银世界的同时,他就下定了决心,就打来了那个长途,说了那样一句话。后来,他还曾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有没有结果不要紧,只要能和潘虹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美好的。说真的,如果我只有二十岁,只为他的那个长途,只为他的这一句话,我便会跟定了他。一如十四年前,为了爱情,便可以放弃在上海的一切,跟了米家山去成都那样。可是,今天我已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了。十四年前我能做的事,今天我不能。十四年前我无须顾忌的事,今天我要顾忌了。”
也许像潘虹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可以不停地在每一部戏中去释放自己的情感,在剧中她总是处于女主角的位置,围绕着她有很多的故事,每个故事又牵涉很多的男人,这常常让她感到自己的情感很饱和,因此仿佛总也没有精力和兴趣投入到一场真真切切、完完全全的现实的感情中。
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生活上,我是个失败者。如今,我只有更多地工作,在事业的摩天大楼,一步步向上攀登,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潘虹说她的单身生活非常简单,也很有规律,闲暇时看书看碟,喜欢游泳,“每天晚上早早洗过澡,泡杯咖啡,看一会儿书,然后刷牙、睡觉。”她还说自己非常不具备团体精神,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同时,她特别强调对朋友要真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