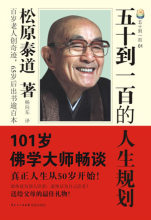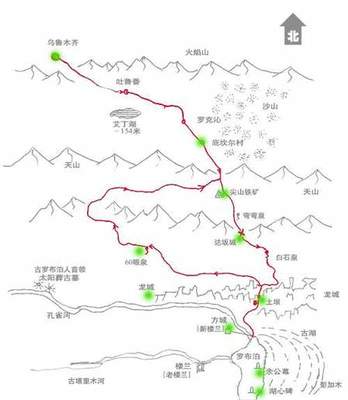多年前写过一篇纪念四五运动的小文,现再翻出来回味一下。
亲身参与36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虽然某些具体细节记不太清了,但很多场面还是历历在目。
那天早晨,我来到广场的时候,发现昨天铺天盖地的花圈被清理一空。不久,人群开始越聚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不知是愤怒的群众,还是公安便衣人员干的,一些外国记者的照相机被抛到空中,而后落到地上砸得稀烂。原来被调来围住广场来维护秩序的工人民兵,此时都懒洋洋的坐在地上看热闹。到了下午,人们开始围攻广场东南角的一座小红楼,后来才知道那里面是所谓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首都工人民兵的指挥部。两边一直对峙不休,外面的群众向里面仍砖头等物,一些人爬墙往里冲,结果其中有人被里面的人抓了进去。红楼里面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向外反攻过好几次,但没有根本瓦解围攻。外面的人毕竟为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当里面的人反攻出来的时候,便象溃堤之水一般四散而逃,成百辆的自行车被踩踏的七歪八扭。但当里面的人一缩回楼内,外面的人又从周围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围攻。记得这中间有一名军人撤退不及,被群众包围追打不已。在这期间,一辆中吉普模样的汽车被推翻,接着燃烧起来。还有一辆为红楼送饭的面包车被人们围住,先是将里面的馒头等食品乱扔,然后又将此车合力翻倒,接着有人用烟头将车点燃......。
傍晚6点钟的时候,广场四周扩音器突然全部响起,传来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警告,命令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我是大约7点半钟离开的,经过北京重型机床厂的时候,看见里面的工人民兵正集合待发。后来听说,这些民兵中不少人是白天跑到广场闹事,而晚上又到那里执行镇压。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的一对远房亲戚,七机部的工程师丈夫到广场参加闹事,而他的老婆却是市公安局的便衣,两人竟在广场上碰上了。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一个熟人的哥哥当时就在那小红楼里负责保卫工作,后来为此立了大功。
1976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除了四人帮和凡是派加以否定之外,中外各界人士各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肯定评价。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一扬人民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事件”;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认为,“这是一场真正马列主义力量拒斥中共教条的运动”。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一场民众反抗中共统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内,以邓小平为首,重新当权的改革势力认为这是一场由真正共产党人领导的,反对极左派的斗争。而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如果你问十个人对四五运动的看法,你也许会得到十种不同的回答。

那么到底什么是四五运动的起因和实质?以笔者看来,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不满情绪已蕴积到了将发生总聚变型爆炸的临界点。的确,除了极少数极左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外,几乎每一个人都不满。不满的原因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工人有工人的不满,干部有干部的不满,军人有军人的不满,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不满,上山下乡的知青更有他们的不满。甚至某些既得利益者也因末能得更大利益而不满。反极左情绪,反新贵情绪,反压抑情绪,甚至“反革命”情绪和反社会情绪笼覃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整个民族肌体似乎丧失了得以欢笑的机制和功能。每一个嗅觉稍微灵敏的人,都可以闻到某种凶兆的气味。谣言、小道消息通过中国特有的折光政治的渠道渗透于整个国民生活中。不满的“瓦斯”一遇火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爆炸。
然而,四五运动参与者的目标及其社会基础决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它是由多种分力聚成的一股总合力。每一个参与四五运动的人都一定会有某种心灵畏惧感。以群众整群众是党内极左派最有效的一种权术。群众揭发运动,真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更可悲的是,父子互相揭发,亲戚互相揭发,朋友互相揭发,师生互相揭发,邻居互相揭发等等。这种亲人和熟人的告密和检举,足以摧毁一个人最终的精神信念。
我访问过一些因参与四五运动而被捕者。人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在群众专政下,即使最初朦朦胧胧地感到自己有真理,但这种自信心立即会荡然无存。其中有一位说:在国民党刑场上,许多共产党人可以从容就义;而我们在狱中决没有大义凛然可言。除非像张志新或林昭那样“疯”了。一个政权和制度的完善不在于是否所有的法律条文,所有的政府机构及所有的行政决策都是完善的,而在于其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是否完善,即是否可以多层次、多渠道、及时准确地得到信息反馈,从而使决策者理性地进行调节和平衡。但要想达到这一步.就必须以民主性和多元性为基点。四五运动的爆发,就是因为民意、民怨、民怒得不到正常与合法的渠道进行疏导和上达;以致于以一种反常、极端,甚至暴乱的形式来发泄。而当时掌握在极左派手中的国家机器根本没有一种随时接受社会反馈来调节自己的机制和功能。从而,非要达到“崩溃的边缘”(官方语)时才可以某种反常形式进行调节。
四五运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渎神与敬神。四五运动给人们一个印象,即一方面把神降为人,而另一方面又把人升为神;不少人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寄托在对某种偶像的崇拜上。二是以自发盲动为主体特徵。卷入这场运动的许多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多数以简单地发泄不满为快。运动参加者们日后的急剧分化。正如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一开始就并非是有一个统一目标那样,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型,他们中有人成了座上宾,有人仍会再次沦为阶下囚。三是运动本身的直接影响虽是有限的,但间接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它为随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者在决策的天平上增添一个民意的砝码,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为日後邓小平的复出打下了重要民心基础,而且尤其为民众的觉醒敲起了拂晓的晨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