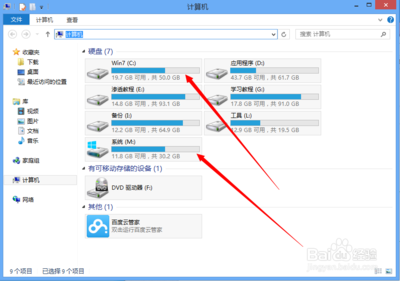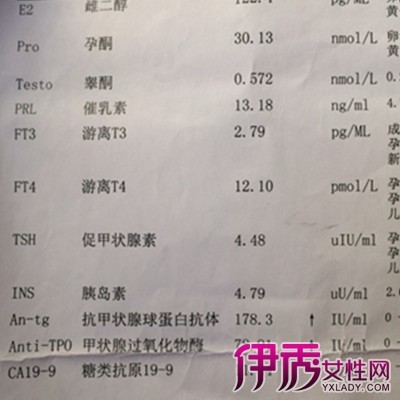尽管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我说的是我暂居北美,而我的家在东北。不是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好像一提东北,人们都会联想到松花江。我家在东北的南端,距大连约200多公里,距沈阳约100多公里。离松花江远着呢,身边倒是有一条河,叫做辽河。在东北,算是最温暖的地带了,但是和北京相比,每个春天气温都会相差五到十度。所以每个春天去北京,出家门的时候会看到光秃秃的树干,而几个小时后到了北京,却能看到那些枝干已经发出嫩芽,当然我指的不是同一棵树。

回到原来话题:尽管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这里的温差和东北的温差原本应该是相差无几的,甚至应该比东北更冷,可是今年这里的气候却极端反常,不知道是不是和那个关于2012年的恐怖传说有关,反正进入三月下旬几乎每天的气温都超越了历史最高的气象纪录——全部突破了零上20度。早听说过多伦多没有春天,从冬天可以直接过度到夏天,春天好像仅仅是一座便桥。这次确实亲身领教了,早上穿着从家里带来的防雨绸大棉袄上街遛弯,回头率骤然增加了若干个百分点,让我多了几分受宠若惊的腼腆。仔细看看才醒悟,原来年轻人已经穿上背心和裤头了。
这句话好像总是绕不出来:尽管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但是一提到春天,我的思维还是会马上穿越到我的故乡东北。
东北是令很多人羡慕的地方,别的不说了,只说说这里的气候——因为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很多体验,但我认为最大的体验应该是充分领略四季的无限风光。如果一个人总是生存在高寒地带,或者是高温地带,那肯定是相当无趣。而四季的风光最令人心仪的无疑是春天。
东北的春天是渐进的。由极寒逐渐变为温和有一个相当长的过度期,这期间的气温会一点点的回暖,极体贴的让人们慢慢适应。然后是土地变得湿润了,变得湿润的土地散发出一种腥味儿,接着,春风来了,像个吉普赛女郎自我陶醉的跳起激情四射的舞蹈,那些小草们纷纷从泥土里拱出观看,而树上的嫩芽也好奇的探出头来,这时土地的腥味儿就多了几分新生儿一样的甘甜与清香,这样的混合气味儿极具穿透力,一旦进入了人们的鼻息,就像酒鬼闻到了二锅头一样,周身舒坦并带动了脑神经的兴奋。
小时候的鼻子是非常敏感的,每到这个时节,我都会兴奋得如醉汉一般,汇几个小伙伴去郊区踏青。此时因为脱去了厚厚的冬装,如同练武术的人褪去了沙袋,周身轻松,有种一纵身就会腾空上天的感觉。我们会一路上鸟儿似的飞奔,选择一块碧绿的山坡,把身体摆成一个大字,尽可以舒适的躺在那些青草地上,看天上的白云随风懒懒的飘动,想象它们会变成哪种动物的形状。会感觉到温热的地气慢慢渗透到脊背,轻柔的抚慰我们尚属稚嫩的躯体,甚至能体味到小草在身下努力生长的倔强。在我们的身边,会有几头老牛默默的吃草,偶尔,会有一只牛抬起头来,朝天“哞哞”的吼叫,感觉那意思如人类在吟诵唐诗一样抒情。
在那些春天的夜晚,我们会齐聚家边胡同口,打了鸡血一样野驴般的撒欢。捉迷藏、追逐、尖叫,总之会不停地疯,春天会使精力异常的旺盛,因此可以尽情的消费。在我们不断疯跑的日子里,巷口的小杨树会一天天的丰满起来,直到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它已经变得异常挺拔秀美,满身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披挂了一身的翡翠。而邻家的女孩也像这株杨树般在一个春天里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我们成了迷惘的一代。刚上到小学五年级就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罕见的一幕:全民性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学生放假。那个春天,我们再也嗅不到了春的气息,因为城里城外到处都充满了热辣辣的火药味儿,原本温婉柔顺的春天提前变成了暴烈的夏天。我们像一群街溜子,整天在城里城外流窜,看大人们像中了邪一样以近乎疯狂的状态演讲、撒传单、焚毁古迹和书籍、牵着“走资派”游街、武斗。被大人们所感染,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戴上红袖标,跟着撒传单、贴大字报、学画漫画。后来证明,消耗了十年光阴的这场政治运动竟然是场祸国殃民的闹剧。这十年,我们辜负了多少个春天的白昼和夜晚?而这十年,正是我们青春期,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
等我们终于有机会尽情的享受春天的时候,可惜却已进入了中年甚至是老年,家庭、事业、社会、人情,很多时候,因为深陷其中,我们丢失了嗅觉,也丢失了感知,儿时对春天的那种感觉和期盼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春天一次次的被我辜负,美妙绝伦的春光在我们的忽略下悻悻的离我而去。
春天在哪里?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能时刻保持一颗童心,就会重新燃烧起青春的激情,春天就会永远和我们不离不弃,即便是已经失去的春天也会悄然回归到我们的生命与记忆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