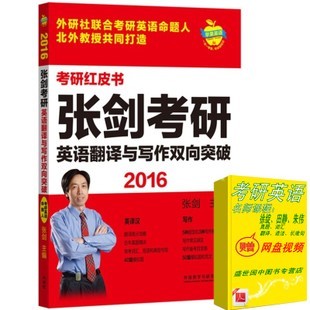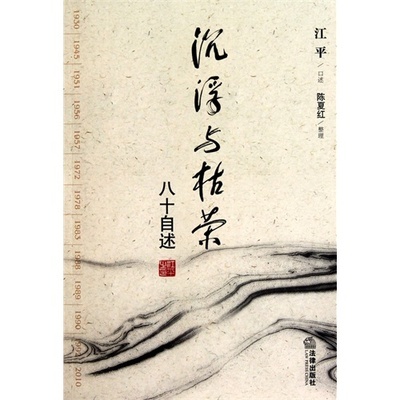吴征镒:九十自述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极言行程的最后艰辛境界。我今忽忽九十年矣。这才体会到九十以后恐怕也是人生历程的艰辛阶段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我在九十岁时作半生总结时的目的,应该如此吧!?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达九十,看来这是因为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少而壮,又逢二战,中间先是军阀混战,十一岁还在家塾又遇到第一次大革命,十五岁(1931)“九·一八”事变又起,1937年我二十一岁时,即遇八年抗战,而后三年内战,好不容易在1949年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却戴着“乌龟壳”(石膏背心)在清华校医院中躺着,时年三十三岁,还是独身。这以后,又有抗美援朝,加上列强长期的封锁;“树欲静而风不止”,国内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我幼年多病,虽在成年以后,因逃难、调查考察和四处奔走,身体反倒好了,但又在六十七岁时左股股骨颈骨折,而又带下了陈伤和各种疾病,七十二岁又因胆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几死,次年做“摘胆”手术,而后双目因白内障等换晶体,耳聋又戴上助听器,以致于到了“主机尚未坏,零件已多不灵”的“多病所需唯药物”的老年境界。八十二岁结束国内外考察工作,以六年时间折节读书,到2006年完成四种自主创新著作。总之可以说:我是患难余生,幸逢盛世!但愿能再多活几年。
回想九十年来,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叙述。
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岁至十七岁)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吴筠孙(竹楼)曾是清朝光绪甲午年(1895)恩科传胪(总第四名),和张骞(季直)同科,游宦到1911年,在湖北荆宜兵备道任上放弃对黎元洪、汤化龙等起义的抵抗,被当地人民以“万民伞”欢送返里,又于民初加入汤化龙、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重新做了江西省秘书长,而后简任为浔阳道尹。我于民国五年(1916年)出生在九江衙内,次年祖父大约因进步党退出北洋政府内阁,党魁又在加拿大遇刺身死,而激发脑溢血不治。我童年时家道中落,“屡遭大故”,到八岁时,父吴启贤(佑人)又因政府欠薪,从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辞官返家,我才入家塾。塾师黄吉甫,是堂房外公,在塾中于读“四书五经”之外,又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自读《袁王纲鉴易知录》,打下了中国文字和文学、历史的基础,同时先后师从张德明、茅以仁、张彭瑜,读英文和数学。至十一岁而遇第一次大革命,家中“测海楼”藏书中的善本遭国民党军官盗走。十三岁以同等学力入江都县中,读了两年,又以同等学力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直到1933年毕业。至十七岁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从此,七十多年间回扬州时间不足一年,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解放前为北平)和昆明度过。所以我是出生在九江,长大在扬州,成人在北京,终生在昆明的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仪征只是祖父应科举时的寄籍,安徽歙县才是曾祖以上的祖籍。
这一期间,虽处于中学学龄,但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特喜吃栽种的新鲜豌豆,采金花菜和看竹笋生长等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1929年(初中一年级)得唐寿(叔眉)先生的启发,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1931年高一时又受到唐耀(曙东)先生的鼓励,并课外读了邹秉文、钱崇澍和胡先的《高等植物学》和彭世芳的《植物形态学》(实为外部形态)。从商务版《自然界》杂志中体会到“边采集,边思考”的优良习惯和初步对植物地理概念的认识。唐老师选用的课本是陈桢(席山)先生的名著《高中生物学》。他见我在前一二年来所采标本,乃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予以展出,以资鼓励。这批标本约有100多种都由我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名和学名,并由我二哥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那时他们同在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这件事对我幼稚的心灵自然很有影响,使我坚定了立志投考大学生物系,而不去考交通大学去学当工程师。入高中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又是“一二·八”之战,一时爱国心奋起,在扬州四乡奔走呼吁,三日之后赋“救亡歌”古风一首,道出了一个无党派的未成年人对于长期内战不停,人民困苦,却还渴望和平和建设国家,一致对外的幼稚呼声,这时我只有十五岁。但在1932年暑假中还由体育教师王小商率领,去苏州天平山、无锡太湖旅行。1937年7月间终于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十三名。那时华北已成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下一目标。
大学时期(十七岁至二十一岁)
从1933年至1937年,我正在“弱冠之年”,得五哥征铠以半薪资助,又靠清寒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那时华北实已岌岌可危,地下火已在运行。1935年何应钦和梅津签订了“何梅协定”,实已出卖了华北。志士仁人(民族解放先锋队)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运动,到次年又有了张学良的“兵谏”——西安事变,事实上日本的亡我之心已经不可遏止,而蒋介石被迫抗日之势已成。我的大学时期处于战乱中,只是由于坚持“读书效国”、“科学救国”,而更加奋发努力。那时清华推行“通才教育”,一则为将来深造打好基础,二来也为了学生就业多些门路。大学一年级不分科,国文由朱自清系主任教授,英文由外文系名教授叶公超担任,其余除通史必修外,理学院的学生必须学普通化学(高崇熙)、普通物理(萨本栋)、文学院学生则必读普通生物(陈桢)。就是这样的必修课扎扎实实读了一年,使来自四面八方程度不齐的青年学得“整齐划一”一些。二年级我得入生物系,但不分组,无脊椎动物学也属必修。在植物形态学班上初识吴韫珍(振声)教授,他所授的课在上课前三十分钟,已将黑板写满,学生必须先去半点钟,才能完成笔记。植物形态学在当时世界上正在开展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的研究,他所用的课本是美国大学课本,为张景钺教授的老师所写,还要参考欧洲的课本Strassburg所写的教科书。他讲课时并不“照本宣科”,而是随时将发表在BotanicalGazette,Annals ofBatany等英、美名刊物上的内容详细介绍给学生。沈同时任助教,实验则是用自制的形态学切片。由于如此教,所以我的“师兄”们中有后来早期研究藻类的江燕杰(汪振儒),完成美白生活史的石磊,和早期从事苔藓研究的王启无、杨承元,还有后来以形态学研究古植物的徐仁等,无疑都是当时的名师高徒。三年级时我又得分入植物组,从吴师习植物分类学和本地植物。后者的教材虽是由刘汝强所编《华北植物》英文版,但分类学课上他都系统地介绍Engler系统、Wettstein系统,并参考Bessey的上位、周位、下位花的演化,和那时刚出现不久的Hutchinson系统,实已将假花说和真花说作为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对立面全面介绍出来,跟上世界发展的形势。他的这门课,由我后来做他的助教三年,而得见其发展。他后来直接选用Hutchinson一元二系的系统讲授,除运用自己亲绘的花果解剖精图,结合当地实物讲授外,特别重视各科或科以上的大类群的系统演化趋势(evdutionarytendences),将Hutchinson所绘单、双子叶系统演化树,从“条条”结合“块块”(大类群)来讲活,现在回想起来,这无疑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受业弟子们后来发展的八纲系统,及其“多系—多期—多域”发育的假说实源于先生的学术思想,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笔之于书”。1935年,李继侗教授于年前赴荷兰进修植物生理学回国,他为植物组开设了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必修课。记得那时国际上初创植物生长素(auxin)的研究,他用Maximov的植物生理的主要原理和实验方法,给学生们所设计的小而简单易行的实验,足以使他在课堂上讲得更加鲜活起来。植物生态学记得是四年级植物组必修,他选用Schimper、Warming、Haberland、Raeunkiar等名著作参考,而讲授时则用历年清华师生在北平,远达小五台山、易县等处森林群落的实际调查作为材料,系统介绍了群落学和植物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野外观察方法,尤其是以植物地理分布的观察由个体而群落组合,循序渐进的入门方法,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特别是他惯用的简易的由远及近、远近结合的讲授方式,首先掌握特定地区的植被类型和气候顶极,尤其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将生态学的野外基础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和其地理分异的基础上。总之,在入系分组的三年中,打下了我今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到了1936年夏天,植物组学生又在吴师和杨承元助教的率领下,亲赴小五台山作野外考察采集,并搜集四年级毕业论文材料。此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已定为“华北的莎草科——薹草亚科的分类学研究”,为的是选一个疑难较多的类群,从切实的囊果(utricle)和果颖的精确对比入手,先从优势类群入手,而后再选点深入的方法,解决薹草亚科两个属的分类问题,使之成为华北植物志的组成部分。此外,在此形势危急的四年中,除了将所开的必修课(含严楚江先生开设的植物解剖学)和选修的动物组课,包括比较解剖和动物生理全部修完以外,又读了化学系的定量分析、有机化学和地学系地质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课,从而更扩大了基础。至于陈桢先生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史,那是动植物两组的共同必修课,就更不用说了。陈师和吴师实际上从动物和植物两个方面,用达尔文进化论及其遗传、变异基础连贯起来,使学生对生物学有了全面理解,在毕业后,能走上各种有关生物的岗位。可惜那时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有,那系里是会设法开设的。三四年级时有大半年参加学生运动就过去了,但我既没有加入“民先”,仍然抱着“读书救国”论,于“七七事变”前一天,以第一个月任助教的八十元大洋的工资,参加段绳武发起和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去了大西北、内蒙古和宁夏。从此,所有的童年至青年的学习笔记、实验报告以及毕业论文所附的自绘精图便一扫而光。
抗战八年(二十二岁至三十岁)
我步入社会和步入机关是从抗战八年开始,“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目的原是运用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思想“移民实边”,是段绳武打算把河北省中部农民引去“河套”开荒的,团员由于自费,成分很杂,除他请的土水利专家外,调查植物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历史(有回族白寿彝教授)、法律、社会、新闻,乃至党务都有一些,我在其中倒显得异样。一个多月后通过调查采集,我初步认识了草原半荒漠和荒漠,每天在“朝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下工作。但等到我们过了贺兰山缺,在蒙古王公(达王)府中时,已是8月23日,闻北平沦陷,回不去了,于是团里发放剩余旅费、伙食余款给各人,无结果而散。所有梦想都成泡影。我和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卜姓同学,乘最便宜的黄河船,一个漏底的“方舟”下河曲,到包头,又乘火车转大同、太原、石家庄,辗转到家,分文不名,就此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刚上扬州震旦中学教生物一堂课,就接到李师来电,叫我速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大学行列。旋即又与张澜庆等先到南京,时正值日寇第一次大轰炸,中央大学大礼堂后墙成一大窟窿,旋登舟去武汉转长沙。从此离家达九年之久。
三校初合,助教人浮于事,李师叫我参加清华农科所做调查研究工作。于是和周家炽、王清和、朱宝(弘复)、毛应斗、郭海峰等七八人在岳麓山后左家垅,工作并住在清华农学院工地小院中,除在岳麓和衡山采集标本以外,谈不上研究,日唯读剑南诗抄。从衡山归来,长沙小吴门东站遭第一次轰炸,我所在圣经学院只数百米见墙侧飞来人头,面目如生,乃知近代战争的残酷。12月底,大哥(吴白)和七弟由南京辗转逃难到长沙,始悉家中一切。大约12月中,长沙临大酝酿迁昆明,仍由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次年1月中,我遂随李师,并毛应斗、郭海峰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步行,直至1938年的4月28日,清华校庆日抵昆明,此次逃难有日记载于《笳吹弦诵在昆明》一书中。联大虽只有八年的实体存在,却与国同运,而这八年,正是我在清华毕业后初尝人生酸甜苦辣的八年。
1938年,初到昆明,那时的日子还好过,这一年6月至7月和熊秉信(熊庆来先生长子)在昆明四郊调查采集,他研究地质、古生物,我则采集植物和记载植被,一个月已大体认识到昆明一个县就有比河北一省还多的植物区系,不同海拔、不同岩性上有不同的植物和植被。喘息甫定,接着又随张景钺、吴韫珍二师和周家炽、杨承元、姚荷生等共6人组成一个小的综合考察队,到大理(苍山)、宾川(鸡足山)采集调查,目的是寻找实验材料,因此藻、菌、地衣、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一应俱全,不但亲受二师指点,亲身体会,也得诸位师兼友的切磋琢磨。初次见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植物和植被,使我眼界大开。归来两个月后又随李继侗师参加一个更大规模的滇西南考察团,目的是为赈济委员会选择一片荒地,以便迁移难民。此团为社会调查(李景汉)和团长林×、民族(江应梁)、地质(王嘉荫)、地磁(张丙吉)、林业与森林(李师)、动物(北平研究院陆鼎恒)等二十多人的“综考队”,沿着第一次开通的滇缅公路,从大理下关,经漾濞、永平,过两座尚被常绿阔叶林覆盖着的山顶(太平埔和黄连埔),过澜沧江功果桥,下保山坝,然后又下怒江桥,经六库到芒市、遮放、勐卯(瑞丽)这三个以傣族和景颇族为主的地区。这条公路横跨过三大峡谷区的中下部,我们师生在刚取得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灌丛五彩缤纷的印象后,又看到亚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包括河岸林、稀树灌丛和有刺灌丛)等等。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又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除人生以外的植物学感受,进一步提出了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弄清全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问题,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考察也是各自有些收获,但无综合结果而散。这一块边陲宝地于几年后随珍珠港事变也被日寇侵占,但我还是系统鉴定,写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入》。因为其中有一鸭跖草科植物,采于景颇山上,当时缺少文献资料,无法确定,遂被搁置。直到1945年,联大生物系标本室的右邻——清华农科所昆虫组的陆近仁教授怂恿我投华西边疆学会汇报,才于1946年刊出,但只列出前半部分,即含椴树科扁担杆新种二个,植物采集名录的后半部分又由于联大复员和三年内战,尘封至今。
好景不长,到1939年,杨承元因三年助教期满,举家去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教书,那里的待遇优厚一些,这一年我就无法再做野外工作,眼见朱宝和姚荷生赴车里(今景洪)。1940年后即物价上涨,中间思普茶场(今勐海南糯山)的白孟愚(回族,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相识),首邀我去西双版纳,因生物系无经费出外考察采集,只得困守昆明。我在用“洋油箱”堆成的标本室内,将没上标本台纸的标本,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氏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将几年所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标本系统整理和鉴定。
1940年夏我也三年助教期满,李师认为我还应扩大基础,劝我投考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由简焯坡接替助教,是年我同逃难来滇的八级生物系同学王伏雄同时考取导师张景钺教授的硕士生,王做裸子植物胚胎学研究,我做杜鹃花属花部维管束结构的研究,这都是当时形态学的前沿。可惜入学不久,又是日机九架轰炸西南联大,新校舍南院有两三幢土墙洋铁皮盖顶的实验室被毁,标本室幸未中弹。但从此就开始了逃空袭生活,一直到美军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来昆。我和王伏雄于是被疏散到大普吉清华农科所,一边上戴芳澜先生初开真菌学课,一边做硕士论文,一边继续做文献和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所有主要文献系吴师在赴奥京向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韩马迪(H.Handel-Mazzetti)要来的中国植物名录,从此一直做了十年。除了蕨类以外,凡秦氏所拍Kew,Wien,Uppsola的Thunberg标本室的Thunberg模式都做了。如果文献有而照片没有,就随手用各种纸张如上有青天白日旗的废旧文凭,也和照片卡片一样写上去,意欲编写一部“中国植物名汇”,这一些卡片先后达三万张,对我日后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很有用,从而也促进了编写植物志的专科工作者的查阅,其所写国内外植物分布记录也是我以后钻研植物地理的基础。特别是由于精读标本上陈年记录,使我既熟悉了采集家和研究学者,也熟悉了该植物的各种小生境,和各种植物地理考察记录相结合,各种各自在群落中的位置,也就了如指掌。大约在1950年以前的中国植物的有关记载不致太短缺。其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植物所的王文采、崔鸿宾、汤彦承等在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时发挥了一些作用。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后方民众生活日益困难,吴韫珍师只身留在昆明,贫病交加,又因新接受经利彬的聘请,在教育部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兼差,决心要将胃病治好,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动手术,不幸病未能愈,却因在缺药情况下,内外伤崩裂,转腹膜炎不治,而于1941年6月英年早逝。他的一切教学任务和新待开辟的《滇南本草图谱》工作不得不由我承担。以后数年,由于昆明缺乏植物分类学师资,而个人生活也日益困难,所以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也由我兼课,但我主要住在大普吉清华农科所院中,而在附近的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与匡可任、蔡德惠在1941—1945年前后一年,实只三年中,自写、自画、自印(石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计25种26幅图,印成于1945年4月,但未能公开发行,该所即停办。这本书是在1939年中与吴师共同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云南植物,尤其是云南的草药和野生花卉开始,而以此书告终的“植物考据学”工作的成果,且也是中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1945—1946年间,迁回昆明,从此主要精力集中在办私立五华中学和参加学生运动,除继续写卡片外,业务了无进展。然而闻一多师于1946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刺杀,以及蔡德惠于书成后早夭,又都进一步促使我在政治上觉醒,决心投身革命,1944年入民盟,1946年入党乃是必然结果。
三年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科学院接管和整理时期(1946年8月起至1952年,时年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
1949年5月,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
抗战胜利,内战旋开,1946年8—9月,复员回北平,立即参加多次学生运动,和在新诗社、剧艺社活动,在讲师以下阶层中组织成“讲助教联合会”和“职员联合会”,后者由吴师长子吴人勉和王志诚牵头,外则参加民盟北京市委历次发起的签名运动。至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后,9月党即让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区泊头镇,10月又经河间、保定、涿县、房山门头沟回到北京外围青龙桥,参加接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工作。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后,参加北京市军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接管市内大专院校、各系统研究所和文物单位的工作,后文化单位和普通教育分出,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我任高教处副处长。5月参加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此后因触电跌伤腰椎,须疗养半年,而调回清华生物系,在校医室内度过当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初在系里认识段金玉。至12月,刚卸掉石膏背心,即调入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恽子强、丁瓒任正副党委书记,我与汪志华任党支部正副书记,但全院党员共只七人组成党组管理一切,北京各所都无党员。
1950年初,国民党留下相互对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生物学方面还有两个私立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了消除它们之间的“门户之见”,组织了以钱崇澍为主任,我为副主任的静生所整理委员会,实质上是科学研究系统整理、合并、新建、重建工作的试点。经过一个月的工作,终于较完满地将静生所、北研院植物所合并,而改名植物分类研究所,钱为所长,我副之。从而也解决了科学院办公室房屋问题。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分因已无研究人员,乃将北研动物所改建昆虫研究所,而将其余动物标本请陈桢先生主持成立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以后扩建为动物研究所,又将昆虫所并回。
我从1950年2月起任北京植物所研究员兼副所长,至次年在当时西区(即今动物园)内各所包括北研历史所建立民盟组织,吸收北研的林镕和静生所的张肇骞入盟,俱由科学院任命为副所长,自己退居第四位。初时所中只有北研和静生人员,均为植物分类学方面人才,至次年侯学煜自美归国,俞德浚、钟补求自英归国,中央研究院系统的王伏雄、喻诚鸿、段续川等自愿来北京,乃分别建立了植物生态、植物形态(初包括细胞学)和植物园,由科学院决定扩建植物分类所为北京植物研究所。至4月间随原北研动物所所长张玺赴青岛,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定所址,遂与童第周、曾呈奎、王家楫(时任中研动物所所长)共商,选好所址,同时确定了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建所轮廓。同年,与朱弘复(即朱宝)随竺可桢副院长组织的科学考察团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日、俄、伪留下的各种研究机构,实为以后建立东北分院各所探路,武衡始加入科学院的领导行列。此行我和朱弘复还考察东北各省的自然状况,在伊春的原始红松和落叶阔叶林中考察,并初次见到大兴安岭的落叶松林。归来不久至8月间,参加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与汪志华、曹日昌、黄宗甄等为大会主席梁希教授致闭幕词的起草和执笔工作。自此以后,全国各种学会联合成“科联”,而科学社、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包括在国外建立的)、工程师协会和科学时代社等民间组织、群众团体,合并为科学普及协会(简称科普),这两个组织以后又合并而成全国科协。11月又由农业部、高教部借调,与农业部三位中国专家(陈芳济、孙××等)和两部工作人员杨明华等14人,组成工作团驻北京农业大学调查“乐天宇事件”,这是由于乐天宇同志的工作作风问题和强制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引起校务委员会各党外老专家,如汤佩松、戴芳澜等的不满,以及李景钧教授出走香港引起的。事件真相大致清楚,教授情绪初步稳定工作尚未结束,又奉科学院命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地区栽培植物起源”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行有三重使命,首先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又是在二战后新兴国家印度召开的,所以临行前我和侯学煜由周总理亲自接见指示:“多交朋友,多了解情况”;第二重使命是在过香港时争取李景钧返国;第三重使命是争取陈焕镛回到科学院,争取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殷宏章和在印度Sahni古植物研究所任所长的徐仁归国。该团由陈焕镛任团长,我和侯由北京出发到广州与陈会合,徐仁则在印度参加。过香港时找到李景钧教授,告诉他国内情况,但他不肯回来,其余任务都顺利完成,于2月间返国。写成报告回国内宣传考察印度、历时两个月的结果,是我解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这一年的一个星期天(4月22日)与段金玉结婚。两个月后,在所内酝酿编写《河北植物志》,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植物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初次将钱崇澎、陈焕镛、胡先骕三老以讲笑话的方式为《中国植物志》促进了一下。
同年7—9月,由于抗美援朝开始,我国遭受以美国为首列强的封锁,而工业的恢复与振兴又需要橡胶种植业和橡胶工业,此时蔡希陶已在云南南部展开野生橡胶藤的调查,颇多种类被发现。上海时已由罗宗洛将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生理部分集中扩建;所中罗士苇建议种植橡胶草,而海南、云南方面在接管时,前已有华侨引种巴西橡胶树成功的报告。于是由陈云副总理亲自抓,我和原任华东农业部长的何康同志都参与其事,这是我们参与开创橡胶种植业的开始。研究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并由陈云副总理做战略决策,认为橡胶草和橡胶藤的提取工艺,一时难以解决,决定在我国南方的常年无霜地区,如海南那大原私人胶园已有成年大树,云南瑞丽也有种胶树成功的片段,乃定出组织大规模在海南、广东、广西进行的宜林地调查,并继而调集退伍军人,大规模开荒种植。自此以后直到1958年,六年间我的重点工作都和橡胶发展有关。旋又由农业部借调与该部王司长、陈仁、马XX和农业科学院董玉琛、黄玉珉等5人,陪同苏联捷米里亚采夫农业科学院伊凡诺夫院士赴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华南考察,遍及全国农业和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此行遍历了中国从东北到广东的东南半壁的农业地区,加强了实地考察和受到与大农业有关的思想认识教育,受到与农学有关各科学家的启发,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浙江萧山集约农业,以及广东顺德的“桑基鱼塘”式的循环农业经济,很受启发。是年10月,原从华北解放区入城的由乐天宇领导的遗传实验馆也并入北京植物所,由我去接管,馆中有胡含等研究人员,以后逐渐扩建形成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约略同时,属于北京农业大学,以戴芳澜为首的真菌学部分,曾一度归植物所领导,以后与方心芳为首的曾在黄海工业研究所的细菌学部分合并成立为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这一年中,还和杨森(当时刚从部队调入科研机关)一起赴南京接管中山植物园,并将原中央研究院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部分人员,以裴鉴(钱老女婿)、单人骅为首的植物分类学部分合并为植物研究所华东工作站,以后又独立为南京中山植物园。这解放后三年,我所以如此匆忙奔走,一则反映当时在科学界党的力量非常薄弱,二则反映生物学在解放前虽属仅次于地质学的强项,但中青年力量断档,植物学界更不例外。
一波三折时期(1953—1965年,时年三十七岁至五十岁)
雷州半岛“斩岜烧岜”,是我亲身实践热带林业和橡胶种植的第一次
1953年初,由于科学院将派遣访苏代表团,各个学科都在做准备,我就选读了中国自1916年钱崇澍在国外发表的分类、生理、生态三篇文章,就以后的主要论文精读,并摘要写成《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即植物学者专科报告)一文,以备向苏联学者交流。同时着重学习胡先骕、刘慎谔和黄秉维等有关中国植物地理分区的问题,初步形成中国区系和植被分区以兰州为中心的三大片的轮廓概念,并以青藏高原作为屋脊,向北、向东、向南降低的系列,整理我十年名录工作中所得印象,将各区的特有属作了初步的归入,这就是我后来作植被类型分类和中国植物分区的草创。此团在2月底组成,以钱三强和张稼夫(时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为正副团长,科学院内有华罗庚、赵九章、张钰哲、冯德培、贝时璋、朱冼等,院外有梁思成、吕叔湘、沈其震、张文佑等共26人,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欧,于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以后又访问了列宁格勒(后改回为彼得堡)、基辅、新西伯利亚和塔什干,在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会见了苏方的许多院士,但我们以学习为主,并未用到前述的两项准备。至5月原路回国,6月在长春进行各科的总结。在苏联参观学习期间,我多和马溶之(土壤)、李XX(农业)在一起,故而除植物学研究所外,也参观了不少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还见到了李森科院士。我们的俄文都只在识字阶段,幸得在苏联读博士生的汪向明同志的全力协助。当时正值向苏联一边倒的高峰中,苏联科学、教育各方面也确实比我已看到的我国和印度的科学研究先进得多,学习真是做到“有闻必录”(华罗庚讥我之辞)。故而写成的报告除内部者外,共发表了三篇,《科学通报》和《植物学报》都予以刊载,虽不免有些“教条”、几乎连苏方介绍者的原话一字不漏地宣扬,但始终是客观介绍,没有联系国情分析批判,更没有随便给中外学者扣帽子,故而虽然会见到李森科,用他的观点和原话宣扬他,但并未使国内学者反感或攻击,以理服人,综合分析不厌其洋。当然在以后看来,当时苏方的“个人崇拜”和“阶级偏见”,对作为生物遗传本性和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过于偏向环境条件,甚至无视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并用行政强制推行一个学派的论点还是随处可见的,今仍其旧,一并刊出,以供读者分析和批评。此行所学的积极方面是在竺副院长领导下,“遗貌取神”地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有重点的大规模综合考察,于是下半年开始北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在南方则以橡胶北移和其他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为重点分别组成综合考察。另一个则是由竺副院长领导地理、气候、土壤、水文、动植物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我国自然条件和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的工作。两者都可以认为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贯彻。前者是我在1953年冬季开始研究橡胶宜林地北移,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工作参与热带植物区系植被调查研究的开始,后者则是我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论文《中国植被的类型》和我国第一张植被图(实系植被类型复原的植被图)的张本。
正在这些调整、调查、新建生物学各有关所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粤西、海南和广西南部的橡胶种植业,已在李继侗师于1952年初领导全国院校生物系师生开展这三处自然环境大调查后的基础上,由退伍解放军开辟而建立的橡胶种植场,由于遍地开花,上得过猛,加之用拖拉机开垦,挖出热带杂木林树根而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和橡胶生长不良的问题。新成立的农垦部由王震领导,何康时任司长,向科学院求助。院部随即派我和新成立的南京土壤研究所(从地质调查所分出)的马溶之所长、李庆逵研究员以及新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扩充转化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罗宗洛所长一行四人,赴琼、粤等地考察,我们在广州与广东农垦局局长李嘉人接头后即赴现场,与农垦部派许成文、郑学勤二人,以及当地农垦部门领导和技术人员先到海南西部考察两株老胶树(王牌树)的生态和土壤环境,然后赴海南岛东西部和雷州半岛的新建橡胶种植场。考察后,经过我们三人对植被、土壤的考察,和罗所长对于橡胶树营养生理条件的调查研究,经相互讨论,终于确定放弃粤西、桂东沿海、海南西南干旱沙地以及龙州一带石灰岩土上的种植橡胶场的计划,放弃拖拉机农业措施,改用马来一带的“斩岜烧岜”(即刀耕火种,但不再游耕),“大苗壮苗定植”,以及用本地树种栽培和营造防护林,在未选好林下覆盖植物之前,先尽量利用林下次生植被等防护措施,从而初步稳定了华南的橡胶种植业。总之,这次考察是我向罗、李、马等学习的一次机会,也是我亲身实践热带林业和橡胶种植的第一次。由此将解放后,我自学卢鋈的《中国的气候》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自然地理》、《植物地理学》(阿略兴),以及Richards的《热带雨林》等书,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在脑海中首次形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粗浅轮廓,实际感觉到植物、土壤、气候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而为以后要致力的热带生物地理群落,实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
就此,这一年冬季我就和朱太平参加了海南岛西部,以那大为中心的植被和土壤调查,与南京土壤所张佑民、赵其国等,共三处同时进行综合考察,徐闻队由焦启源、曲仲湘领队,海南东路由林英、黄成就领队,复旦大学刚毕业的七名女生(陈灵芝、胡嘉琪等)分别参加粤西(徐闻、海康)和海南东路,华南植物所派何绍颐、周远瑞、王铸豪三人参加,都是新手,这个阵容已经是当年植被和区系及土壤综合调查的主力。
从1953—1955年三年中,每年率综合考察队赴海南,而最后一年又从粤西到信宜一带,并经北海一带到广西、西南的龙州、友谊关,时法国和越南已开战,旋又到南宁、桂林总结工作,从而初步结束了华南热带资源考察队的工作。这几年中我开始认识华南热带季雨林,特别对其次生林和灌草丛等热带植被的分布、演替等规律有所了解,其他稀少的为原始雨林、海岸林、红树林等则是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但对热带北缘的特点,季风、台风、寒潮和石灰岩区干旱仍有切身体验。在此基础上重写了植被初步分区中有关热带植被的部分。
1956年苏联科学院提出和我国合作,研究解决紫胶虫北移至苏联的寄主问题,初由科学院派刘崇乐率队,蔡希陶在云南就地参加,赴保山、龙陵、德宏等地,苏方则由Popov(动物)及其女弟子、Fedorov等三个植物学家来华,当他们一行到大理专区时,院计划局又派我和简焯坡二人赶去。至次年乃由刘为正队长、我和蔡副之,正式组成西南生物区系及资源综合考察队,实以橡胶宜林地和紫胶寄主国两项重点,苏联专家的任务只是动植物区系调查和采集。
此行既先到德宏一带,于我是旧地重游,植物区系和植被都比较熟悉,遂受苏联学者给我以“植物电脑”的谑称。到第二年由我陪同植物学家三人转移至屏边、金平一带,适逢大雨初至,未能完成在大围山搭草屋采集的任务,又有北京动物所调查蝴蝶的李传隆坠马受伤的惊险,只好提前下山,并顺便考察了引种金鸡纳的种植场。有此两年经验,第三年队伍大为扩大,并集中在西双版纳一带,刘队长则率有关专家和人员赴景东筹划建紫胶虫工作站。在西双版纳调查了两年,至1959年,在普文一带与侯学煜、曲仲湘陪同下的苏卡乔夫院士的队伍会合,筹划在西双版纳建立热带生态地理群落定位研究站的工作。我和Fedorov等三个植物学家则到大勐龙,但找到了较普文龙山更为典型的热带雨林片段,那时勐养还未通勐仑、勐腊,更没有发现望天树林Parashorea,大勐龙小街的曼仰广龙山其实仍是次生雨林。大约1957年,在滇东南工作结束后,曾和dorov等三人首登峨眉山,上下各三日,次年去青岛。至第三年(1959),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植物学家之间的合作尚在高潮中,是年我和Lavrenko、A.Takhtaian、Sokolov院士等三人正在大动力之际,当时从小勐养到勐仑和勐腊的公路始通,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所长Baranov(形态学家)又由王伏雄等陪同,到了西双版纳,于是我们合流,同到勐仑的葫芦岛勘查热带植物园址,从而为现在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确定了园址,随即分去昆明植物园的主要力量创办此园。到1960年,仍由苏卡乔夫派遣森林土壤学家Zonn和森林生态学家Delis为大勐龙群落站调查和设计实验项目,主要是森林土壤和残落物、凋落物关系的观察实验。我方旋即由李庆逵和我亲去为简陋的站址奠基动土,而北京植物所的赵世祥同志也由于雨后两次过河,被浪卷走。
从1953年至1960年,是学习苏联经验,并和苏联学者合作的始末。
1958年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一年,也是我一生的最大转折点,是这一个“一波三折”的转折点。是年初的一天,忽然周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同志到我在中关村时我和汤佩松为邻的宿舍来找我,他说,总理要到广东新会视察野生经济植物利用和废物利用等问题,要我作随身工作人员,接着由总理办公室童小鹏主任接见和安排。此行约一月,亲见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在这两方面的出色工作以及葵扇工厂、葵筋牙签就是在总理视察时的指示下作废物利用制成的。此行听了总理大报告,和他在来回的专用船上的亲切讲话,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只身只由我和罗青长陪同,视察江门新由波兰援建的糖厂。年终在云南继续考察后,回到北京时姜纪五同志已调植物所任书记和副所长,他热心于亲自抓植物资源组的工作。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寻一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创树,才对得起这一“学部委员”头衔。时张肇骞已先一年调往华南,协助陈焕镛工作,我遂毅然请示调往云南昆明,与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学研究上了结我的夙愿。得科学院党政领导首肯,乃正式调往当时新设立的由刘希玲领导的云南分院,该年浦代英已先调昆明,我去后就形成了领导班子。从此,是我先参加领导植被调查工作四年,而后又领导植物资源组工作四年,至此又回到分类区系工作上来,从而完成了“一波三折”的我一生中的大转折时期。此时我就体会到研究植被和植物资源必须先过植物区系这一关,说白了就是如果不认识植物,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自此而后,乃以主力承担《中国植物志》这一巨大历史任务,并创始了《云南植物名录》和《云南植物志》的工作。我实际上不是“跃进”,而是“跃退”到区系关前,尽力搜寻各科、属的最晚近的专著,将要鉴定的全部种类摊开,进行对比研究,尽力“取法乎上”,使鉴定比较准确,不致重复。同时也可见各属下的系统演化趋势,各种间较可靠的划分,以及其地理分化的规律。自1959年11月以后,逢开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必出席,在俞德浚主编病逝后,还任主持,先后达四十年。
1961年2月随竺可桢副院长在广州开热带资源开发利用会议,实即从1953—1961年,先后八年间,有关热作综合调查研究的总结,此行记得有顾准参加。我在会上首次提出“开发热带作物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区,以保存和继续观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一建议后由钱老、陈老等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提出议案。我又和寿振黄在云南省提出建立全省24个自然保护区的具体建议,并在热带勐龙、小勐养,首先由曲仲湘率队进行本底调查,这可是我涉足保护生物学的开始,现我国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大事业。在这个会上还讨论了橡胶、油料代用品,以及热带红壤的严重水土保持问题。此次会议的同年9月后又向新成立的综合考察委员会漆克昌主任汇报云南综考队的工作张本。云南橡胶宜林地的选择标准问题自此初步结束,以后就转入西双版纳的热作开发建设等工作;同时,小勐养、勐仑和勐醒等三处的自然保护区也予以划定,因橡胶宜林地属保密性质,故云南综考队没有对外公开的工作总结报告和论文发表。
1961年在姜纪五同志的领导下,北京植物所与国家商业部合作,开展了1958至1959年的全国性的经济植物大普查,国务院并发表了全国进行“小秋收”的指导性文件。在此基础上集体写作了两卷本的《中国经济植物志》,此书原由内部发行,以后逐渐公开。从业务上讲,我是该书的主编。
1962年,在郭沫若院长和文化部夏衍同志赴古巴考察之后,他们归国时曾参观昆明植物分所,郭老写下了四言诗一首。5—6月间院部又组织我率华南所两年轻同志赴古巴作热带植物考察,我们取道苏联,重访莫斯科,乘火车至捷克斯洛伐克京城布拉格,然后乘捷机经爱尔兰越大西洋,达加拿大的东北海岸,再循北美大西洋岸南下,经佛罗里达领海上空,直达古巴京城哈瓦那,随即被接待至“猪滩”(吉龙湾),并从古巴中部由东而西,后由北而南,遍历了古巴全国至海外松岛。这是我首次到新世界,并见到加勒比海植物区系,虽然只采了少数植物标本,但却在其南岸原为Arnoldarboretum的热带分园内,采得各种树木种子共一大柳条包,托时在古巴作外交访问的卫生部长李德全带回国。这批种子是当时在美国封锁条件下漏网的首批热带植物,有酒椰子Raphia、香果Casimiroa(芸香科)、猴面包树、轻木、象耳豆等等,均分给西双版纳植物园和海南那大的热作学院植物园种植,其中有些至今已成大树。此行得我国驻古巴大使申健的大力协助,申是旧相识,12年前他在印度使馆任一秘。不但如此,此行也为后来赵其国(土壤学)、郝诒纯(微古生物学)赴古巴作援助专家作了铺垫。
从古巴归国不久,8月又和云南大学生物系朱彦丞教授,北京植物所研究生陈艺林等赴丽江、中甸进行植被和植物区系调查,历时约两个月,开始作进藏的准备,并学习法瑞学派的原理和调查方法,朱则也要植物分类学者和他合作,因而以后被邀在云南大学首开植物地理课。此行正值雨季搭帐篷,生活艰苦备尝,但能见到大片高山草甸、亚高山针叶林和多在阳坡的高山栎林,心情也大为开畅。中甸之行在次年又举行了一次,并到了德钦,且登上哈巴雪山海拔5400米的山顶,也见到了中甸白水台的钙华景观。
在大勐龙的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观察实验站,自1959年开始工作,已历时五年,乃于1963年3月在景洪召开四年(1959—1962年)实验工作总结,除李庆逵和我外,还有竺副院长和北京植物所汤佩松所长。四年来的实验记录已可见群落下土壤中矿物质的流转情况,但由于林中小气候梯度观察一直未能进行,待到1964年而终于夭折,甚为可惜。此站如工作至今,当为世界上在热带林内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先例之一。当所内议决将此站并入勐仑植物园时,我不禁下泪。从此,结束了我对热带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也从此杜绝了我踏入实验室的脚步。至“十年动乱”后而将所中的土壤、微生物等部分一律划出,微生物部分后归云南大学,于土壤中的放射菌颇有创获,这是后话。
1964年1—4月,与北京植物所汤彦承、张永田组队赴越南北方,和越方合作进行植物区系考察,在越南度过新旧两个“乙巳年”。名为合作,但越方只有年轻人,由阮X率领。此行几乎足迹踏遍黄连山、凉山,北至3000米的Phansipan以下,南达清义,北越和南越的界河,东北达下龙湾和汪必,但西北的莱州和东北的石灰岩区高平未到,举凡沙坝(Chapa)、三位山(Bavi)、三岛(Tamdao)等法国采点都有所涉猎,见到不少以喙核桃Annamocarya、马蹄参Diplopanax为标帜的原始林段,也漫游于有福建柏Fokenia为大树的林海残迹。但所采标本2000余号,至“十年动乱”期间,才由李锡文整理成名录付与越南。此行收获在于肯定了越南北方至我国南方的区系相似性,及其从第三纪以来共同的历史发展背景,这些都充实了随后我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一文的内容。归途经老街过红河桥到河口,而返昆。接着准备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非拉科学讨论会,我将该年C·G·deDallaTorre&H.Harms发表的Genera Siphonogamarum adSystema Englerianum Conscripta 1907)所载的世界植物属的分布记录,结合我在1940—1950年间,据秦仁昌摄的模式标本照片所做卡片的国内外分布记录进行了系统分析,按照自创的地理成分和历史成分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将当时我国已有记录的1998属加以分析,归纳为15个大分布区类型和三十几个变型,起草成《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一文,作为大会交流的八篇论文之一,在新建成的北京科学会堂上向亚非拉三洲百多位学者宣读,会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简报,全文后纳入《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中。这是我解放后又一篇比较有质量的论文,文中提及“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岛之间,有着一个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居于北纬20°一40°的中国南部与西南部与印度支那的广袤地区,是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的科、属的。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地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出生地。这乃是我多年来研究的创见。
会后(9月)又赴庐山开第一次植物引种驯化学术会议,实系中国植物园在解放后相继恢复和创建后,在科学院中的第一次展示。与俞德浚、陈封怀等同游含鄱口并照相。
1964年10月,又奉院外事局派,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肖培根及华南植物园年轻同志等四人组队赴柬埔寨考察,时还值西哈努克亲王和我国开始友好合作。我们从金边,东南至白马,南至象山,北至吴哥窟,西经大湖至柬泰边境西梳风,几遍历全国,只是未上“长山”的胡志明小道。所见原始林区甚少,但也见到稀树草原中的龙脑香林,和吉里隆的热带松林。柬埔寨若和越南相比,显然热带性更强,更带有印度色彩。此行原拟了解胖大海和白豆蔻的原产地并引种,则未能如愿。
1965年1月,在北京参加国家大地图集的自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我与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同住一房,始识黄,但此后未能有更多交往。在此次,我承担了云南南部和海南的植被与植物资源的地图编制,至“文化大革命”后始得交卷。
“十年动乱”期间(1966—1976年,时五十岁至六十岁)
参加体力劳动如搬砖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饭。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当权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毫无例外地被批斗和进“牛棚”,参加体力劳动如搬砖砌防空洞是家常便饭。无止境地交待“造反派”要求的各种材料。这一期间,大约是1970年,全国兴起大搞中草药运动,我的历史问题也基本弄清楚,但还未“解放”,被分配去烧开水炉,劳动之余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始与杨永康相识。利用同志们为我搜来的各地中草药手册,包括云南省内所有专区,省外如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对各地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或许对各地在认识和采集中草药植物过程中还有些用处,虽然时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但利用机会发挥一技之长,做了一点有用的事。至1972年,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这也使我对植物分类的工作不致间断。后来本人的历史调查和审查初步结束,恢复到所革委会业务组工作。期间,我共写了各种交待材料有四大袋,在“十年动乱”结束时,都如数退回了。当年,还与张敖罗等赴蒙自草坝的“五七”干校学习锻炼,也在嵩明一带“拉练”,但总在所内,没有下到边区,大概因为我是经常出入边区的吧!
1974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贯彻“调整、整顿”方针,各方面有所起色。年初,参加了中科院在广州召开的“三志”会议(即《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抱子植物志》)。从此,《中国植物志》唇形科的编研又陆续恢复。会后即回昆明,与云南大学的朱彦丞教授一同接待来访的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人这是当时少有的外事活动。是年,又随院部秦力生秘书长、石山等领导赴菲律宾访问,到马尼拉和吕宋岛考察,参观了世界水稻研究所、碧瑶市的养蚕研究所等,初见当时菲律宾有关部门用遥感了解资源和环境的设施,我国还没有,直到科学大会后才有地理方面的试用工作。
次年,中科院组织青藏高原考察,5月启程进藏,随行的有陈书坤、西北高原生物所的杜庆等,走的是青藏线,达藏西至南的日喀则、聂拉木和吉隆,最西到萨噶,主要考察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和青藏高原高原面的植物区系,包括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和高寒荒漠等,首次进藏历时3个月。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我曾两次组织科学家随解放大军进藏,在我年近花甲之时,终又能实现进藏考察的夙愿,大概由于“十年动乱”中锻炼了身心的综合反应吧,出藏后尚有余力,乃与李文华、武素功同游黄山诸峰,并下西海。
1976年6月,又二次进藏,随行者 为臧穆、杨崇仁和管开云,由昆明出发,走滇藏线进藏,横穿三江大峡谷,主要考察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和东南坡植被,即西藏山南地区,并从雅安转红军长征路回所。此次亲睹横断山脉地区植被的垂直分布带,考察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和澜(沧江)、怒(江)分水岭植物垂直带的分异,以及与西藏高原面上的,还有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河谷柏树林和大片的原始云杉林等,对高原植物区系的多样性有印象深刻的差异和联系,对三江河谷的干热、干暖及干冷河谷的植被的递变更有直观的感受,对横断山地区和西藏高原植物区系有比较详尽的了解和认识,收获颇丰。此行在易贡的原始林中,从广播听到毛主席逝世。回所后的第三天,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欣喜若狂,以此结束了“十年动乱”,其中花甲之年是在林芝度过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历时十年,至1986年获国家特等奖。
从科学的春天到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时代(1976—2006年,从六十岁至九十岁)
最后十年中,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为主的专著。
从1976年科学春天到来后,至今已有三十个年头了。在头二十年里,身体尚可,但遭两次打击,一在骨骼,一在胆胰,且各种行政事务和外事考察繁多,还不能坐下来折节读书和深入思考。连续三届(五、六、七)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曾任过中共云南省省委委员(1979年起一届),又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1—1991年),兼任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1980—1984年)和云南省科委副主任(1975—1980年),当选过云南省科协主席(1987—1992年)。从解放初期参与大量的生物学改组和建所的工作,到后来幸逢盛世的诸多工作,我办事都不忘“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警句,总算在惊涛骇浪中免于犯大错误。尽管有各种事务缠身,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宝贵年华里抓紧进行科研是至关要紧的事情。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有关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头等大事,包括全国植物志和一些关键地区的植物志在内,《中国植物志》从1959年起,由钱崇澍、陈焕镛、林镕、俞德浚诸老和我任过主编,但他们都工作不久就逝去,独我经历最长,目睹其成,亦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何其幸也。虽云好事多磨,终得国家连续而得力的支持,至2004年其第一卷问世,含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巨著终究大功告成。在十年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西藏植物志》五卷已于1987年全部问世。《云南植物志》在云南省科技厅的持续支持下,得省内外植物学工作者的通力协作,全书也即将完成。随之各省区的植物志也都陆续出版,“过区系关”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我担任主编的《中国植被》在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则于1980年即已出版,成为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在我们国家步入科技创新时代之时,要利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在与我有不解之缘的植物学研究中有所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我有机会对国内外植物区系进行考察。对国内植物的考察,我再进东北、内蒙古,上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对我国北方的温带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植被作了进一步考察,加深了对我国北方植物区系的感性认识。接着是二次入疆,一次是从西宁越祁连山,6月中进山还遇漫天大雪,穿河西走廊入新疆,实睹戈壁荒漠及其中天山、阿尔泰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还到新源的野果子沟看原生的苹果属Malus的自然林;二次是直访天山阿尔泰,直观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稍后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等地,乃至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直至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到台南直至最南端海岸(1998),从而结束了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
此间再入粤海总结热带人工群落的工作,这样使我对我国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特别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代性和过渡性有了更为直接的感性认识。加上20世纪70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的考察,
使我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国外的考察,从“小球推动大球”美国代表团访华开始,1979—1996年间,我有机会到除了非洲大陆的各大洲诸国都作了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我访问美国,东起纽约,西达夏威夷,到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密苏里植物园都非一次。四访英伦,两进法国、德国、瑞典,查阅了欧洲各大著名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包括重访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并对欧亚大陆上的水青冈属Fagus和栎属Quercus落叶阔叶林群区获得较深的印象。五到日本,遍历诸岛,与诸多日本朋友相识,并得到植物化学和药学方面对我所的协助。在日本植物学家的陪同下,还在京都、熊本分别进行了野外考察,使我对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分异和联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对北美洲的考察,北起加拿大,从西至东曾到美国的佛罗里达作了考察,使我阅历大增,对中国—北美的区系分异与联系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深有感悟。在南美洲,从北到南经委内瑞拉、巴西,达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对三国在南半球的植被分布和区系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同时还亲睹了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丰富和壮观,只是无机会直达南美大陆的最南端,稍有遗憾,但已在阿根廷登上安底斯山尾端。在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交流中,特别是召开的第十三次(澳大利亚悉尼)、十四次(德国柏林)、十五次(日本横滨)世界植物学大会,扩充了我的学识眼界,得益匪浅,也让各国科学家对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了解。特别是大洋洲之行,北达布列斯班Brisbane,使我既见到了大洋洲本土区系的特殊性,也见到了亚澳之间的联系,尽管分居南北半球。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先后被选为美国植物学会外籍终身会员,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SCN)理事,以及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与各国植物学家的交往有新的发展。
最后十年中,我才折节读书,并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为主的专著。从对国内外的实际考察而有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又上升到理性探索与思考,在各方面积累的基础上,使我对中国的植物区系的分布特点、起源、演化以及在世界植物区系大背景下的地位和意义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在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中,我主要通过多年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知识的积累,深入认识到时至今日,首先应掌握这样一个真理: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又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命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其中绿色植物一直占居第一生产者的地位发展至今。它们的演化并非单系、单期、单域方式发生和沿着上升而逐渐扩大的螺旋曲线演化,而是从一开始就多系、多期、多域地发生,并有节律地历经多次渐变和突变矛盾的解决,在地球的历次大事件、大变动中通过多次大爆发,愈喷发而愈大愈复杂的爆发式前进。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各类生物自身运动(遗传与环境是主要矛盾),由持续的矛盾的解决而不断爆发式上升,因而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被子植物种类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在世界植物区系的大背景上,具体分析了我国350多科,3100多属,3万多种种子植物(有花植物),发展了系统演化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发展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逐科属(有些到种)分析,从而确认被子植物起源于两亿年以前(侏罗纪),太平洋作为泛古大洋从当时泛古大陆中在北半球东北部的一个海沟,经过海底扩张而蜕变为现今的太平洋,其后才有古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出现,最后才是大西洋的完全形成和现今地中海的形成。这一理论有其地质、地史根据,而且是和绿色高等植物,以及与其协同进化的昆虫、鸟兽的生物地理分布规律相符的。澳大利亚、印度板块和非洲大陆各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中徘徊,分别形成的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之间的最近两次分合,而形成与被子植物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次泛古大陆。海陆的不同组合和以后在旧世界兴起的基本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和新世界的基本南北向的落基山、安第斯山造山运动,都分别影响了白垩—老第三纪以来第二次大爆发后高等植物各类群的分布及分布区的形成。我在世界植物科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背景上所掌握的中国植物种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构成了我对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近代西方有关学者所拟的图景有了许多基本不同,更加明确了上述演化方式和种属、区系的发生发展方式,初步创立了有关这些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在植物地理学方面自觉运用唯物辩证分析的结果,使我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和间断分布,新特有和古特有,洲际间断分布和洲际、洲内的对应科属种,区系发生、分布、发展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使我能够探索到科属种和区系地理学能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有可能进一步了解种的具体演化过程,或者能对宏观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微观的基因形成及基因表达相结合方面有所启发和贡献,并使人类可能进一步控制绿色高等植物,使其在适应自然、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中能进一步解放其第一生产力,而使人类生产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人类生存环境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在世界植物园协会(1993)上以及大阪五人(中、英、美、日首席学者)座谈会上一再提出的“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其间我反复强调并提出: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既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从而提出: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历史发展过程问题,以及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在热带至温带以多层多种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认识到这些统一对立观点,是我在保护生物学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工作中的根本思路和发展过程,也是我获得国际大奖“COSMOS”奖的主要依据。到现在,我还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即自然保护事业与当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密切结合,否则很难达到“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这一当代严重任务才引发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和建议(1999)。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到设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实施,或许是解决“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的必要措施。
几十年来,我有机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研究生。近年来我与诸弟子协作,完成了《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2003)、《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2003)、《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和《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6)等新论著,这可代表我们集体的自主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探索吧!这只有在后人具体实践和认识中评议,才可以否定或充分肯定吧!我愿作引玉之抛砖。
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吴征镒
2006年5月9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