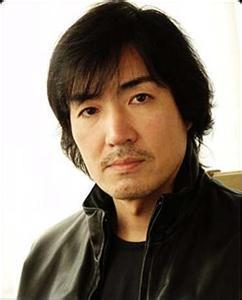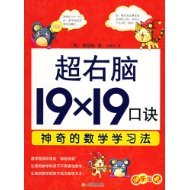溥心畲(1896-1963),名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恭亲王之孙。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于青岛威廉帝国研修院修西洋文学史。曾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抗日战争期间,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先后到日本、韩国、泰国、香港等地开画展,并为当地大学讲学。
溥心畲画风是属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走的是既无师承又无画友的自学成材之路。他《自述》:“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董、巨、刘松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毛,花竹之类。然不及书法之专,以书法作画,画自易工。”溥氏以古为本,亦以自然为师。他在《论书画》中说:“古者无旧本传摹,依物写形,形乃得其神理,后人转摹前迹,形留而神去。”移居台湾后,历游名川古迹,尤其对台湾特有的动植物很感兴趣,常以大自然的景色入画,增添了文人画自身的雅趣。
纸本水墨,109.5cm×57.5cm。中国美术馆藏。
溥心畲得传统正脉,受马远、夏圭的影响较深。他在传统山水画法度严谨的基础上灵活变通,创造出新,开创自家凤范。溥心畲的清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他悟到荣华富贵之后的平淡才是人生至境,因而他在画中营造的空灵超逸的境界令人叹服。《雪中访友图》茂密的松林生于冈峦之上,路径隐于林壑之中,曲折流淌的溪水将观者的目光引向画面的深处.深山幽僻处两位逸士和一抱琴童子踏雪前住山中访友。全画用笔精细周到.敷色淡雅.突出表现了山中雪后的宁静与秀美,表达了画家对淡泊生活的向往。
张大千 溥心畬 江寺静远镜心材质、形制:设色纸本尺寸:44×36.4cm。
溥儒(1896~1963)松阴高士图·行书七言联水墨纸本镜片·纸本对联对联识文:玉局一编时在手,桓谭万卷镇随身。款识:溥儒。画款识:松阴高士。心畬。钤印:旧王孙(朱)溥儒之印(白)一壶之中(朱)溥儒(朱)
溥心畬 学步图 镜心
溥心畬 戏 镜心
溥心畬 红衣垂露 团扇面
题识:红衣垂露。心畬。
钤印:溥儒之印
说明:团扇与折扇是书画扇最重要的两种形制。折扇由朝鲜传入中国,团扇则起源于中国的“便面”,原为人出门时在不便的场合掩面而用,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有描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由歌中可见,那时的团扇,已在实用功能之外,为使用者增添几分情绪与风姿。即使在折扇流行之后,团扇仍受仕女锺爱—团扇持于手,确有别样一番绰约。
从此扇用纸及形制看,应产于日本。据考,唐朝时空海大师将团扇从中国引入日本,基本形制是以细竹为圆形骨架,再贴上和纸制成。历代相传衍变,团扇的制作方法也发生变化。
此扇与编号217拍品张大千绘于日本的团扇分属衍变后的两种形制。张氏一扇仍以竹为骨,不过掺入折扇扇骨制法,以小骨攒集于扇柄,往外散发成椭圆状,和纸包住竹骨;此扇则纯以和纸制成,在纸上压出凹凸效果,仿效扇骨,如果在底部配以扇柄,即可执扇于手。
1955年夏天,溥心畬韩国讲学结束,又赴日本,年终方由李墨云等人接回台湾,期间与大千有数月同处,两人共同出游、品尝佳肴、吟诗作画……溥氏渡过数年来最为适意的一段时间,拍品日式团扇面或即作于此时,溥氏以清逸之笔,写荷塘景致,一盛放一含苞的红荷两朵,苇叶数茎,一只蜻蜓正款款飞来,画风清新可喜,与张大千画荷团扇有神韵相通之处。
溥心畬(1896-1963),名儒,號羲皇上人,又號西山逸士。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農曆七月二十四日生於北京恭王府。他是清朝第六位皇帝道光(旻寧)的第六子恭親王奕訢之孫,恭親王第二子群王載瀅的次子。屬於皇族畫家。他在「渡海三大家」中年齡最大。一般所謂的皇族畫家,大都有一種富貴氣息,畫風偏於華麗細膩、柔媚清雅;在他的許多作品上都蓋有邊框帶龍紋或無龍紋的「舊王孫」印章。這方印章,表明了溥心畬先生那天潢貴冑的身世。但這樣的身世若是在本朝覆滅成為遺族,而寄情於書畫所表現出來的畫風,則是如明末八大山人和石濤一般大塊寫意、奔放淋漓。
而溥心畬在民國建立後,體認到做為一代被廢黜的封建王朝的「舊王孫」來說,究竟是如枯葉落入激流中,這是無法改變的一去不復返的歷史現實。但做為個人而言,畢竟能自己掌握命撸梢罉渲L,變為依己自立,故而勤勉於詩文書中,馳騁在藝術天地裡,因此他並無八大、石濤那樣滿腹的悲憤,畫風還是屬於貴冑世族的氣息,不過由於他的文學底子加上形同隱居的生活選擇,讓他又能一洗鉛華,縝麗不媚俗,流露出文人的氣息,無論在表現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種文人心靈、魚樵耕讀與神趣世界的嚮往,還有遠承宋人體察萬物生意,與自然親和的宇宙觀及文化觀,皆可謂完全謹守傳統中國文人精神本位﹝農業社會的文化結構﹞,然而他的書畫作品卻並未落於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內涵的真實與精采。
溥心畬生在西洋文化大量湧入中國時,其自幼即受到傳統嚴謹的禮教薰陶,他的個性又內向好學,因而打下了深厚的學養基礎,也使他背負了傳承文化道統及國家情感的重大壓力與使命感。十九歲赴德國留學,研習生物與天文等西學,前後在德國達八年,但西學,似乎對他以後治藝為學的生涯而言,並沒有重大的影響與延續。他未因此受西風的影響而放棄舊學,依然保持著純粹的華夏傳統,以他正統文人的背景和世家子弟特有的貴冑氣息,宗法宋元,並在繼承傳統的同時,自成一格。
溥心畬繪畫的儒雅氣質,是自他讀書中來。他自許生平大業為治理經學,讀書由理學入手及至爾雅、說文、訓詁、旁涉諸子百家以至詩文古辭,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視書畫為文人餘事。因此使他的畫風露出一種高雅潔靜的人文特質,為人之所不及。「畫重氣韻。氣韻者,畫外之事也。」溥氏一生堅持讀經重文,以為書畫的根本,所以無怪乎他教學生畫畫,用更多的時間教學生讀《十三經》,常常把學生讀跑了。 溥心畬的畫風並無師承,全由擬悟古人法書名畫以及書香詩文蘊育而成,其畫作常援詩入畫。![[转载]溥心畲绘画作品欣赏 朱耷绘画作品欣赏](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81732t0179204f0b0835b215.jpg)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