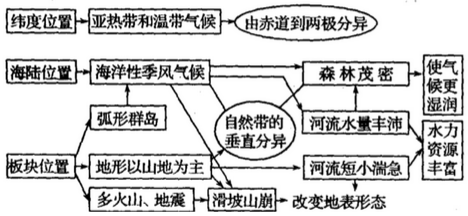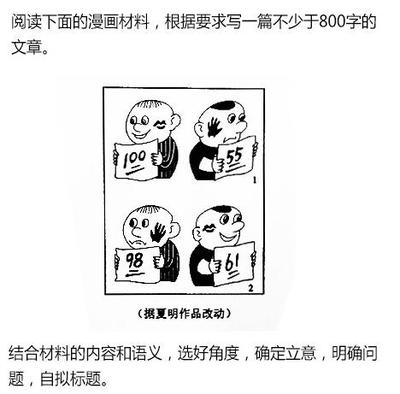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613417
有女舜华
【殊途卷】
第一章 龙游浅水遭虾戏
1、修禊
三月三,草长莺飞,天朗气清,正是游目驰怀的一脉好春光。垂荫细柳下,妖童媛女,三两成群,嬉游河曲。
在那绿荫清流之畔,却有那一处临水施挂幔帐,薄沙轻透,看似与世隔绝,却又叫人远远望见幔帐内隐隐绰绰的几许姿影。
一只羽觞顺水流缓缓而下,广袖轻撩,素净的手将之从水中捞起,珠玉淋漓,也不知道洒下的是水亦是酒。那手的主人却不管不顾,浑然未觉般将羽觞置于唇边,仰头灌下。
身侧有娇娇轻嗤:“噫,曹郎牛饮乎?”
那郎君却只是不理,自顾饮毕,长吁:“好酒。”
透过树荫的一束阳光,恰好洒在他的面上,肤光粲然,炫目夺魂。那女郎看得一愣,倏地粉面发烫,羞涩地别转头去。
曲水另一侧立即有人大声笑道:“曹明玕,真真祸害不浅。”

青帐内临水铺设毡席,错落零散地坐了七名男子,年纪都在弱冠之间,粲服广袖,相貌清俊,这些都是高门士子,除却身份尊贵外,举手投足间的风韵气度也非常人可以比拟。而他们身边围绕的那些女郎,更是百媚千娇,出身虽不高,却也是嗣出士族。
先前看曹明玕看失神的少女羞臊之余,却转而扬起头颅,一双秀目亮晶晶地盯着曹明玕道:“郎君可悦九娘?”
曹明玕不觉一愣,身侧调笑声顿起,鼓噪道:“九娘子自荐枕席,明玕莫辜负沈家女郎一番情意。”
近年北方士族纷纷南迁渡江,然而此时江南仍以旧时孙吴政权时名门士族为主,吴郡、吴兴、吴会三地合称三吴,以陆、顾、朱、张四姓为四大家。吴兴沈氏虽不在四大家之列,却也不容小觑。
但是眼前这位沈九娘的出身并不高,她家在建康只是吴兴沈氏的一支庶出,兼之她又是家中庶女,两相一比,曹明玕既是曹魏宗室之后,其姑父又高居琅邪王重臣,沈九娘若能被其纳为侍妾,吴兴的沈氏本家都得对她们这一支另眼相待。
此次能够出门陪同修禊踏青,原是沈九娘再三恳求了父亲,写了无数名帖才得以成行。如今建康曹家郎君早已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年纪虽轻,却已富有才名,相貌俊美,这等的才貌双全,人品家世,引得建康的女郎们纷纷爱之慕之。
“素闻京都有河东珠玉,不知比曹郎如何?”
随着幔帐轻纱被纤纤玉手掀起一角,帐后露出一清水芙蓉般的绝丽容颜。帐内诸人见其容光,不由都是眼前一亮,那少女年方及笄,发梳飞仙髻,纤腰广袖,罗衣双带,配上那一口吴侬软语,竟是说不出的勾人心弦。
沈九娘面色大变,少女眼波朝她冷冷一瞥,嘴角噙着笑,隔空朝她屈膝行礼:“雨芹阿姊。”声音仍是糯糯的,带着点女儿家的娇语薄嗔。
沈九娘原本跽伏于曹明玕身前,而今被那少女这般作势点名,不由羞臊得满面通红,仓惶起身,颔首回礼。尚未启口招呼,那头便已有人起哄高声询问:“来的是谁家娇娇?”
那少女扬眉嫣然一笑,当真明媚无双:“我乃沈九娘,沈氏瑞雪。”
众人皆愕然。
怎的又来一位沈氏九娘?
倒是卧躺在榻席上的曹明玕第一个洞察了沈瑞雪的心思,嘴角微微翘起,不觉笑了。这一笑,又如春风拂面,灿若朝霞般令人错不开目。
“原是吴兴沈氏九娘子到了。”
沈雨芹面色苍白,满脸委屈,怒不敢言。
沈瑞雪是吴兴沈氏家主最小的嫡女,在吴兴沈氏本家诸女中排行第九。而沈雨芹不过是建康这一支旁系的第九女,而且还是个庶出的,显然本家沈氏族谱上根本就没有她这一号人物存在。
沈瑞雪年纪虽小,容姿却盛,她施施然进了幔帐,身后方又跟进三名华衣女郎,均是十五六岁的年纪,看着装打扮并不像是随侍婢女,但沈瑞雪也不引荐,只是带着三女进了幔帐,走近水滨。
水波粼粼,沈瑞雪迎风而立,裙带随风起舞,端的是一副仙人神姿。果然,场中有人忍不住持手中如意叩击盂盆,应和声中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洛神赋》。
沈瑞雪不骄不躁,双靥微红,明眸善睐,目光在场中徐徐转了一圈,最后又落回曹明玕身上。
曹明玕仍是卧坐于席,纹丝不动,衣襟微松,满身落拓,桀骜不驯。
沈瑞雪嘴唇微动,想说些什么却又忍住,别开眼去瞅那唱赋之人。曹明玕哂然一笑,右手懒洋洋地抬起,随手一指:“你……”
沈瑞雪欣然回头,却发现曹明玕手指之人并不是她,而是她身后三女中的一女。
再看那女郎圆脸杏眼,生得不算貌美,却也有几分可爱,此刻似乎犹自不信曹明玕是在跟她说话,瞪着一双玲珑大眼,满脸激动,双手更是紧张地捏着绮带微微发颤。
沈瑞雪柳眉细不可察地一蹙:“这是吴兴钱氏阿静。”
吴兴钱氏?
众人面露困惑,吴兴士族大姓也不过有个沈氏,这个钱氏,听都没听说过。
这厢那钱静羞羞答答,头颅压的更低了,手足无措地走近两步,向曹明玕行了个礼:“曹郎有礼。”声音低微得也只有沈瑞雪和曹明玕二人方能听见。
那厢已有女郎从水边站起,朗声问道:“我等孤陋,不曾听闻过钱氏,还请沈九娘相告,这是江南哪一大家?”
沈瑞雪浅浅一笑:“不过是吴兴一商家之户。”
此言一吐,众人顿时熄了兴致,性情稍好些的不过神情淡漠,脾气不好的直接拉下脸来,责问道:“沈九娘,你怎可带此等商贾之流的人来污了我等耳目,扰了我等雅兴?”
晋人喜好雅致风骨,为人行事崇尚洒脱不羁,但同时却又将士族门第看得甚重。今日修禊同邀之人,不论出身高低,都是出自士族,即便像沈雨芹这样的出自寒门庶女,那也是世家子弟,哪是满身铜臭,不入品流的商贾之户可以比拟的?
钱静却仍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些风度翩翩的俊美郎君,见他们顷刻间翻脸薄情相待,不由得眼眶蓄泪,一副欲哭的楚楚样。她本生的娇俏可爱,这一委屈含泪的模样更是惹人可怜,可就连那素来惜花的曹明玕竟也漠然无视起她的存在,自顾自地饮起酒来。
钱静只觉得胸口发闷,接下来的半个多时辰犹如在火上煎熬,众人眼中她似乎成了个透明的影子,即便是身份尴尬的沈雨芹,也能从善如流地重新融入其中,唯独她……她贝齿紧咬着唇,直咬得唇破流血都宛然未觉,满脑子浑浑噩噩。
也不知过了多久,四下里宴也散,席已冷,幔帐轻薄,微风起舞。那憧憧人影仿佛已远去,连个残影都不曾留下。
“女郎。”
耳边一声轻唤,终将她恍惚的神志拉回。茫然四顾,凄凉满腔,眼泪就这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女郎!”钱静的样子吓坏了她的贴身婢女菡萏,“女郎因何哭泣?”
胸臆难舒,这种丢脸的事实在令她难以启齿,于是只是皱眉不答。菡萏奉上手巾,钱静胡乱抹了脸,稍稍整了妆容,扭头瞥见菡萏一副忧心忡忡的眼神瞅着她,便忍不住问道:“可还有不妥?”
“女郎眼睛红了,不如奴婢唤冯叟驾车过来?”
钱静也估到自己眼前这副样子见不得外人,想了想刚要应声,幔帐外有个声音唤道:“女郎可在?”听着声音陌生,钱静不明所以,菡萏倒听出是侍女红蕉。
红蕉才不过十一二岁,平时只管院落打扫等杂役,并不曾贴身服侍过自家女郎。这会儿怎会冒冒失失地过来?
“红蕉。”
帐外的小侍女听闻,掀起帐纱探头,一脸欣喜:“女郎果然在此!奴婢方才见好多车乘自这溪边离去,便猜女郎或许在此。”
菡萏斥道:“你来此作甚?”
红蕉见菡萏神态不佳,忙把怀中之物举高:“奴婢来送幕离。”
钱静面上一喜,刚要伸手取来戴上遮面,菡萏却奇道:“谁让你送这个来的?”
红蕉一脸讨好:“方才奴婢几个闲聊,郁离说虽然那些京都来的贵人并不在意男女之防,但如今既渡了江,到底行事还是得依着我们江南士族旧例来才算稳妥,那沈九娘若存了心思学京都的官样儿妆扮讨巧,这才真成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奴婢觉着有理,不想让沈九娘害了女郎,便起了心思,给女郎送幕离来。”
菡萏不觉失笑:“你倒会讨巧。不论如何,这幕离送的恰到好处,回头赏你。”
红蕉满脸欢喜。
却不防钱静一声冷笑:“她倒是好深的心思,这般的奴婢,我可实在使不起!”
红蕉吓得一哆嗦,扑通跪下伏地,全身瑟瑟。
菡萏见钱静满脸怒容,心里也是一阵惶恐,有心想劝却有不知道怎么措词方才合适。钱静将幕离扔到地上,一甩袖子,忿忿而走。
红蕉惧怕地哭了起来,菡萏只觉得背上发冷,将红蕉从地上拉起:“哭什么,女郎又没骂你。”
红蕉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菡萏救我。”心里实在怕极了,浑身瘫软使不出力来。
菡萏力气小,拉不动她,只得按捺下性子,蹲下身问她:“你跟我说实话,究竟是谁让你来的?”
红蕉哭道:“是……是水芋。水芋说郁离的话在理,如果我在女郎跟前得了脸,以后便能升作贴身侍婢……水芋是为了我好才……”
“这个水芋!真真是唯恐天下不乱,郁离怎又碍了她眼。你快起来!你再不起,我可不管你了。”
“菡……阿姊!阿姊!我错了,求阿姊救我,我怕女郎打我……”
“唉,你个傻子,女郎不会拿你怎样。”
“刚才女郎好生气……”
“她没生你气。”
红蕉抽抽噎噎,一脸懵懂:“女郎不是生我气,那她是在生谁的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