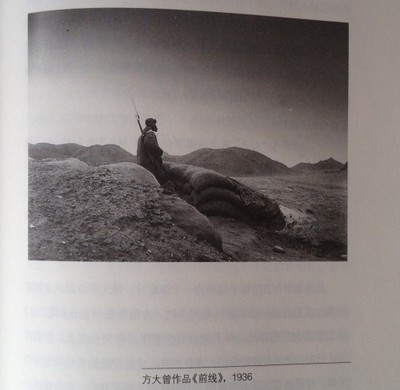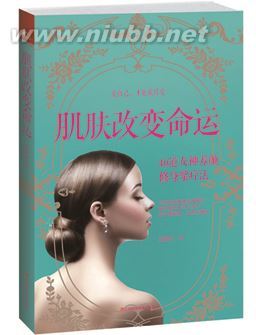这是一篇关于认识和改变强迫症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吸引人之处是作者成为心理医师之前也是一个备受折磨的强迫症患者,他以剖析自身的经历揭开了强迫症的奥秘;另外他用真实我、现实我、理想我来解释个人的心理,具有很大范围的效用,可以解释很多心理病症;而且他以自身克服强迫症和改变性格为案例可以增加不少可信度;最后,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像写作学术论文一样介绍心理学知识,行文也特有文采,而且旁征博引,跟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的理论进行比较,又增添不少学术上的说服力。总之,不管是什么人,得病的还是健康的,看看,你可以了解更多的关于自己内心的秘密,你会活得更加快乐。
在浩瀚的天空下,在时间的长河里,千万次追问生命和灵魂:我是谁?
我时而下沉,跟弗洛伊德一起勘察潜意识的暗流,时而上浮,憧憬马斯洛自我实现的天堂。更多的时候,我被华生斯金纳强化负强化的绳索牵引着,身不由己。
人的心灵可以历经磨难而更璀璨,也可能轻而易举被一根稻草压垮。形形色色的心理障碍,集中反映了人性的敏感和脆弱,给患者带来难以名状的痛苦和煎熬。
我们每个人都是实现了百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后,才来到世上的,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为生命的神奇和独特性而自豪。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然而,人的命运又是如此不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可测度的命运玄机喟然长叹。
我有超群的智商,这一点可以通过我从700多名高一学生中脱颖而出,跳级考上重点大学得到验证。但我的性格却有严重的缺陷,埋伏着后来导致强迫症几乎使我精神崩溃的隐患。二十年来,为了战胜强迫症和改造性格,我殚精竭虑,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而这些能量本来应该释放到事业上,创造辉煌业绩的。
现在,我以一名患者和心理医生的双重身份来讲述我的经历,把自己独特的感受、思考和发现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滤去杂乱的无意义的残渣,从中透析出有益于人格完善的新鲜血液。
我的经历匪夷所思,我的内心世界波澜壮阔。
此书对那些同我一样渴望解脱心灵羁绊、渴望自我超越的人,可能有所启发。
跳级考上重点大学
16岁那年,我以骄人的高考成绩从高一直接升入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制造了一点轰动效应。当我孤身一人登上南下的列车向武汉进发时,我茫然无知。高考成绩并不反映我的心理成熟度,除了数理化,我孤陋寡闻的程度令人惊讶。入学后,我写好平生第一封书信,竟不知如何发出去。悄悄跟在同学后面,学样把信投入邮箱,很快就退了回来。问同学,引他大笑,原来我没有贴邮票。我诧异,反复琢磨一个问题:寄信为什么还要贴"油票"?这也反映出当时的"票证情结"。食油奇缺,每人每月半斤,滴油如金,只好托关系走门子割点肥肉炼炼。
大武汉的繁华叫我开眼,在长江大桥上望江水浩浩东流,升腾起一种高尚的情感:我一定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第一学期考试,我各门功课全优,尤其高等数学得了全队唯一的满分。教数学的焦教员连连赞叹,说我了不起。我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次考试都第一,好像从没有下来前三名,而且从来没感到学习之累。再次强调我的智商,学习能力之强决非夸张。但从大二开始滑坡,学习成绩的下降速度,与我的苦恼度成正比。转折点业已模糊,但有件事对我的刺激极为强烈。
那时,兴老套的击鼓传花的把戏。鼓声一落,"花"在谁手里,谁就得出个节目,唱歌、跳舞、朗诵、说笑话,都行。有个沈阳的同学谈吐幽默,风度翩翩,博得满堂彩。大家都比较投入,玩得开心。突然,咚的一声,像砸在我的头上,脑袋一下子变大了。我吃力地站起来,脸胀得通红,浑身滋滋地冒汗。我紧张得手足无措,嗫嚅半天说不出话来,傻傻的笑。同学们一开始还起哄,看见我这熊样,就饶了我。可我尴尬得恨无地缝。从此,为莘莘学子展现青春光彩的"花",就躲开我走了。
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我在学习上建立起来的自尊和自信,那个击鼓的同学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那该死的一槌,惊醒了我的"自我",使我险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我开始反思和评价自我。我开始明白,原来除了学习,还有许多更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原来性格也可以散射夺人的魅力。而所有这一切我都低能得像个傻瓜。我思考着、苦恼着,找不到答案,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
三种自我
精神分析下震地狱,人本主义上撼天堂,行为主义在人间横行,心理学上的这三大思潮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行为作出了解释。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了人的行为?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人深层潜意识中的力比多(性驱力),而行为主义则坚持由人所处的环境支配,人本主义从人类的基本需要出发,指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释放潜能、自我完善的倾向。
我个人认为,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理论较适合用来解释性格的形成,而人本主义理论可用来指导性格的健康发展和完善,提高人格的层次。人格涵盖性格,性格是人格的核心成分之一。结合自己的体会,我发现人格遵循如下发展模式:
无我——自我——接纳自我——开放自我——表达自我——超越自我(自我实现)
无我是自我意识觉醒前的混沌状态,自我是觉醒后的"我"。自我由三种成分构成,分别称为真实自我、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现实自我是思考着、行为着的实体,真实自我是隐藏在实体后的动力定型,理想自我是自我设计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模式。人生是一出戏,现实我是演员,真实我是以内在规律制约剧情发展的原型,理想我是指导现实我演好这场戏的导演。一个优秀的演员,既要服从 导演的指挥,又要投入角色中感受原型内在的冲动。真实我说"我要如何",理想我说"应该如何"。
真实我处于潜意识层,清醒着的自我平时不能觉察,就像电磁波,我们看不见,但它存在。
当主体人格处于"无我"状态时,现实我尚未觉醒,理想我尚未形成,真实我最活跃。幼儿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不戴任何伪装和面具,自然流露各种欲望,对游戏的投入和专注以及从中获得的巨大欢乐,都令成人纳罕和嫉妒。我女儿一岁多时在童车上站着排便,兴奋得咯咯直叫来回奔跑。幼儿期是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我因此认为性格的本质特征在真实自我里。按精神分析理论,性格的形成是"自我"在"超我"的监督下,"本我"欲望有条件满足的结果。行为主义则认为性格是成人世界(环境)对儿童行为不断进行强化的产物,所谓积行成习,积习成性。教科书上说,性格是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体系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
人的一切心理问题都出在自我形成后。三种自我各自履行职责,潜意识中的真实我在暗中制约现实我,而理想我则对现实我施加强大的意识力量。现实我若能有效地协调真实我和理想我,就能顺利度过危险期,使人格得以健康发展和提升。
对性格的反思
那次击鼓传花惊醒了我的自我后,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性格。
父母遗传给我的气质无疑是抑郁质的,这没办法。但他们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性格,通过暗示和模仿的机制,已内化为我的性格成分。在一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他的影响不可估量。我父亲做事极为循规蹈矩,待人接物的礼貌有点过火。他骑单车,一进胡同口就下来推着回家,见人打招呼以免失礼。我不记得有第二个男人这样做。家里来客人吃饭,他从不让我上桌,而且必须在里屋待着,等客人走后才能出来。他从不开玩笑,家庭气氛沉闷。他说话拐弯抹角吞吞吐吐,显得底气不足。我父亲年轻时一直很健康,常自夸不知医院大门朝哪,但后来查出有点高血压,医生劝他不吃肥肉,从此母亲做的菜中就见不得一丁点。说到他怕事的程度,仅举一例:我家与邻居发生纠纷,姐姐和母亲在外面与他们争吵,而父亲躲在屋里没出来,他后来解释说刚下夜班睡得死,没听见。我和姐姐都不信。这件事深深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次我被一个坏孩子用石子打破了头,哭着回家,可父母既不去找打人者算账,甚至不敢通知其以蛮横霸道闻名的家长。他们的忍气吞声彻底消灭了我残存的一点攻击意识和攻击能力。父亲给我的印象永远萎萎缩缩、缩缩畏畏,我没见过他一次挺直腰板的自信,好想在我心理脆弱想退缩的时候,父亲振臂一呼,豪气冲天地带领我"冲锋"。父亲动手能力奇差或者根本不愿意动手,家中修修补补万事求人,我大学毕业时,他传给我一身人情债。我父亲早已仙逝,在此评论他没有丝毫不敬,只是为了研究我性格形成的根源。无论如何,父亲用他微薄的工资养活了一家六口人,而且对我的学习抓得紧,对我寄予厚望。
在我的性格特征中,首先给我造成强烈刺激的,就是极度的腼腆怕羞。其实从小就这样,但一直没对我产生大的负面影响,直到击鼓传花。类似的事件早在上高一时就发生过一回。语文老师让我站起来背诵高尔基的《海燕》,我刚开了个头:"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就思维阻断,出现了暂时性遗忘。这是由于高度紧张在大脑皮层形成优势兴奋中心,按负诱导规律造成周围大面积区域的广泛抑制的现象。当时我面红耳赤、大汗淋漓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以致我的同桌见了我就"出汗出汗、红脸红脸"地喊了很久。我的性意识萌发较晚,直到15岁才刚刚抬头,喜欢看漂亮的女同学,知道在她们面前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过这种朦胧的意识还不足以使我把腼腆怕羞视为男性的致命弱点。见人脸红的毛病伴随我十几年,越克制越严重,苦不堪言。后来接触森田疗法,才知道这是精神交互作用的结果:抗拒某种感觉(症状)而失败,就产生焦虑,焦虑使患者越发关注那种感觉,感觉阈限的降低加强了感觉,患者就更焦虑,更焦虑使感觉更加强,如此恶性循环。
大学是才子云集的地方,尤其从大城市来的同学,不光学习好,而且见多识广,吹拉弹唱,各方面都特别优秀。而我在众人面前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相形之下无比惭愧自卑。我极力掩饰自己的羞涩,模仿别人想表现得自然大方,结果弄得更不可收拾。理想自我对现实自我说"千万别紧张",真实自我接着说"就要紧张,因为紧张是我的性格,一直这样"。理想自我的指示我听见了并且努力按他的指示去做,但真实自我虽藏而不露却暗中较劲,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拽,最后理想自我败下阵来。假如现实我能觉察真实我的存在和愿望,接纳他而不是压制他,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真实自我形成于幼年期,是个孩子,一味压制会导致他的逆反心理,纵使理想自我说得天花乱坠他也不理会。只有先接纳他并耐心地劝说和诱导,最好潜移默化地对他施加影响,他才能不断汲取理想自我的成分并内化为自身的特征。简单粗暴急于求成将使真实我和理想我彻底决裂,使现实我陷入莫名其妙的两难困境。
救人还是不救人?
意识的大坝一旦决口,潜意识的洪流就汹涌而至,我性格中的缺憾因子纷纷浮出水面,轮番攻击脆弱敏感的自我。我的神经就像灵敏度极高的天平,落下一粒尘埃就使它失去平衡。我必须倾尽全力制作平衡的砝码,结果天平越过平衡点更加摇摆不定。我开始失眠,辗转反侧中,希奇古怪的念头出现了: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姓孟?我的祖先两千年前是何人,是否也像我一样见人脸红?......不行,赶紧刹车,明天还要上课呢。越强迫自己睡觉越睡不着,纷飞的意念像电影镜头掠过大脑的屏幕,有些镜头慢下来最终定格为一个问题,譬如碰上有人落水我救还是不救?路遇歹徒行凶我管还是不管?如果袖手旁观,必遭舆论谴责,那就假装没看见躲开,可良心上又过不去。还是应该救人。可是我虽然会游泳,但一口气憋不长,可能不但救不上来还被落水者抓住不得解脱,于是我开始为自己设计解脱的方法:抓他的头发、拧他的胳膊、托他的下巴......把他托出水面后,以何种游姿把他带到岸上也颇值得斟酌,蛙游、侧游还是仰游?一团乱麻。最后又觉得救不上来连自己一块淹死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我的想象中落水者不是他而是她,而且是个漂亮多情的少女。我若把她救上来她必对我感激不尽,并因此爱上我,想到这里我美孜孜地忘了自己姓啥。这件事美是够美,可我转念一想,万一我淹死了怎么办?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分析权衡,仍不得其解。关于路遇歹徒行凶的联想差不许多,当然被害人最好也是美丽的她。她大声呼救,我冲上去三拳两脚把歹徒打跑,或者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我负了伤她温柔地给我包扎伤口。话说回来,我有这个本事吗?瞧我这瘦不拉叽的书生样,不被凶残的歹徒打死才怪!我就这样想啊想,直到天亮。
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手淫,而且越来越频繁。我那时的性知识可以说一片空白,简直就是性盲。记忆中,从未听父母谈起过有关性的话题,他们筑起"性"的铜墙铁壁,等我用青春的躯体去撞得鲜血淋漓。wa?@
小时候家中几乎没有藏书,桌子上只摆着几本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也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村里倒有一个大喇叭,整天呜哩哇啦唱样板戏,揭批四类分子。村里有一个姓孙的反革命,社员在地头上开他的批斗会,因为有人揭发他在家里翻出"变天账",扬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基干民兵怒愤填膺冲过去喂他一顿革命铁拳,就见他奄奄一息说吃不消了。所以那个时代藏书是很危险的。有一天大人都不在家,我因闲得无聊,就到处乱翻,发现床底下有个破纸箱子,箱子里有几本发黄的书。其中一本大概是关于道德和法制教育的,说有一名革命干部因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与一女青年发生了不正当的肉体关系,从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还有几个强奸犯被判死刑的案例,犯罪过程描述比较笼统,都是到那种关系上点到为止。我尚不十分明白那种关系究竟怎么回事,却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我后来又偷着把那本书拿出来看了好几回,而且浮想联翩。我意识到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是不正当的、见不得人的,但搞不懂为什么使我兴奋,想压也压不住,只是后来才被紧张的学习转移了或掩盖了。这就是我上大学前获得的唯一的性知识,如果这也可以称为性知识的话。哦,还有一次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草,有个大孩子讲,他问一个在妇产医院上班的人看见了什么,那人回答:"操,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这句话使我产生丰富的想象,长达数年。
晚上胡思乱想睡不好,白天上课时就哈欠连天昏昏欲睡,使劲拧大腿,强打精神,只觉头晕脑胀,眼前金星飞转视线模糊,教员讲的啥黑板上写的啥,一概不知。我以为都是手淫惹的祸。每次手淫都伴随悔恨自责,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那时书籍和报刊光讲手淫的危害,教导青少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用坚强的意志克服这种恶习。我为此深感忧虑和恐惧,觉得身体要垮了。以后才知道手淫其实与正常的性行为并无本质差别,只要不过度,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尤其对成长期的青少年,手淫是释放积聚起来的性能量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当时使我深受其害的,不是手淫本身,而是对它的错误认识。我本就内向孤僻,现在更把自己封闭起来,独来独往,默默地一个人咀嚼苦果。
我敏感多疑,自暴自弃,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快乐洒脱,就更寂寞难耐。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兴趣,只关心自己,在日记上倾诉苦闷。我越是急于摆脱就越是事与愿违,有两件屁大的事更增加了我对自己性格的不满。第一件事:某天晚上全区队看电视,坐在我后面的同学把脚放在我的凳子腿上不停地抖动,我感觉凳子鼓鼓涌涌的挺别扭,就回头看他以示不满。黑暗中不知他注意到没有,但他的脚好像收回去了。可没多会儿,那只臭脚又来了,而且抖得更厉害。我心里很矛盾,想制止又怕得罪他,最终也没有鼓起回头再看他一眼的勇气。我整个晚上都在考虑该不该回头警告那个抖腿的同学,电视上演的啥根本不清楚。这个抖腿的镜头日后在我脑海反复出现,因为我在如何对待这种事上一直拿不定主意,尽管我切实感到自己怯懦窝囊,尽管有时觉得这算什么事儿,但仍然控制不住地想想想——再碰上抖腿的怎么办?第二件事:有一天早晨起床后,临床的同学说我打呼噜,我说我从来不打呼噜,你一定听错了,是别人打的。可他说就是我,而且打得他睡不着觉。我对这件事想了一整天,耿耿于怀:我怎么会打呼噜呢,不可能呀!当天晚上就不敢早睡,屏心静听,旁边两个老兄终于鼾声如雷,声震屋宇。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呼不呼,但别人在呼已确定无疑。第二天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没成想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他早就知道,接着生动地向我描述某某的鼾声高亢激昂,某某的低沉悲怆,而他俩的打呼水平比起隔壁的高鸣来就不行了,人家五音齐全字正腔圆不让帕瓦罗蒂,那才叫艺术家。还有李振业这小子,那天因爬墙外出被队长罚站两小时,是标准的立姿,害得他晚上打呼噜只有5和7两个音节。我的天,当我被他一句话搅得寝食难安时,他压根就没拿我那小儿科的呼噜当回事,更让我纳罕的是,别人的呼呼噜噜也能给他带来偌大的快乐。这不能不对我有所启发。
由此可知,我敏感多疑的程度已接近极限,比方说,我跟谁打招呼,人家没反应,或者很久没收到某人的回信,我就得反复检讨自己,回忆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哪里不小心得罪了人家。伴随神经衰弱的加重,强迫症状产生了,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名词,也搞不懂那些难以克制的念头和动作究竟咋回事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