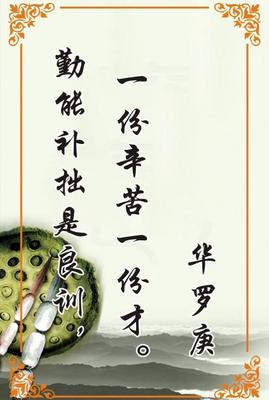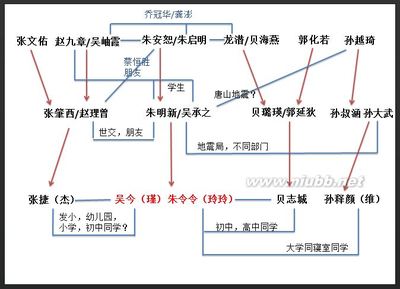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理一分殊是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颐可以说是该理论的奠基人,而朱熹的阐述与 发挥,则可以看作理一分殊理论的成熟,程朱二人的理一分殊理论是 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 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主张性即理,历来被认为是程朱之间主要相同点。程子与朱子都讲性即理,但程子将性即理主要是阐发孟子性善义。在程子思想中,性理“非从宇宙界落下”。而在朱子学说中,天地间公共之理落入人之形气中才形成所谓性,“宇宙界人生界一贯直下”。

程 颐与朱熹都认为,个人在宇亩中处于一定关系之中,对他人他物负有一定义务,由于关系地位不同,个人对他人直接承担的义务也有所差别。从而仁爱的原则在实施上呈现出亲疏有等的差别。但程朱认为,虽然施行上亲疏有氓但其间体现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即道憾基本原理表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具体规范中又贯穿着普遍原理。而朱熹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关系是伦理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关系。
“理一分殊”就程颐本意而言,“理”指道德原则;“一”与“殊”相对,“一”指同一、统一,“殊”指差异、差别;“分”在这里指本分或等分。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分”在这里指禀分。所谓理一分殊,即是“一”与“万”的关系。“体统是一太极,然一物又各具一太极”,因此,“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 个”。物物各有理, 总只是一个理。中庸章句》中“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可做两节看:当讲“理一而分殊”时,是“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系就宇宙普遍法则之超越、绝对的宰制力的下贯言,所谓“天人相贯”;当讲“分殊而理一”时,是“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系就上达言,人伦日用之事理、物理、伦理,皆要通过我们内心之中的性理洞明以穷尽宇宙哪一个终极本体的太极,所谓“天人相通”。
程颐的“理一分殊”,根据大部分学者的考究,是源自于佛家 的。朱熹对程颐的思想固然有继承,但他对理一分殊的理论自 觉却未必完全是来源于佛教 朱熹明白地指出, 未必完全是来源于佛教。 朱子的“理一分殊”,很大部分是受 到道家的影响,结合到家和佛家的思想提出来的。
“理一分殊”就程颐提出达一论题的时候说,它是一个意义比较具体的命题,主要表现一种伦理学的意义。朱烹也继承了这一点。但朱子的贡献正在于直到他才把这一命题的意义加以扩大,包含了若干更普遍的哲学意义。
程颐讲的理一分殊本来是可以用体用论来解释的,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但二者间没有本末的意义。照朱烹的讲法,理一分殊又是本(本原)末(派生)的关系。本体与本原意义略有区别,前者是本体论的说法,后者则有宇宙论的涵义。每个事物既然是具体的,它们的存在形式、运动法则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朱熹认为,它们各自的“理”不同,这是“分殊”;但这不同的理, 又都是根源于一个理,所以是理一分殊。 “月印万川”比喻可以形象具体地表达理一分殊的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还特别强调它在性理意义上的理的运用。在性理的意义上,理一分殊的意义是超宇宙本体的太极与万物之性的关系。
朱熹对理一分殊还解释说: “万一各正、 大小有定,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盖统体是一太极,然一物又 是一太极。”朱熹这样解释是从质上着眼,吸收道家、 道教形而上之体来提升儒家哲学的思辩水平,加以改造后与儒家形而下的用相结合, 是朱熹论 “理一分殊” 的特点。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 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理一分殊” 原是程颐在给弟子杨时注解 《西铭》 时提出的。程颐把理一分殊理解为万理归于一理, 他强调一物之理 即是万物之理, 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那种一切即一、一即一 切的神话。
总的来说,程子的“理一分殊”有三个特点:1.平面化,2.人伦界,3伦理意义。朱子的“理一分殊”亦有三个特点:1,立体化,2,宇宙界和人伦界的相通,3,众理意义。
性二元论:
朱烹哲学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为本性。
“性”只是全部“理”之中以特殊方式存在的一部分,天地之理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人物之性则如被盛入器皿中的海水,他们的内容完全一致。如果说两者有差别的话,那就是理与性在存在形式上有随气流行与被气拘定的分别。
朱烹认为,从人和物的角度看,人物之性部是从天凛受得夹的。若从天的角度看,则可说是天命与或赋与万物。
按照朱烹哲学,天地之理只能叫理,京于人物之身的理才能叫性。因此,虽然相对于特定的形气体质而言,未有此气此质时天地之理未尝不在,但性一定是与气质结合无间的。
朱烹认为,天地问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票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使人之本性与天地之理有了一种直接的宇宙论的联系。朱层认为,从人和物的角度来看,人物之性都是从天禀受而来;从天的角度看,则可说是天赋与或命与万物以性,他认为达也就是《中店》 “天命之谓性”的意义。因此在朱窥哲学中,天理被禀受到个体人物身上所成的性常称作“天命之性”。
气质之性反映出的,既有理的作用,也有气的作用,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交错综合,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抵气质之性则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每个人的天命之性是相同的,而因人的气质不同,所以人与人的气质之性是不同的。
朱子天人观
程颐、程颢把“天”理解为宇宙的普遍法则——天理。“天者,理也”二程认为,人与万物以“理”相通,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朱熹有时把天理解为自然的存在,“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但他更多地还是把“天”界定为“理”,“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天人相通在乎“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为性,······”由于“理一分殊”才有人与万物的差别,“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各有理。”朱熹的理有时实在“气”之内,有时又在“气”之外的抽象的精神实体。朱熹还把“天“理解为义理之天,因而,把“天人合一”理解为“天人合德”。朱熹又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天理的有效方法,要求闻一知十、格一知十,当“格”到一定程度就能“豁然贯通”,求得“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天人合一”境界。
《中庸》首句开宗明义曰: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统帅全篇的总纲。其中的“天命之谓性”, 可以说蕴含了儒家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观念。对于“天命之谓性”的内涵,朱熹的解释是: “ 命,尤令也。性, 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 气以成形, 而理亦赋焉。” 认为“天”赋予人以“性”, 人从天那里获得了自身的本质性规定( “ 质”或“理”)
一、理也者气也者 形而上下
朱子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子认为,形而上学者谓之道,形而下学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个形迹。所以道器两者不分离。在这里,所谓形而上,就是抽象、超越的意思,而形而下,就是实在的器用的层面。理,是万物形成之前的一个总规律,是化生万物的根本;气,是形成万物的具体材料,是化生万物的工具。所以人与物的降生,必然禀受了这一“理”,然后才有各自的属性;必然禀受了这一“气”,然后才有各自的形状。这就简洁地阐释了作为朱子理学大厦中基石部分的理、气、性、形等概念,并巧妙地将天地之理、气与人、物之性、形结合起来,从而完善了他的继承和发展了上古“天人合一”思想。
朱子认为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相结合乃是产生万物(包括人在内)的本原。换言之,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理”与“气”结合而成的。“理”是精神、主体;“气”是物质、客体。
二.朱子认为,人只是天下万物中的一种。从本原上来说,天与人绝不能分离的。当人类步入社会之后,人更具有其它动物所没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这是人之本质属性所在,也是人之优越性所在。如果脱离了人的双重性,就无法去论“人”了,也就无法去正确处理人与天的关系。把朱子人性两重性视为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亚层次。告诫人们:“只有‘克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 告诫人们:“只有‘克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三、天即人人即天 理一分殊
朱子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朱子论天人都渗透着宇宙本原之“理”,所以天就是人,人也就是天。天人一体两分。自然的天不比人大,人也不比天小。此乃“理一分殊”理论在天人关系上的推衍。朱子发挥中国禅宗中“一即一切”的观点,提出了“理一分殊”说。
五、人是最灵之物 不问命运
朱子主张“只看义理如何,都不问那命。”(《朱子语类》卷34)朱子论天人,尤其论理气,喜讲一体两分,既对立又统一,其中蕴涵着辩证法的因素。所以,人对天命有何足畏?事业前途只讲“义理”,不讲“命运”。
七、天地万物之本 致中致和
“天地之位本于致中,万物之育本于致和。各有脉络,潜相灌溉,而不可乱耳。”在这里,朱子又从另一角度进行天人说的论述,他指出天地的得位根本在于无所偏倚,万物的化育根本在于恰到好处。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暗中又互相交融,而其次序又是不可打乱的。朱子以《中庸》为根基,强调“天人”之根本在于“致中”“致和”。换言之,也就是天人“合一”。所谓“合一”,就是两者“中和”。
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 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 将一种思想体系转化为一种法律、习
俗、实践系统, 它具有强制性。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 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 将一种思想体系转化为一种法律、习俗、实践系统, 它具有强制性。
朱子使“帝王的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朱子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缘由在此。南宋晚年,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这与朱子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分不开。朱子建立了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客观唯心主义推到一个新阶段。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道教思想。天理论引入社会政治思想,使这些领域也呈现不同的面貌。朱子的理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正因为朱子的思想在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做了更加详尽、更加符合统治者要求的讲述,有利于统治者对人们的思想进行规范,因此,朱子的理学让统治者更加确立了儒学在统治中的重要性,因此推动了儒家的制度化进程。
封建社会后期儒家的传统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礼教,起了重要作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