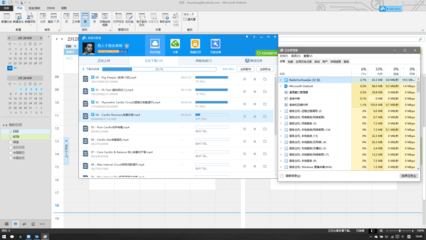如果要从湖南的地域文化中分辨出一重性别色彩,相信所有人都会深深地感觉,那实在是一种极富阳刚之美的文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送给彭德怀的诗篇。寥寥六言四句,道尽了湖南人的本色。
近代以来,只有湖南有这样的人物。也只有湖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在谈论湖南文化时往往也会提到另一句话:湘女多情。
最容易让人产生这一联想的当然是湖南有一个地方叫桃花江。上世纪30年代黎锦晖创作的一曲软软的《桃花江》,简直让它成了美人盛产之地的代名词:
我听得人家说——
〔白〕说什么?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呀,比不上美人多!
〔白〕不错呀!
果然不错。
我每天都到那桃花林里头坐,
来来往往我都看见过——
……
黎锦晖先生出自著名的湘潭黎氏,他以湖南的地名写出来的作品,在一般人看来,总该是有点凭据的吧?
偏偏这首歌流传那么广。在激奋人心的抗战歌声响起之前,它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
由于它长期被摒弃的缘故,笔者少年时一直没机会看到《桃花江》的歌词。然而正是这样,它也就一直令人感到好奇。
记得大学里听那些成熟的学长们谈论美女,无论何时何地,桃花江三个字总是能勾起他们某种特定的眼神。
当然不光有桃江。民国时期湖南有一句流传甚广的风土谣谚:
湘潭木屐益阳伞,沅江女子过得拣。
“沅江”一作“益阳”。
当然还不光是益阳一带。民国军政要人李宗仁先生直到晚年,还在回忆录中津津乐道他年青时观察到的湖南南部的女性风俗。那是1916年,他第一次随部队越过南岭从广东北上,一过湘粤交界的坪石,便觉得风土人情大异:
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都是天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
此情此景,当然令人感慨殊深。以至于其审美观霎那间便发生了转变,回去时,反觉其“朝于斯、夕于斯”的本乡文化难以适应:
归粤途中,进入湘粤交界的乐昌县时,陡见妇女完全天足,在山上和田野中工作,有的挑着担子,在路上横冲直撞,类皆面目黎黑,汗流浃背;以视湘省妇女的白暂细嫩,举止斯文,真有霄壤之别。骤看之下,颇不顺眼。
而尤其让李老先生终身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小插曲。进入湖南不久,在安仁、攸县的交界地带他作战负伤,于是被抬着送往后方:
当晚宿在一伙铺里。铺主人有一年方二八的掌上珠,她听说我的勇敢,转败为胜,乃自动替我包扎、烧水、泡茶,百般抚慰,殷勤备至。当我翌日离去之时,她似乎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令我感激难忘。湘女多情,英雄气短,这也是受伤后一段颇值得回味的故事。
很可惜,这一故事到此也就嘎然而止,没能衍生出更多的罗曼史。不过倒确实应验了“湘女多情”的口实。
可是,如果我们纵观历古,恐怕是很难得出“湘女多情”的印象的。
不仅很难说“湘女多情”,自古以来,湘江流域的女性简直就很少在历史上露面。
号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古典美人西施、王昭君、赵飞燕、杨贵妃,无一出自湖南。其中出自南方的两位,西施是越人,老家在今诸暨、萧山一带;王昭君家乡离湖南稍近,在三峡秭归,湖北人。
秦汉时期,美女是河北平原的特产。《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描写中山、赵一带的风俗是:
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一个地方的风气竟至于如此被写进国史里,古往今来,好象也只有当时当地。
南北朝时期,号称“佳丽”之地的颇不少。梁简文帝有句云:“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陆琼则称“临淄佳丽地”。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形容江南,如谢朓所云“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而入唐以后,“佳丽”几几乎已成为江南的专利。王勃有“吴姬越女何丰茸”之叹,杜牧有“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之咏,就连号称“诗史”、一般人心目中未免几分道学气的杜甫亦有“越女天下白”之评。
宋代以后,这一趋势愈发明显。传说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引得金主起投鞭渡江之志。无须说破,令他无限向往的还有荷花深处那无数的“嬉嬉钓叟莲娃”。
明清以降,扬州的瘦马、苏扬的名妓天下闻名。而北方,则是“大同的婆娘”在明代号称天下三绝之一。
可以说,直到民国年间一些女革命家、女作家、女艺人出现之前,湖南的女子就很少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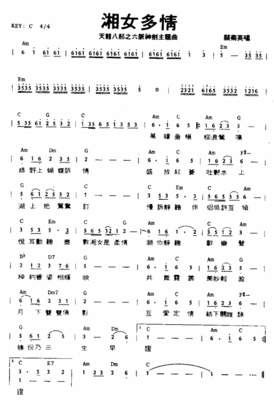
那么湖南的女性都在做些什么呢?
她们在辛勤默默地劳作,相夫教子。甚至,她们比男性承担得更多、付出得更多。
也许人们都记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载楚越之地“呰窳偷生”,又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两句话表面上都是对当地男性的评价,“呰窳偷生”指的是一幅材力短弱、病殃殃的样子,而“丈夫早夭”则分明指该地域的女性并无异常。既然如此,那些活计主要是谁做呢?
类似的记载一直不多见,直到北宋,《岳阳风土记》中才有一些具体的资料: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赘,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这当然是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残余。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不过讲良心话,虽说看起来是“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实际上当时该地的女性也绝不容易,并无机会坐享清福:
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诋诮。衣服之上以帛为带,交结胸前后,富者至用锦绣,其实便操作也,而自以为礼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擒纵时所结,人畏其威不敢辄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鼎澧亦然。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等本事,也不可能引得堂堂七尺男儿去上门作赘,且“无复悔怨”。
资料中只讲到巴陵、华容以及沅水下游、澧水流域,笔者相信,当时整个三湘四水间应该都差不多。因为从民族分布、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与南方土著民族相关的一些较古老的习俗都是从北逐渐向南推移的。当时四水下游地区如此,其中上游不会例外。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曾动情地讲述他家乡的妇女生活习俗:
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笔者深信,这一习俗在历史上曾长期、普遍地存在于沅湘之间。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于儒家文化的涵濡同化,湖南的女性被逐渐引入裹脚、主内的轨道,或可称之为向闺秀化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大规模的江西移民入居之后的事。
但即便如此,由于地域经济水平的限制,湖南的女性仍需要承担大量的劳动。光绪《耒阳县志》描写其风俗云:
女服事乎内,主中馈,勤纱绩,工缝纫,操作不缀,无论贫富大都类然。
而同治《临湘县志》甚至讲当地的妇女:
且有插秧荷草、刈蒿萎、披荆棘者。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子,应该是不会太多情的。即使要多情也不会有足够的闲暇和心境。如果说,粗糙的生活还不足以磨灭她们多情的天性,那么,更应该成为她们标记的是她们身上的另一种性格成分。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道:
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的确,与其说多情,还不如说倔强更能显现湖南女性的性格特色。
无独有偶,著名女作家白薇的评传中,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存在:
碧珠的母亲,性豪爽,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又象湖南农村一般妇女一样,十分勤劳,亲自种菜,挖土,耕山地,料理果园,养猪,碾米……内外总管,集于一身。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到“倔强”二字,但其中“倔强”的底色仍很显眼。谓予不信,请看小碧珠长大后的表现:当她历尽艰辛从虐待她的婆家逃出来,跑到衡阳、长沙去念师范,毕业前她父亲为了让她回家,花钱请学校的教工将她严密看守,并且将她的行李搬走,她硬是从厕所的出污口逃出,凭着同学凑集的五块多钱,只身逃到上海,后来出洋。
常言道,找媳妇看岳母。谁说白薇的这番表现,不是得自她母亲的遗传呢?
当然,除了母亲的遗传,还有隔代的。《白薇评传》中还说:
祖母赵翠兰的思想启蒙和父亲黄达人的言传身教,给黄彰这个从小经历了各种艰苦锻炼的少女,培养起一种勇敢向上、貌视传统的叛逆精神。
所谓“勇敢向上、貌视传统”,无疑是“倔强”的最到位的解读。
岂止一个白薇。丁玲,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女作家,又何尝不如是?
作为一个大作家,丁玲得到的评论已堪称无数。在笔者读到的评论当中,当以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最为深刻:
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
实在是耐人寻味,王蒙竟然在“多情”之前也用了“倔强”一词。这之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思考:
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历史呢?是命运塑造小说还是小说塑造命运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楚呢?谁能说,丁玲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没有她本人的性格元素呢?谁能说,她本身的性格不是来自于湖湘间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呢?
丁玲在作品中表白道:
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人……
恐怕没有人能不承认,这何尝不是丁玲的夫子自道!
又何止作家。王人美,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年以后与著名国画家叶浅予重组家庭,按说两个艺术家生活在一起,又都是社会名流,这样的组合总该是温情脉脉、和和美美吧?然而不尽然。叶浅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婚姻生活时,给王人美的内容题为“磕磕碰碰第五课”,其中对王人美的性格的感受是:
她的性格急燥,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
实在是妙得很,这一位的性格又是一个“强”字。
那么,让我们回到起点,“湘女多情”的口实又是怎样来的呢?
征诸文献,“湘女多情”的“湘女”起先并不是指湘江流域的女性,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传说中的娥皇、女英。
关于娥皇、女英,有一个起源甚早、流传甚广的美丽传说。
她们是尧帝的二女,舜帝的二妃。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疑;二妃前来寻夫,竟哭死在湘江边:
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述异记》)
她们死后成为湘水之神,号湘君、湘夫人。为了纪念她们,洞庭湖中的君山上建起了一座湘妃庙。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从唐代开始,很多人将“湘妃庙”称为“湘女庙”。既如此,“湘妃”也就被称作“湘女”。
李白《望夫石》诗云:
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
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将“湘君”、“湘夫人”、“湘妃”称为“湘女”的诗篇。
从那以后,以“湘女”形之于诗的不胜枚举。如元代的陈孚有句谓:“染竹痕深湘女泪”,而明人张昱有句云:“江上数声湘女瑟,烟中一曲竹枝歌。”
当然,如同所有文人墨客的咏古诗一样,那些描写湘女的诗意大多很陈腐。而真正让人感同身受的还是毛泽东那著名的两句: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不仅因为作者是湘人,更因为诗篇中包含着作者的真情、血泪。
饶有意思的是,以往讲“湘女”的,大多只突出她们的“恨”。不知是觉得对于她们这样的身份,称之“多情”不大合适,还是觉得既已如此,其多情自在不言中?
曾几何时,“湘女”的“湘”被人们从“湘妃”的“湘”,一变而为“湘江流域”的“湘”,再变而至于“湘省”的“湘”,于是乎有“恨”也就单单地成为“多情”了。
这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事。毕竟,澄碧的湘江的哺育出来的,无论男女,大多是性情中人。
愿从今以后的湘女不再有恨,永远多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