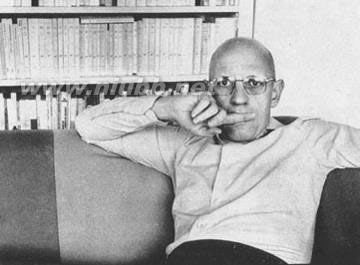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
作者:陈晓明
一、前言:文化研究的当代趋势
传统的“文化研究”一直默默无闻地隶属于人类学领域,然而现今时兴的“文化研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回答现今的“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是什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卡里·内尔逊和保拉·A·特莱契勒编辑的厚厚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的前言里,编者也表示了对给“文化研究”下定义的迟疑。在他们看来,试图给出文化研究以一种单一的定义和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甚至引述斯图亚特·霍尔的话说:“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1】。文化研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没有人可以控制它的发展。文化研究这个古旧的行当,几乎是突然之间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否认它成为大学的一门显学。它不再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或历史学指称的那个冷辟的学术领域,而是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历史、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似乎正在宣告传统的学科边界正在消失。特别是因为研究主体多半出自大学英语文学系或比较文学系,直接表明传统的文学批评学科正在经历巨大变故。文学批评这个行业在变得五花八门和丰富广博的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传统形象。它不再那么局限于纯粹的文学,对文学的读解方式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使人们在谈论所谓的纯文学时也不再那么天真单纯,其中隐含的动机和诡计,足以使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当代政治学相去未远。文学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向文化研究转向,人们当然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批评又一次焕发了生命力,然而,人们也应该有所疑虑文学批评这个行业存在的真实性。但不管如何,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涵盖了多门学科,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学术事业的联合体。在杰姆逊看来:“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2】“后学科”这种说法当然有些故弄玄虚,实际上,它也就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或超级学科。从事文学批评的大学研究人员多数转向文化研究这件事实正象杰姆逊所表述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愿望”,尽管这种“愿望”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图相关,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文学批评这门学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宁可将“文化研究”放置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历经的历史变动中去理解它的学术特征和它的当代意义。
现今时兴的文化研究大体上可以化分为二大块,其一是大众文化研究;其二是新历史主义。狭义的文化研究即是指大众文化研究,而广义的文化研究可以包括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色彩较浓,大都有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因此也可见在这一领域,女权主义显得十分活跃。因此大众文化研究与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有交叉重叠的关系。由于新历史主义偏向于文学文本分析,强调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审美意蕴,因而新历史主义经常被称为文化诗学。例如,新历史主义主将格林布雷(Greenbllat)就自称其研究为文化诗学。另一方面,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也有相近之处,1985年,Johathan Dolimore与Alan Sinfield 合编《政治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论新论》一书,该书就把美国新历史主义与英国的文化唯物论视为理论的同盟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后殖民理论研究异军突起,这个领域尽管偏向于英语文学批评,但其文化色彩较浓是无庸置疑的。其方法论显然是后结构主义的综合运用。从总体上来看,尽管这些专业的研究对象不再限于文学,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实质脱胎于文学批评。准确地说,它们的研究方法乃是新近文学理论与批评革新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构成当前文学理论与批评新近最主要的成果。
就文化研究的知识构型而言,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可以直接上溯到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方面包括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系谱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的文化仿真理论;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如拉康、德留兹、居塔里等等,这些学说共同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其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二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三是威廉斯代表的英国文化唯物论。从总体上来说,正是把后结构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调和在一起而使文化研究具有了“后-后结构主义”的特色。
就其方法论而言,可以看出后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走向全面综合,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理论观念与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不拘一格的发挥,在广泛概括和综合的基础上展开具体的理论实践。例如,现在很难说是谁谁秉承了拉康,谁谁是福科理论的翻板,也很难说女权主义只是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混合。当今女权主义显然又融合了福科与德里达。就新历史主义而言,显然与福科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与德里达也不无关系,甚至与文化唯物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表明现今的理论批评在综合的基础上正在构建一种包容性更大的超越单纯派别的新理论话语。就文化研究的理论素质而言,正是在广泛讨论后结构主义那些基本命题的理论推论中,文化研究得以全面而完整地展开学术实践,因此,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不仅仅构成文化研究的理论前题,也可以看成是文化研究的有机的一部分,或者说,前者也就是它的经典部分。
因此用后-后结构主义来描述理论的前移运动,就不是夸大其辞的说法。事实上,早在1987年,理查德·强森(RichardJohnson)发表《究竟何谓文化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所指称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可作为相互参照。他认为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可以都可看成是“后-后结构主义”【3】的运动。布兰林格 (Patrick Brantlinger)1992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发表关于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的演讲,题目就是《后-后结构主义或天真的想望?》。可见以后结构主义为参照来理解新近的理论批评发展趋势已是不少理论研究者致力于关注的重点。按照特里. 伊格尔顿的看法,所谓“后”的含意,并不代表原本的现象有所改变,只不过是情况加剧【4】。文化研究对后结构主义的超越,可以看成是把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观念推到极致,在知识综合性运用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由此创造了文化研究更具包容性的知识景观,对理论的发展前景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且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对当代后现代社会,或全球化时代的生活现实作出直接的阐释,这些都使文化研究具有非同凡响的吸引力。
二、必要的前提: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我的讨论中,“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因此我把新历史主义看成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源自斯蒂芬·格林布雷(StephenGreenblatt)。1982年,格林布雷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而流行开来。尽管格林布雷更乐于用另一个术语“文化诗学”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古典文化研究工作,但新历史主义这种说法似乎更能引起广泛的兴趣。把文化研究或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放在一起来讨论,并不是什么特别生硬的做法。事实上,经常被描述为对后结构主义反动的新历史主义,其实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的谪传弟子。后结构主义的信条“文本之外无他物”(德里达语),并不是说文本与社会历史是隔绝,相反,社会历史全部汇集在文本的内在组织结构中。只不过新历史主义进一步强调那些美学问题与其他社会话语、行为和机构有复杂关系;而这种多重决定和不确定的关系反映了个人主体和集体实践的意识结构。新历史主义者都试图成为离经叛道的人,只不过这一代学者不再有五、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社会革命倾向,无宁说他们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他们的反动不过是试图在经典文本中找出一系列非正统的解释链,由此来重建迥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场。很显然,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做法不过直接来自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正是过去近二十年来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根本动摇了那些规定着传统人文学科的意识观点、道德法则和本体论原则,以及对意义和价值的产生和发展程序的诘难,从本质或直接的表意模式到历史的、受语用限制并互相差边的表意模式的转换,对完整性和同一性的全面质疑等等,给予新历史主义提供了现成的思想和方法论武器。
八十年代以来,解构主义经过耶鲁四君子的推波助澜,在美国迅速得到广泛响应。显然,美国的解构主义者把解构理论与新批评的遗产--形式主义分析相混合,保罗·德曼、J·希尔斯·米勒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努力去发掘文本中的美学要素,解构主义策略主要是用于发掘文本形式的内在组织。J·希尔斯·米勒对新历史主义的做法就十分不满,早在新历史主义初露端倪时,米勒1986年在现代语言学会上的演讲就对新历史主义提出批评:“最近几年,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全面的转向,抛弃了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5】他指的显然是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新历史主义的主将路易·蒙特鲁斯辩解道:米勒是把话语领域和社会领域对立起来,而文化研究则是强调二者的内在联系,相互依存。他认为,一方面,社会被理解为由话语关系构成的;另一方面,语言运用被理解为对话性的,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蒙特鲁斯的辩解正是点出了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联系。他否认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或解构理论)的纲领(“文本之外无他物”)有出入。他援引杰姆逊的观点“历史只有在文本形式中才可被感触。”【6】事实上,新历史主义把解构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去发掘隐藏于其的多重决定等级的建构力量。任何像米勒所说的“以评议本身为对象”的主张都已经并将永远是处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之中的一个位置所产生的语言为对象的。象格林布雷所理解的那样,文学和艺术的特性是社会历史所确定,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产品的区别不是文本的内在特质;而是艺术家、听众和读者所创造并不断修改的。新历史主义的提问是:作品是谁写的?谁在阅读?各自以什么动机和目的进入写作和阅读?这个过程为托尼·贝内特的“阅读构成”理论描述为“试图确定一些决定因素,它们通过作用于文本和读者的关联,以此沟通文本与语域,联结这两者并提供两者建设性相互作用的途径;语域不表现为一套独立于话语之外的关系,而是一套互文性话语关系,既为文本产生读者,也为读者产生文本……文本、读者和语域……是一套话语构成的关系中的可变因素。不同的阅读构成……产生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语域。”【7】从这里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对美国解构主义的改造,不过是把对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改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在这里,社会历史成为一个文本,一个超级的、充满岐义的后结构主义实验性文本。格林布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文化诗学”下的定义是:“研究文化活动的集体创造,并探讨这些活动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关注的是“集体信仰和经验怎样形成,怎样从一种状况传向另一种,怎样集中于可把握的美学形式,怎样进入消费领域,以及通常被视为艺术形式的文化活动和其他相关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界限是怎样划分的”。【8】新历史主义最实质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过是德里达和福科的综合运用。
福科对整个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全面,以至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科的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福科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任何一部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上福科的痕迹。这不管是在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些观点,还是关于少数族群和女权主义最激进的立场,都可以看到福科的幽灵在四处徘徊。当然,福科影响最直接而最有效的可能是对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福科不仅动摇了传统经典历史学的基础,而且开拓了历史学的新领域。这个领域有着根本不同的主题和分析方法。新历史主义对那些边缘文化现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福科的影响,例如,游行、札记、仕女手册、医疗文件、宫廷习俗、教会信条、巫术及反巫术的有关材料等等,这些文化资源都是福科所热衷的课题。就方法论而言,福科从来不避讳,他书写历史就是为了消灭历史。福科提出“考古学”(archaeology)去代替历史(history)。他的知识考古学对传统历史学的那些经典主题,例如:边缘性、传统、影响、原因、类比、类型学等等进行全面质疑。这个人对反常的意识形式和社会存在方式有着奇怪的热情,并给予独特的揭示。福科赞扬创造的无序性(disording)、解构性和匿名性(unnaming)的精神。他对意识历史中的“裂隙”,“非连续性”和“断裂性”有着持续的兴趣,他乐于去发掘意识历史中的多种时代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而漠视类同(similarities)。福科的研究似乎有一种主题却没有一个可概括的情节。象他在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词与物》中所作的那样,他的研究主题就是人文科学中事物的秩序在词语中的再现。如果它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话,那它就是关于“再现”本身【9】。福科试图通过否定所有历史描述与解释的传统范畴,从而找到历史意识本身的“临界点”。
作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始作俑者,格林布雷明显得益于福科的理论。其他姑且不论,他的最具影响的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确立》一书,可以看成是福科的“权力”理论(例如《纪律与惩罚》)的杰出发挥。格林布雷把他的理论目标说成是一种努力来“获得对权力的一种特别形式的人的表现--那个“我”--的结果的具体理解,这种权力既体现在特定的机构中--法院、教会、殖民政府、父权家庭--也溶合在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表达法的典型方式、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中。”【10】。关于此,弗兰克·林特利查(Frank Lentrichia)以《福科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为题撰文指出:格林布雷对权力的描述支持福科的权力理论,不仅保留了福科对权力的具体的机构化特点,它的可触摸性的不断强调,也保留了他陷入权力是捉摸不定、实际上不可界定的观念之中的状况。正如福科惯常所作的那样,格林布雷描述的权力同样不是确定在一定的界限内--“而是从不知什么地方跑出来扩散到所有地方,并吸收一切社会关系以至使社会集团之间所有的争端与“冲突”都成为仅仅是政治纷争的表现,成为一场建立在一种单一力量基础之上的事先设计好的冲突剧,这种力量制造出‘对立’来作为其虚假的政治效果之一。格林布雷关于那个‘我’的讲述,同福科的一样,将把它失陷于专制性的叙事体作品同当今世界成为恶梦般的地方这两者之间的巧合戏剧化。”【11】。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者普遍接受福科的关于历史学的观念,他们坚持认为历史学家们不可能客观地描述过去,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它,从而在他们自己与环境之间造成距离,这些距离使得新历史主义者有理由对历史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完整性置之不顾。新历史主义者的兴趣在于引进福科的断裂与不连续性这些非正统的观念,格林布雷说道:“对客观性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统一性叙述这些遭禁忌的传统愿望被自我的关切的公开传播所代替;过去和现在之间所谓的不连续性(一个福科式原理)被描绘成一个连续的叙述,其起点和终点都是我自己。”【12】尽管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带有很强的幻想成份,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推翻了历史决定论的统治观念,还是重新肯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集权主义,依然值得讨论,但它确实为当代文学批评创造了一种繁荣景象。
三、政治上正确:新的意识形态趋势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看来,文化研究这个联合体目前正集纯学术与泛政治于一体,“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此外也指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13】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学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成‘学术’问题,就显得不明智”;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有理由对许多时兴的事物表示不满并给予激烈的批评,尽管杰姆逊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文化研究确实明显具有学术政治化倾向。只不过这种政治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式的宏伟政治,它是学院里的政治,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政治。简要地说,这种政治包含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实践与知识分子信奉的一系列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关于西方学院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实践非本文力所能及,在这里,我更倾向于讨论那些流行的政治观点,是如何贯穿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并且有力地构成了知识分子新的意识形态。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不解之缘。正如丹尼尔. 贝尔所说:“十九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通过对必然性的强调以及向它的信奉者灌输热情,已经完全可以和宗教相匹敌。由于这些意识形态把必然性和社会进步看作是同一的,因此它们也就和科学的积极价值联系在一起。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和那个企图维护其社会地位的知识阶层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和那个企图维护其社会地位的知识阶层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14】。尽管本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支配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霸权,专制政体,民族革命,文化认同等等,构成了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超级系统。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意识形态也从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平息。五十年代末,麦卡锡主义声名狼藉,“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时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15】,但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重新又使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和功能,如果说十九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信念还是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构造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则表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也是思想文化的产物,但更主要的是强有力地支配着思想文化的再生产。六十年代激进主义运动随着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的结束而弱化,知识分子普遍退回书斋,寻求纯粹知识的构造,以替代激烈的社会运动。例如,象巴特这样的一度追随萨特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语言学的文本分析实验,并且个人的美学趣味也转向了纪德式的优雅与纯净。确实,七十年代以来是意识形态衰退的年代,然而,不管是“宏伟叙事”的解体,还是冷战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是“历史的终结”【16】,都不过意味着旧有的意识形态体系陷入危机,而新的意识形态正趋于形成。
如果说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化研究”自觉酿造学术的意识形态,那显然是夸大其辞的说法;“文化研究”表征的政治性,之所以是一种学术的“政治”,在于这种“政治”乃是学术话语包含或折射的观点、立场和态度。文化研究正是在承袭和发挥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知识体系时,表达了学术话语的特殊政治意向。在这一意义上,后结构主义解构中心,反抗权威,强调边缘性,强调少数族群的利益,这既是后结构主义习惯寻找的研究主题,也是它力图表达的思想意向。文化研究承接了这些主题,并且推到更加彻底的地步。这些学术话语包含的政治态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不断扩展和增殖。“政治上正确”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美大学校园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共识,这些“政治上正确”的命题包括: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挑战,反种族歧视、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强调少数族群(例如同性恋者)的权益等等。这些观念已经不仅仅是维护一些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的权益,更重要的在于它已经变成大学的信条,在这些方面没有人敢于越雷池半步。在当今时代的西方大学墙院内,谁要是对有色人种有所非议,对妇女有所不恭,或者对环境漠不关心,以及对同性恋者不给予必要的同情理解,那么这个人会被视为在“政治上”犯下方向性的错误,至少会被看成是“政治上”的落伍者。这些原本基于新保守主义的宽容性的价值观,现在多少已经有了激进的态势[17]。
文化研究的政治倾向最突出反映在女权主义和反种族歧视问题上。女权主义的政治性这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经典女性主义理论始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Feminism),社会性别差异论构成其理论基石。这种理论认为,男女不平等的因素不是两性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结果。很显然,女权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女性的社会属性或阶级属性。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西蒙·波伏娃(Simmone deBeauvoir)。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中开始风靡学术界,随着解构主义的盛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普遍把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战斗性十足的文风。这可以在保加利亚藉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的一系列写作中看出。1970年,罗兰·巴特撰写一篇题为《陌生的外国女人》,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学界推举克里斯蒂娃。在巴特看来,克里斯蒂娃的陌生话语根本瓦解了我们习惯的思想信念,这种表达方式完全置身于我们存在的空间之外,并且以无法抗拒的力量从我们的话语边缘直接切入。虽然七十年代初还很难说克里斯蒂娃受到解构主义多深的影响,但致力于反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构想,使克里斯蒂娃的写作一开始就天然具有解构主义的倾向,同时也表明女权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天然联系。这种解构主义式的女权主义在八十年代风头十足,然而,传统的以及白人妇女推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晚近的文化研究中遇到强劲的挑战,当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阶级论,现在被更明确而尖锐的种族理论所取代。反种族歧视的双面刃:激烈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以及反抗白人中心主义。这二个方面足以把当代女权主义和种族理论混为一谈,大有把白人女权主义驱逐出境之势。1990年6 月,在美国俄亥阿克伦布(Akron, Ohio)召开的全美女性学联合会(NWSA)第13次年会,一批参加会议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集体退离会场,以表示对联合会总部种族歧视的抗议【18】。而这些人的真实意图则是抨击联合会是一个由白人女性把持的、只为白人女性说话的团体;她们声称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体女性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的组织。并且使女权主义的政治诉求变得空前激烈。很显然,女权主义与反种族歧视立场的结合,使女权主义的政治性得到空前的加强,如果说传统的女权主义者多半还是白人妇女的话,她们的矛头所向主要是男权统治,而现在的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其政治批判对象则是指向帝国主义。对于她们来说,本土的男权统治并不是最可恨的,相当多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令人惊异地为本土的男权压迫制度辩护。她们极为不满白人女权主义者认为的第三世界妇女受当地父权制的压迫比西方发达国家妇女受本国父权制的压迫程度更深的说法。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无知的偏见。她们反对用西方的男女平等观念用于解释第三世界的妇女地位,不少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指出在殖民主义时期之前,第三世界国家中早就存在男女平等或男女互相尊重的思潮。她们指出:“殖民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以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了第三世界国家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状况。”【19】
这些来自第三世界或者与第三世界有血缘联系的女权主义者,现在正在致力于夺取长期被白人女权主义者占据的话语权力位置。在当今种族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的时期,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以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姿态展开新的理论攻势,而白人女权主义不过是这一轮理论革命的必要牺牲品。这当然不是什么学术机构内部的争权夺利,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理论在向后殖民理论暗递秋波的同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使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俨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白人女权主义者自己。现在黑人女权主义者在对白人女权主义的驳斥中,更加鲜明地阐发了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立场。过去女权主义用来对付男权统治的“姐妹情”的观点现在受到质疑,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查拉·提·墨罕提(Chandra T.Mchanty)毫不留情地指出:“除了姐妹情之外,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20】对于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父权制不过是宗主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工具,更重要在于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
现在,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难以抹去历史阴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罪恶史使他们在“政治上正确”大打折扣。现在真理的天平显然向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方面倾斜,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白人女权主义者被视为充满偏见的有极大局限性的理论怪物,这些人充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和想当然的偏见,例如,她们对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中存在的妇女外阴和阴蒂切除术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埃及女作家娜瓦尔·依·萨达维(Nawal elSaadaw)指责说,她们热衷于去这些国家观看这种手术,却对跨国公司是如何剥削这些国家中的廉价劳动力漠不关心。更重要的是,白人女权主义的结论更加可疑,例如,弗兰·霍斯肯(FranKosken)这个号称研究非洲妇女切割术的权威,她认为父权制通过对性行为的控制来统治妇女,使她们依赖男人--这种说法受到怀疑。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指出,这些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这些研究中,历来以优等文化自居,凌驾于其他国家妇女之上,实际上采用的是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立场。现在这种怀疑已经上升为学术伦理的指责,美籍墨西哥女权主义学者阿尔玛·加西亚(AlmaCarcia)认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对少数种族妇女要么采取讨好的态度,要么以权威自居,却对她们很少提供帮助。
很显然,“政治上正确”使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变得理直气壮,而“种族偏见”的概念正在以另一种形式扩大化。“种族”日益成为文化交流中的障碍,令人惊异的是,现在,这种障碍横亘在白人女权主义者面前,这使她们在真理面前步履蹒跚,因为,白人女权主义的政治动机和理论的诚实性都受到怀疑,这使她们的理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现在,更为致命的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文化身份成为无法抹去的局限,不少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正是抓住这一要害从而对白人女权主义者研究第三世界妇女问题的“学术资格”表示怀疑。美籍华人学者周蕾(ReyChow)指出:“西方女权主义者应该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西方妇女运动是在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时期产生和发展的。这个社会的发达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要与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对话,应该首先认识和批评自身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第三世界妇女运动和理论。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强加在第三世界妇女身上。”【21】这很有点象中国长期盛行的“血统论”,出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白人女权主义者的首要工作是反省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历史(这与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论调如出一辙)。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一直抱怨白人女权主义者存在着“优越感”,似乎她们天生就不可能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理解第三世界的妇女问题。正如她们的皮肤无法变黑一样。很显然,白人女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受到怀疑,而这种怀疑根源于她的文化身份,特殊的文化决定了人们是否有可能,有资格去“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按照这种理论,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当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她们的角色和资格同样有可能受到怀疑。她们生长并受教育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离本土文化,何以能理解本土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妇女呢?例如,斯皮瓦克自以为是印度受压迫妇女的代言人,但印度本土的知识分子并不以为然。同样的质疑还可以推论下去,就是在本土文化范围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又如何能理解“受压迫”“受剥削”的妇女呢?斯皮瓦克曾经以“沉默的从属阶级能够发言吗?”为题撰文,但她的发言就能够代表从属阶级吗?
当种族问题被移植到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时,也就意味着白人女权主义者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在关于女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上,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的声音已经远远盖过白人女权主义,这些还显得温文尔雅的名媛淑女,现在只有在诸如“女同性恋”、爱滋、环保或青年亚文化群等问题上有些发言权,而在妇女与殖民主义历史这一最热门的论题上,节节败退,只有洗耳恭听那些代表第三世界“从属阶级”发言的女权主义者责问和训导。事实上,这种局面乃是当今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映。这些反西方父权制文化的女权主义者们,不过是把西方当今的父权制的主流话语推到另一个高度。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很大种度上承继了尼采激烈抨击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历史宏伟叙事,进一步对西方的文明持各种批判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自现代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其主流倾向就是批判西方文明自身,清理西方的知识传统构成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主导批判精神--这本身又不断构成西方的知识传统。显然,后结构主义在这方面走得更远,象福科和德里达,以及列奥塔和德留兹等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西方现有的知识传统进行彻底的清理。这项西方知识传统内部的批判,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又具有了东方/ 西方的双重视野。在西方的知识危机的裂痕中,可以扯出一部庞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史,原来面对自身历史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突然发现他们要面对第三世界,面对一群曾经饱受压迫和奴役的“他者”。所幸的是,最激进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目前还只限于批驳白人女权主义者,而更强大的后殖民理论显然还不能撼动西方知识传统的主流势力,这使作茧自缚的激进的西方理论家们还可以高枕无忧,目前只有白人女权主义者自食恶果。
四、后殖民理论: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
后殖民理论与帝国主义论述密切相联,最早的关于帝国主义论述的经典理论当推霍布森 (J. A. Hobson)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过最为精辟的分析,1916年,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疑是对帝国主义阐释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这些早期的经典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今时兴的后殖民理论的思想前提,后殖民理论家大多数人信奉过或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后殖民理论更主要的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后裔,通过运用和发挥后结构主义理论,或者说通过把后结构主义理论推广到殖民主义历史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开拓了一片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
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过是批判帝国主义理论的必然延续,只不过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更偏重于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殖民主义批判偏向于文化理论。早在五十年代,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写下《黑皮肤,白面具》,可以说是批判殖民主义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作。范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文化态度和表意策略,反省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在文化上构造殖民地,从而更好地把握和控制殖民地。关于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互动,特别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渗透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工作,这位出生在法属安第利斯群岛的马丁尼克岛的精神病医生,终其短暂的一生都是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奋斗,他甚至公开为武装暴力辩护。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实比广大黑人遭受白人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却哑口无言的心理创伤更令他震惊。范农揭示出殖民主义是一种藏在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花言巧语面具下、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渗透性压迫结构。很显然,范农的理论在于强调种族差异性,它坚决反对白人种族优越性这种观念,他把黑人试图学习白人,试图成为白种人的文化想象看成严重的精神妄想症。由于被盖上黑人的印记,同时徒劳地力求使自己成为白人,黑人就形成了一种过度敏感的心理失常,“过分受到外来的限制”,从而,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特性被异化。范农对殖民地文化与白种人文化的同化持悲观态度,同化的结果不过是使黑人更深地陷入想要“得到白人另眼相看”的妄想狂的精神分裂怪圈。这种精神分裂症尤为明显地发生在城市上流社会的土著知识分子身上,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同时是由于物质利益与殖民地经济持续密切关联所决定。例如,乡村农民较少受到这种妄想狂患者心理的影响。范农后来在他进一步的研究著作中指出,乡村农民的传统习俗以及对被白人移民所占有的土地毫不含糊的需要,为反抗种族主义提供了基础。在范农的反殖民主义理论表述背后,是他持续不断的革命要求,这种革命要求的矛头当然对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在多大程度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化相对立又值得推敲:“我突然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我自己,并且认识到,我唯有一种权利:那就是向他人要求合乎人道的行为……我唯有一种义务:那就是不由于我自己的选择而放弃我的自由。”范农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他关于种族革命,关于人权的各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他所接受的西方理论。关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观念,这些都与西方现代以来的“现代性”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分裂的文化,一方面,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总体的规划,把人类纳入到理性的范畴和科学的范畴;另一方面,整个“现代性”的设计和展开又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实践来推行,这种“现代性”规划进入第三世界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分裂。现代性的宗主国试图在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培育的那些观念,正好用于推翻西方列强进行的历史实践。在这一意义上,范农为代表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同样处在这种分裂之中,他们正是用“现代性”的观念,去颠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历史实践。
后殖民理论到七十年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1978年赛依德出版《东方主义》。自此以后,赛依德迅速成为美国知识界的超级明星,这位形式主义批评家同时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文化评论》、《社会文本》、《批评探索》、《Boundary 2》和《拉里顿河》这些激进的批评刊物上,他的立场完美体现了流亡文人和激进批评家的双重色彩,他甚至声称:“我的目标就是建立巴勒斯坦国,然后对它进行攻击”。不管赛依德多么巧妙地放出烟幕弹,力图保持他的理论平衡,但他的理论致力于反对西方(白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是不争的事实,而解构西方学术制度,瓦解那些既定的真理,这正是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的中心思想。
赛依德的“东方主义”主要通过对“东方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建制、思想方法和功能的研究,揭示出殖民时代以来,西方形成的一整套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和文化心理。“东方主义”自从发表以来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问题,但“东方主义”的确切涵义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辩。以至于赛依德自己要在1986年再写一篇《东方论再思》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误解,即便如此“东方主义”依然有不少疑点和难点。“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字典含义是指“东方的特征、风格和风俗”,按《牛津英文词典》的解释,“东方主义”一词首次在1769年被霍德斯沃特(Holdswort)评论荷马史诗时使用。Orientalism此后成为研究东方各国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学以及生活风习和文化特性的学科总称。显然,“Orientalism”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东方学”或“东方论”,就《东方主义》一书来说,“东方主义”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其一,作为研究东方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特殊学科总称的“东方主义”,其含义可以用“东方学”来表述;其二、指一种特殊的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例如,在殖民主义时期,不少的西方作家、哲学家、政治论家、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等,都不同程度接受了东方与西方的基本区别的观念,这些观念成为关于东方的风格、习俗、思想方法和历史命运的创作和研究的理论起点;其三、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统治和支配东方的特殊文体。如果从话语表达方式来检验东方主义,就可能发现,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文化有系统地从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和想象力上来掌握和生产东方主义。也就是说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知识霸权,以一种固定的文体表达方式促使所有关于东方的著作、思想和行动受到其限制。总而言之,西方所谈论和理解的“东方”不过是其想象的产物,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武力征服,西方同时在文化上对“东方”进行重塑。
不难看出,赛依德是在巧妙运用福科的知识权力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对东方学进行内在的疏理。就东方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创立与殖民主义历史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合谋的产物,这在赛依德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东方学也必然不可避免表现了对“东方”的曲解和奇异化--这些都是事实。但赛依德在揭露东方学的政治无意识的同时,显然也夸大了这一知识的创造与殖民主义实践的共生关系。在这里面隐含着这么一个问题,就任何知识的构造生成来说,都与当时的历史情势相关,这在哲学上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例如福科对资产阶级兴起时的关于“疯狂”、关于“性禁忌”等等话语的分析,都表明了一种知识的生成本来就与权力实践相关。赛依德不过把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加特殊的处理,并且将其置放在东方/ 西方的二元对立背景,置放到帝国主义/ 第三世界、殖民主义/ 殖民地的关系中来分析。在这样一个特殊化的处理中,赛依德有效突现了“东方主义”这门学科创建和发展的“目的论”背景。也就是说“东方主义”这门学科全然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东方(第三世界)创建的。尽管赛依德自己一再宣称他反对东方/ 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伊斯兰极端的民族主义。但就其对西方知识传统对“东方学”的尖锐而彻底的抨击这一立场而言,很难说他是站在中立的地位。赛依德在批评某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时指出,将有关东方论的争论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伎俩,旨在维护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阿拉伯激进主义者也根本不买“东方论”批评者的帐,在他们看来,东方主义的批评者其实根本就不是反帝国主义的,而是帝国主义的秘密特工【22】。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抨击帝国主义的最佳方式,要不是就顽强坚持东方主义的立场,要么就保持沉默。赛依德也不得不承认,理论话语到了这个地步,“已经离开了现实世界,进入无逻辑且狂乱的境地”。

但是,赛依德在抨击那些“东方论”者的时候,他的逻辑也从来坚韧无比,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些试图驳斥赛依德的“东方论者”,被赛依德无情地批驳为:“延伸其十九世纪的论调,涵盖二十世纪末整个多到不成比例的可能发生事物;它们全都源自于一个(就十九的心态而言)荒谬的情况:即一个东方人胆敢回应东方论述的铁定论断”。【23】在赛依德看来,这些东方主义顽固的辩护者,完全没有一点自我反省的精神,就他们没头没脑的反智识心态而言--按照赛依德的说法,本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当是最典型的的新一代“东方论者”。路易斯曾在他的著作中回应赛依德的观点说,被赛依德定义为“东方论”的那种知识体系,其实不过是西方一贯坚持的对其他社会的了解,是全然由求知欲所启发的,而且相较之下,回教徒既无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获取关于欧洲的知识。赛依德则认为,路易斯的观点表现得好像是仅从学者超脱政治的公正无私立场所发出的,然而他同时又成为反伊斯兰、反阿拉伯、锡安主义(Zionist)、与冷战等狂热运动所引据的权威;所有这些运动都以高尚优雅的外表加以粉饰的狂热心态,与路易斯意图维护的“科学”或知识少有共通之处。
在赛依德看来,年轻一代的东方论学者同样在充当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丹尼尔·派普斯( DanielPipes)的著作《在神的道路上:伊斯兰与政治权力》(In the Path of God: Islam andPolitical Power;1983),受到赛依德的猛烈抨击。赛依德坚持认为,派普斯的著作所表达的观点,完全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一个具侵略性且好干涉他人的国家--美国--来服务的;其利益由他来帮忙界定。派普斯刻意描述回教徒的杂乱无章、它的自卑情结、它的自我防卫心态等等。派普斯著作同样验证了东方论述惯常的片面立场和蛮横态度,缺乏逻辑和论证。赛依德毫不客气地指责:对派普斯而言,伊斯兰是个变化多端且危险的事务,一个介入和干扰西方的政治运动,在其他各地挑起暴乱和狂热的异类。“派普斯著作的核心部分不仅是其本身与里根治下的美国有政治牵连的高度权宜性质,且在此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知不觉地融入媒体塑造的回教枪手、狂热信徒、与暴乱分子的形象中,而且还有这样的主题:回教徒自己就是他们本身历史最大的乱源。”【24】当然,赛依德的反驳不无道理,但也不难看出,赛依德旨在坚定维护伊斯兰的立场时传达出这样的意思:即西方人,或帝国主义的后裔们,无权谈论伊斯兰,更没有资格对伊斯兰的事务指手划脚,西方人被注定了是带有偏见的,因而他们的任何理解都是对伊斯兰的政治文化的有意歪曲和贬抑。跨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误读,无一例外都被赛依德置放到东方/ 西方等级对立之中,赛依德在解构这个等级的同时,其实也在强调乃至强化这个等级对立。
赛依德同样猛烈抨击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观和世界史的写作。在他看来,由维科、黑格尔、马克思、兰克等人创立的唯历史观意味着:整合全人类的唯一人类历史要不是以欧洲,或西方的有利位置为发展极点,就是由此来观察。没有被欧洲观察到,或是没能被它记录到的就此“失落”,直到此后某个时日,它才能够被人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语言学等等新学科吸纳进去。西方世界史的写作,除了有能力处理欧洲之他者的非共时性经验之外,还伴随着一种相当一致的态度:回避欧洲帝国主义与这些分别建构、分别形成和发声的知识之间的关连。赛依德表示,要在最深入基础的层次上,对唯历史观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实际作为之间的挂勾做认识论方式的批判。赛依德的批判表明,世界史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其方法论的前提和作法上,鲜少或没有注意到像东方论述或人种研究这些与帝国主义有牵连的文化活动,而它们在系谱传承来看还是世界史本身的始祖。世界史的各理论,例如,关于“全球规模累积”、或是“资本主义世界国家”,或是“集权主义系谱”,都是倚赖(1)同样立场错误的认知角色与抱唯历史观的观察者,他们在三代之前还是个东方论学者或殖民地的旅客;(2)他们也倚赖一个具均质化和吸纳性质的世界史观框架,将非共时性的发展、历史、文化和人民同化于其中;(3)他们阻碍并压抑对其体制、文化、学科工具之潜在的认识论批判,这些工具将世界史兼容并包的作法,一方面连结到象东方论述这样的局部知识,另一方面和“西方”对于非欧洲、边缘世界持续不坠的霸权挂勾。【25】
后殖民理论对西方文化批判的策略就是把它置放在一个知识霸权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背景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这样,西方的任何与东方或第三世界发生关联的知识体系,都被注定了是殖民主义论述,被注定了是对东方第三世界文化的歪曲与压迫。在另一位后殖民理论主将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论述中,西方文化在与东方发生关联的部分,充塞着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与蛮横谬误的逻辑。1988年,在美国伊利诺利洲(Illinois)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解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斯皮瓦克提交了一篇题为《从属阶级能发言吗?》(“Can the SubalternSpeak?”)的论文,该论文分析了殖民主义时期,英国殖民者关于印度寡妇自焚的论述。印度寡妇爬上死去丈夫的祭台上,然后自我焚毁,这就是寡妇牺牲。斯皮瓦克分析说,梵文对寡妇的传统译文为Sati,早期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将其译为suttee。斯皮瓦克认为,这种翻译本身就包含着殖民主义的观念在里面。在印度传统文化里,Sati的意思就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简单指自焚的寡妇。关于Suttee的殖民主义叙事,把印度妇女的自焚描述为一种罪恶,并且与谋杀、杀婴同归为一类。殖民主义者废除这项习俗,这样殖民主义者则充当了拯救者--“白人将棕色女人自棕色男人手中拯救出来”。斯皮瓦克在批判殖民主义者时,稍为玩弄了一下语词游戏,她认为,印度寡妇自焚可以表述为是一种迷信,而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认为的“罪恶”。作为一种迷信,这项习俗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
早在皮瑞尼(Puranic)时代初期(约公元前四百年)起,波罗门人就已经就sati在圣地上的认可自杀是否具教条合宜性引起争论,自杀行为当然无庸置疑,争论的焦点在于这种行为的种姓起源。波罗门人从未怀疑过寡妇必须遵循独身禁欲的法律,根据圣规的一般法令,寡妇必须回归到停滞的前身。这种法律安排不对称的主体地位有效地将女人定义为一位丈夫的客体;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它是为男性的合法、对称主体地位的利益而运作”【26】。在印度古代的一些描写sati的天赐奖赏的诗句、强调她在许多女性的竟争下,独自成为一特殊占有者的客体。这些诗句对女人在自毁仪式中的自由意志的深刻反讽也耐人寻味:“只要女人(身为人妻)不自焚殉夫,她将永不能超脱她的女性身体”。它的另一面的意义在于:只要寡妇此刻在丈夫的祭台前自毁,就可以杀死在生死轮回中的女性身体。这种自由意志的强调也设定了拥有女性身体的不幸。斯皮瓦克从她女权主义的立场去建立女性意识的反叙事,也就是女性存在、女性从善、成为好女人的欲望、女人的欲望等的反叙事。斯皮瓦克无疑也批驳了印度本土主义者的论点,在这些本土精英主义者看来:“事实上,女人愿意死”。女人的自由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权主义的控制。斯皮瓦克一方面批判了本土主义者对女性主体的性别建构,但她在批判帝国主义的时候,显然掩盖了本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性的建构。斯皮瓦克说,sati超越带有性别特殊性的男性观念,而进升为泛指人类以及灵魂的普遍性。在圣典中,sati是本质、宇宙灵魂。作为一个前置词,它还是合适、快乐的意思。在这种文化神秘的美学意义在斯皮瓦克批驳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时,被过度夸大了。她把“自焚”解释为“迷信”,而这种“迷信”是男权历史建构的结果,而不是象帝国主义所认为的是一项“罪恶”。在斯皮瓦克看来,这非自杀的自杀可以读成真理-知识和地点虔敬的拟象,“对于男性主体而言,自杀的快乐废除了它的地位。对于女性主体而言,认可的自毁带来了对其选择行为的赞美。靠着性别主体的意识形态生产,这种死可以被女性主体了解为自己欲望的例外意符,超越寡妇行为的一般规条。”【27】
斯皮瓦克的结论是,本土主义或反种族中心主义对Sati神话的解释表现出男性种姓权力的意味,而古典印度教中的女性主义也受到本土主义的污染,斯皮瓦克的结论是,“从属阶级不能发言”。尽管斯皮瓦克再三声称她“不是在倡导扼杀寡妇”,但她对帝国主义拯救寡妇自焚这一“社会使命”的尖锐揭露,明显掩盖了她对本土国族主义的批判。她的揭露是积极的,激进的,但她对待第三世界文化的态度却是消极的。既然帝国主义不能真正理解第三世界文化,帝国主义世界做出的“社会使命”,都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误解,那么只有一种方式是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尊重,那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有保持从属阶级的历史状况,尊重历史业已形成的传统“迷信”,这才是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尊重。事实上,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论述中,她的主攻方向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任何文化输入都被视为是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压迫行径。问题的实质在于,斯皮瓦克拒不承认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确立的文化价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试图向全球推广自由、平等、民主等文化价值,这些都被斯皮瓦克看成是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文化渗透,其目的不过是更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人民。事实上,口口声声反对本土主义的斯皮瓦克,离本土至上主义并不遥远,显然,她一直把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相对立。斯皮瓦克把印度接受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统统斥之为“帝国主义遗产”,帝国主义遗产对印度本土文化构成破坏。她认为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不是印度本土的,因为它们不是起源于印度,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印度人,因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起源于欧洲,印度不应该是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因为世俗主义是西方的社会结构。斯皮瓦克以及印度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说,议会民主制度不适合印度,印度应该发明本土化的社会科学和本土化的政治形式。总之,民主、社会主义和宪法,在斯皮瓦克看来,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遗产”【28】。
后殖民理论当然十分复杂,但在它的几位杰出代表人物那里,可以看出它明显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混合产物。后殖民理论率先在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流行,七十年代以来的英语文学教授中前卫分子普遍受解构主义的影响,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考古学,早就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起源和知识霸权的形成,进行了透彻的解剖,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核心任务就是拆解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尽管近年来人们对解构主义的兴趣有所减退,但这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就走向穷途末路。人们乐于把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以及后殖民理论的走红理解成是对解构主义的替代,事实上,这不过是人们在理论综合的水平上更加广泛地运用解构主义而已。解构主义已经深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骨髓中去,很难设想当代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可以与解构理论划清界线。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显然是福科和德里达的调和。这在赛依德、斯皮瓦克、哈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表述中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赛依德的代表作《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很明显是在运用解构主义方法。至于斯皮瓦克这个印度裔美国学者,她的成功起点建立在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等作品的基础上,把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混为一体,使斯皮瓦克的表述含混不清又锐利无比。至于近年走红的哈米巴巴,更是不折不扣的解构主义者。在他早些年(1983年)发表于《屏幕》(Screen)上的文章《他者的问题》,开篇就引述德里达在《结构、符号与游戏》中的观点为题辞,他对“固定性”(fixity)的追问展开论述,对现有的知识和话语权力构造的殖民主体进行解构,这些无疑是解构主义的具体实践【29】。他最近的名躁一时的著作《文化的位置》(The Location ofCulture),可以看出解构方法更加娴熟运用的情形。总之,福科的理论无疑构成了后殖民理论的强大基础,而解构主义则提供了锐利的方法,这使后殖民理论家在分析帝国主义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时游刃有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后殖民理论如何把帝国主义的知识巧妙挪用到和编织进反帝国主义的文化实践。如果再进一步考虑,这种文化实践主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校园里兴盛,这又使人们不得不意识到后殖民理论终究难逃帝国主义“文化遗产”的巢臼。
五、大众文化:新的压迫与解放
大众文化或传媒研究就其专业方法构成而言,是社会学、文学理论与艺术批评三者结合的产物。显然,新近的文学理论方法是其主导方面。这个貌似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实质则是新理论的前沿地带。庞大而渊源流长的法兰克福学派,福科、拉康、威廉姆斯、德里达、鲍德里亚得等人的学说则构成这个领域的理论基础。
就其审美认识论的理论渊源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的阐释,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文化工业”的批判,都成为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经典文本。就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生产批判的理论前提来说,实际是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文化生产批判的理论立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30】在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看来,例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由资本主义大企业控制的文化工业,正在把个人塑造成集体类同的一分子。在那篇著名的攻击大众文化的论文《文化工业,欺瞒群众的启蒙精神》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写道:“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31】信奉艺术的乌托邦或“艺术是幸福的承诺”这种理想,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坚持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艺术观念,阿多尔诺写道:“根据内在批评,一部成功的作品决不是一种在假和谐中解决客观矛盾的作品,而是表达了真正和谐观念的作品,这是通过将纯粹的不妥协的矛盾不定性地体现在作品的最内在的结构中完成的。”【32】持这种观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理所当然对普及性的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次大战战乱期间,从欧洲来到美国,他们对独裁制度有着天然的警惕与批判,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也正面临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全面控制,文化独裁主义正在侵蚀这个好称多元民主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对资本主义文化控制的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几代学者的思想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学院知识分子普遍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展开猛烈抨击。就从知识分子的普遍立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这本来就是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很难设想西方的学院知识分子能够理直气壮地为现实辩护。从理论上讲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既然现实已经很好,那还有什么必要为之辩护呢?
法兰克福学派出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把批判指向定位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对大众意识的控制方面,大众被看成被动的客体,匆略了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文化批判理论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隐含的能动力量。威廉姆斯和霍尔无疑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首要代表人物,他们都来自普通劳动阶级家庭,都有过做成人教育教师的经历,这使他们注重民间社会对媒体的积极反应。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的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年青一代的文化研究者进一步去发掘在现代媒体霸权结构中,文化接受主体的内在多重结构,以及能动实践的可能性。威姆斯“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的观点,不是把文化单纯看成是现实反映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看成构成和改变现实的主要方式,在构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起着能动的作用。因此,威廉姆斯认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他指出:“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述,同样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的澄清。”【33】威廉姆斯推动英国的文化研究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进入到生产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内部实践。在六七十年代,威廉姆斯是少数为媒体辩护的知识分子,这主要基于他的平民主义立场,以及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依然保持的革命性意识相关。他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把人类对媒体的使用归结为四种类型:其一、父权主义,即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操纵媒体;其二、权威主义,即媒体被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三、商业主义,即媒体以积累财富为主要目标;其四、民主模式,其中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威廉姆斯指出,如果现代社会以第四种方来使用媒体,那么,一个有创造性的、民主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将会产生。事实表明,威廉姆斯对媒体的期望过于理想化,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文化”都没有如期实现。但威廉姆斯的设想使人们开始去思考媒体可能提供一个新的交流空间。
六、七十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英国的文化研究有显著的影响。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就是在广泛吸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把文化研究推向当代媒体和大众日常生活领域。斯图亚特·霍尔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相结合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他关注到意识形态编码与大众的解码策略的相互作用,揭示出当代媒体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实践。霍尔认为,大众媒体形成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系可以被发挥为提供系统程序的交往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主导知觉的生产也就被制造出来了。更进一步地说,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利用受其支配范围的社会解释聚集而形成表现现实的符号,被公众接受的符号因此显示为自然的系统而自觉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也就保证了阶级社会的再生产。霍尔分析了撤彻尔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进入民间社会,并获得民间社会的赞同,通过把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社会的想象关系,撤彻尔政府有效地支配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霍尔说,撤彻尔的天才之处在于,她能够把多样性的在文化上具有复杂化的认同压缩进强有力的霸权结构。霍尔的文化分析显然是把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揉合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偶然环节和不断转变的连接关系,这使他更清晰地揭示了政治、经济斗争中的意识形态策略的传播和接受的具体过程。【34】
作为新一代的左派理论家,霍尔的理论融会结构主义以来的各种学说,他对媒体的研究乃是在他持续不断与后结构主义各种理论对话中展开的,批判、质疑,从而丰富了自己,这使霍尔的新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费斯克(JoneFisk)在论及霍尔的思想时指出,虽然霍尔怀疑后现代主义,但在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传统人里面,霍尔是最接近后现代状况的人【35】。他对封闭系统的开放性处理适应后现代的流动性变易特征。如果不过于固执后现代的非决定性观点,霍尔强调结构始终在自行运作。他关于关联(articulation)的理论明显是与德里达拒绝意义的任何固定性(fixity)观点相共鸣。他坚持认为意义是被制造的,是被放置和以特定的方式使用的。霍尔否认现实具有实在本质,他坚持认为现实的表象系统与现实没有区别。在这一点上,霍尔与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所谓的现实本质,不过就是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那些范畴和等级而已。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霍尔的观点与另一个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得里亚德(Baudrillard)相通之处。他关于现实表象化(representations)的看法,类似于鲍得里亚德的现实“仿真化”(simulation)的观念。当然,霍尔的理论目标在于他的左派立场,对资本主义媒体霸权的“解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
威廉姆斯和霍尔的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36】,特别是他们关注民间社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应方式,引起新一代的大众文化研究者把注意力投向观众主体。费斯克(JohnFisk)是八十年以来对媒体研究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接受了霍尔的编码/ 解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关注大众群体社会对资本主义媒体霸权的解码能动性。费斯克所有的理论都贯穿着一个宗旨,那就是他始终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文化生产的主导形式,与消费者积极的再创造意义相区别。在这一点,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明显不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意味着,消费者愈来愈接近产品,但费斯克认为文化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发挥他的主动性的解码功能,促使文化产品转化为他所愿意接受的形态。他在1989年出版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公开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37】。费斯克甚至选取比较极端的例子,如麦当娜这种极有争议的文化明星,他认为麦当娜在传媒的不断谈论中,她的文化意义已经历经了多个级别的转换,从电影、电视、书籍和图片等等第一级别的文化形象,到各种影视节目、报刊杂志和种种评论,麦当娜的形象已经被大大拓展,费斯克特别提醒人们应注意到麦当娜的形象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他认为麦当娜的形象是对传统男权社会关于处女的典型形象的颠覆,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瓦解了经典的妇女象征体系。麦当娜是一个开放性的写作着的文本,它表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大众化的符码,文化工业对这个文化形象的推广,事实上是使民众再造了它的意义,促使它从男权定义的文化象征秩序中解脱出来。费斯克分析试图表明,大众文化可以制造积极的快乐--反抗文化集权的抵制的快乐。
费斯克把他的理论描述为“关于愉快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看来,愉快的形式来自对权力集团控制的严密的技术主义体系的反抗,公众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阅读包含了双重愉快,其一是包含在反对权力集团的象征生产中;其次包含在自我行为的实际生产过程中。费斯克认为现代官僚制度为少数权力集团所控制,民众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大众文化,可以打破“议会民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差距,参与到当代政治中去。大众文化产品在其展开中就可以表达民众对权力集团的批评。少数权力集团认定的客观真理,正在被大众文化实践所瓦解。作者不再是作为上帝的声音表达真理,在大众文化生产实践中,观众作为积极的创造者,日益创造这个时代新的感觉方式。大众文化实践使普通民众抵制权力集团的文化专制,有能力参与到现代象征性的(或者说符号化的)民主体系中去。
费斯克甚至对大众读物和流行小报也给予积极的评价。在他看来,高品味的出版物受占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所支配,它们创造这个时代的信仰主体,而流行小报则怂恿芸芸众生发现各种批评的形式并制造怀疑主义式的快乐。费斯克说:“给予不信任的怀疑主义式的欢笑,从而表达他们不在其中的愉快。看穿了权势者们的大众愉快,指明了这就是从属阶级长期不能发展为主体的历史性结果。”【38】费斯克重新理解并为大众文化全力辩护的观点,无疑打开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激烈的批评。例如英国的尼克·史蒂文生(NickStevenson)就对费斯克的观点提出多方质疑。史蒂文生认为,费斯克并没有对文化接受的象征形式的制度化结构给予足够的关注;他的观点排除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他关于大众出版的观点没有包含实际内容的具体调查(实际的情形可能是大众读物充当了文化霸权集团的同谋);而且他对公共领域的分裂的政治重要性缺乏批评性的概念;史蒂文生认为费斯克一直在把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与公众的阅读混为一谈【39】。尽管费斯克招致不少批评,但不管如何,他关于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力控制和文化集权的看法,在大众文化弥漫着激烈抨击和消极悲观的双重态度的文本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一次对后现代时代的文化主体的重塑,他的观点既使不是对现存事实的发现,至少也可以看成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期望。
马歇尔. 麦克卢汉( Marchal Mclluhan)是最早提“地球村”概念的社会学家之一【40】,在六十年代,麦克卢汉的开拓性研究在媒介就影响卓著。从总体上来说,马氏早斯的观点对消费社会还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当代文化仅仅提供了莫衷一是的幻想形式,同时提供制造大众群体,缩减高雅文学的社会基础。可以看出麦氏前期的观点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但另一方面也与威廉姆斯的观点也有不少的相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麦氏后来的大量写作却与早期观点大相径庭,他再也不把文化内涵作为他的首要观点,而是把重点放在文化传播的技术性意义上。麦氏理解媒体(media)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而是把它看作社会交往的技术媒介(medium),麦氏说媒介就是讯息(message)。按照他的观点,去关注日报中的文章的意识形态或符号结构,就肯定把握不住其中的要点。而那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有效地转化和形成了新的时空关系(例如,电灯照明、交通、通讯等等),重新结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和感觉方式。他的现代技术论不再是一种批判性的异化理论,技术已经被他看作是人类躯体和神经的有机扩展(例如,他把车轮看成是人类双足的延伸,服装则是皮肤的扩展)。麦氏把传统的人类交往形式向现代技术手段的转型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内容。不少对媒介技术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都把电子媒介看成是对传统文化时空的消灭。但麦氏坚持认为,现代媒介创造了文化接受的新的时空(例如,现代人可以公共汽车、火车上阅读,在汽车的收音里接收新闻),全球化时代的公众可以比口头表达的社会更高程度享有同一的文化。地球村已经抹去了印刷制品时代文化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客观上消除整体性和个人主义的文化,电子化并没有因此而构成中心化,而是反中心化。
麦氏的观点为一部分人所称道,也引发不少的批评。威廉姆斯和霍尔对麦氏都有批评。麦氏过于强调媒介的技术性作用,他把一切文化成果都处理为技术程序(似乎是反文化唯物论其道而行之),他的理论忽略了大众交往的象征意义分析,也没有深入分析统治社会关系的相关的社会组织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麦氏有些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有些观点又明显是与后现代主义相佐。后结构主义认为社会和技术关系与意义的生产相分离的观点,受到麦克卢汉的修正。就大众传媒的研究来说,自威廉姆斯和霍尔到史蒂文生和麦克卢汉,可以看到二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到挑战,传媒不再仅仅被看成是消极的和压制性的,同时也被看成是重建现代主体的公共空间。其二,对现代传媒的研究最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话的结果,不管是象威廉姆斯和霍尔这样的领风骚的人物,还是各路后起之秀,都不可避免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展开对话,某种意义上,传媒研究在总体上乃是后结构主义理论进一步拓展的实践。
鲍德里亚 ( Jean Baudrillard ) 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他的理论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文化研究最有份量的一部分。正象所有的法国大师墙里开花墙外香一样,八十年代鲍德里亚在美国走红,他的著作几乎全部被译成英语,并被人们争相谈论。他关于文化符号学的阐释,关于消费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析,这些都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阐述。鲍氏最初的理论论述可以看成是对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论战的产物。六十年代,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统治了法国的知识界,鲍氏开始也追随阿尔都塞,但很快他就与阿尔都塞有根本的分歧。这首先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体的自我生产的看法上。阿尔都塞说,通过阶级等级和意识形态过程而构成主体。但鲍氏认为,在后工业化来临的时代,社会主体的构成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意识形态机器主要是消费资本主义,现时代的社会主体不过是消费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则被鲍氏看成一种没有现实实在性的符号体系。与鲍氏同时期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凭借电视和广告,个人存在转化为现实主体;但鲍氏认为,与产品相关的符号话语与现实无关,主体被符号化,正如现实被符号化一样。他的理论分析表明,物品在被消费前就变成信息(signs),客体的意义通过信号系统进入符号(code)秩序才被建立。鲍氏的《象征交换与死亡》等一系列著作,重新思考了文化、政治、经济和消费结构的内在联系。
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鲍氏被人称之为法国的麦克卢汉。这主要基于他的不少观点与麦氏相对。例如,前面提到麦氏认为媒体可以给大众提更多的参与机会,公共空间可以消除权力的整合。但鲍氏却坚持认为,主体化的有效形式在媒体混乱不堪的交往关系中消失殆尽,而符号科学则被社会的“液化”(liquefaction)取而代之【41】。他最有名的观点是关于“仿真”(simulation)的论述。他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化价值历经了三种“仿真”的阶段:其一、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仿造”(counterfeit)是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其二、在工业化时代,生产(production)是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其三、在当代符号繁衍扩展的时代,仿真(simulation)是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第一种文化秩序的仿真物(simulacrumy)建立在价值的自然法则基础上;第二种文化秩序的仿真物建立在价值的市场法则基础上;第三种文化秩序的仿真物建立在价值的结构法则基础上。【42】鲍德里亚关于现实、超级现实与仿真的关系的见解颇有点惊世骇俗。他认为,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必须以颠倒方式来理解,今天,现实自身就是超现实,超级现实主义(surerealism)的秘密正在于日常现实可以成为超级现实,仅仅在于现实提升了艺术与想象的时刻。今日的日常生活,举凡政治、社会和历史、经济等等,现实已经在仿真的方式上与超现实合并一体,以至于我们现在生活在现实的审美幻象之中。鲍德里亚说,“现实比虚构更陌生的老生常谈不过表明生活审美化的超级现实主义的阶段已经失控,再也没有任何虚构能与生活本身相匹敌。现实已经完全进入现实自身的游戏领域,根本的不满,冷漠的控制论的阶段,代替了热烈的幻想阶段。【43】鲍德里亚把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活看成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象,按传统本质论或本体论哲学所设定的“现实”、“真实”、“本质”等等概念都受到根本的怀疑。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已经为符号以及符号对符号的模仿所替代。日常生活现实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一个审美化和虚构化的过程,它使艺术虚构相形见拙,并且它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虚构。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物品(goods)只要被消费首先要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产品,例如为广告所描绘,为媒体所推崇,成为一种时尚,为人们所理解,才能成为消费品。显然,在鲍德里亚看来,语言符号构成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语言构造了后现代消费的现实。语言不仅描绘现实,同时也创造了现实,而现实反倒成为语言的仿造物。鲍德里亚说,现实和符号都挤进象征,如没有弗洛依德主义就不会有“无意识”这一说,也正如马克思象征性地创造了无产阶级。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鲍德里亚几乎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居然不承认现实实在的存在,他把语言的存在看成是第一性的,而“现实”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不过是语言的模仿物。尽管鲍氏深入而独到地考察了生产和消费、经济和文化、物质和象征的关系,但这一切都是置放在符号学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正如史蒂文生所说的:后工业经济固然在物质地生产客体的同时,也象征地生产消费。但最重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悖离人们的物质需要;消费社会的产品,不管被设计成千奇百样,被推销广告强调到何种程度,也不可能丧失其基本的实用功能【44】。鲍氏过分强调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的文化象征意义,以至于完全不顾及到物质和实际的生活需求方面。虽然鲍氏不无偏颇,但我们依然应该看到,鲍氏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某种特征,在后现代社会视觉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日常生活形式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人们是如此深刻地为媒界所控制,不管是单向度的接受还是有机的抵抗,都无法拒绝符号对当代生活的绝对有效的支配。总之,鲍德里亚重写了符号/ 现实的关系,以他特殊的理论视角疏理了当代生活世界的主体与客体的构成和交往形态,他的观点虽不无极端,但无疑有他的精辟之处,因而他在当代欧美大众文化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六、 结语: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新的理论期待
文化研究不是什么统一的流派,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它不过是正在形成的跨门类的课题,表现了当代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趋于综合的时代潮流。文化研究实际汇聚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学批评诸多门类的知识。就文化研究普遍注重文本分析方法而言,它更象是传统文学批评学科的变种。传统文学批评被无限制放大的同时,也被抹去它的学科界线。在文化研究的视域内,任何事物现象都被看成文学文本(或者说可以当成文学文本细读),同样,文学文本也被当作文化文本加以象征性地阐释。尽管说文化研究显示出知识的花样翻新和方法论的开拓进取,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没有超出后结构主义的范围,而它把各种知识放置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上加以融合,与其说是对后结构主义的超越和替代,不如说是对后结构主义潜能的全面发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文化研究研究标志着一个“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
后结构主义在法国的六十年代后期崭露头角,那时人们不过把它看成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伊迪斯·库兹韦尔1980年出版的《结构主义时代》一书,有三分之一的结构主义者,实际上已在着手“后结构主义”的事业。六十年代后期,法国的思想界发生不动声色的变革。五十年代的存在主义的统一性意识形态解体后,结构主义的客观性观念暂时在法国思想界形成统一的思想氛围。但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使左派知识界的意识形态迅速瓦解。后结构主义是在知识分子失败的意识形态氛围里找到另僻精神飞地的。知识分子从激进的社会革命,退回书斋;同时也从意识形态的整体规划,退回到语言的无限意指活动中去。然而,知识界的撤退并不意味着思想的倒退,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福科、德里达、德留兹、居塔里,以及稍后的布迪尔、鲍得里亚和列奥塔等人,都以对他们直接的学术传统--结构主义的批判,导向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为新的起点。在他们尖锐的理论批判实践中,其实也蕴含着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基础的努力。法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反结构主义和反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倾向,开始不过是被学术界视为一种比较独特怪戾的大陆思想流派。在整个八十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已经不容思想界怠慢,各种思想理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的知识体系,都不得不与之对话。后结构主义饱经风霜,没有一个学派或一种知识,自从它问世以来就遭致到象后结构主义如此猛烈的攻击和无休止的争议。其结果却使得后结构主义以不可阻挡的理论势头迅速蔓延,后结构主义在各种理论的争议中而扎根于其内,这可能是当代思想所意想不到的后果。当人们自以为后结构主义日渐式微时,不久即将发现,当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思想出发点定位在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上。某种程度上改头换面,不过是使后结构主义与其它门类的知识结合得更加广泛和深入而已。文化研究的兴起,当然与现代传媒和现代高科技有关,但后结构主义在其中所起到的内在聚合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准确理解当代思想潮流和知识霸权更新的历史趋势。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历史在政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结束以后,留给知识分子的,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思考,同时也是现实的抉择。学院知识分子习惯的学术政治化倾向,也遇到挑战。九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有着相当大的分歧。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例如福山),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理想,以及自由民主观念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世界历史已经不再需要政治的意识形态去引导人们的思想。然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乐于去发现潜伏在和平格局表面下的危机。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与区域冲突,使一些知识分子有理由认为未来世界历史不可能是风平浪静。享廷顿设想未来文明冲突可能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展开。享廷顿的思路还未摆脱冷战格局的阴影,只不过把前苏联换成趋于强盛的中国,把政治意识形态换成宗教(或种族)。一些知识分子过于乐观,另一些又太悲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们已经很难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构造新的世界秩序。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当然也深刻影响到知识分子阵营,现在已经不再可能用意识形态来展开学术话语的推论实践。但“知识分子无法拒绝政治”(丹尼尔. 贝尔语),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依然贯穿在学术体制领域,经历过后结构主义的洗礼,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反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转变为思想文化意义上和历史观意义上反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反省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反省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左派激进主义运动,把学术变成政治,而后结构主义以来的潮流,则是把政治变成学术。准确地说,把政治问题学术化了。资本主义的启蒙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帝国主义的霸权历史等等,这些政治历史,现在都变成最丰富的学术资源,给后结构主义式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广大而任意的想象空间。后结构主义从语言和文本分析的领域,直接进入帝国主义历史档案馆,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这使它获得新的生机和机遇。在这一历史机遇中,知识分子又获得一种内聚力,不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又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说话。最重要的在于,一度迷惘和空洞的学术政治,再度获得了切实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内容。冷战后的政治格局,给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研究提示了理想的背景。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文化研究正是冷战后的政治格局的恰当表达。现在,“政治上正确”在大学校园内,并不需要直接参与,而仅只是一种学术态度,仅仅是对一种知识的运用,对一种学术方法的把握。学术必须具有政治性,但又不实际具有,这种象征性的学术政治,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的必要内容而已。文化研究力图表达的大学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多少有些故做姿态,虽然是受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的惯性支配,但也象是在挥霍西方的学术自由。而那些后殖民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学墙院内,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看上去象是标谤第三世界的立场,但实质不过是对西方学术话语的发挥或挪用,并未超出西方文化范围。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度滋长出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情绪,这与回归中国传统民族本位的思想意向不谋而合。后殖民理论确实提示了思考近代以来世界文化的新思路,但在用东方/西方二元对立去描述近代文化史时,却要给予充分的警惕,对其历史的虚构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近代中国在文化上从未被殖民过,相反,“现代性焦虑”( 或启蒙的焦虑) 反倒一直是摆脱本土文化集权主义的内在动力。
当然,大众文化研究在重新思考后工业化社会主体的构成及其超越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对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人(主体)已经在历史和当代实践中消失,后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特征,使它把人看成一种消极的符号,是被强制性的结构秩序所决定的任意的符号。人在社会实践中不具有主体性的地位,正如人消弥于历史的结构中一样。重新关注人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关注人在接受后现代传媒时具有的主体抵抗意识,这显示了现今文化研究的建设性意义。经历过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长期的批判之后,也需要重新思考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多重性特征。
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当代学界还属于相当陌生的领域。尽管在八十年代,学界有过“文化热”,“反传统”或“全盘西化”,但这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引导下的思想论争,带有相当强的实用性。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那时的“文化”,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大文化概念,关于跨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从西方传统人类学的角度为理论参照系。而现今的文化研究--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乃是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多门类知识会聚,或者说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是后工业社会文化状况的反映;如果以后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看,与其说它描述和反映了,不如说它创造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扩张的想象图景。文化研究可以说对当今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中国的文化现实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无疑做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不管是关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还是引进西方现代理论,应该说都有相当的成就。但就理论批评的基本构架而言,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和理论来说,基本还是延续五十年代的理论模式,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反映论、文学的主题与形式等等理论范畴,没有任何变动。至于文学批评方法,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还是把文学当作单一的艺术文本来看,在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也是在反映论的意义上进行阐释,对文学的把握从来没有超出艺术感受的范畴。如何把文学看成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一种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象征系统的符号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很少关注的问题。以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文本之外无他物”,并不是说在细读的原则下,把文学文本看作一种字词和句式的修辞物,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去发掘其中隐含的社会历史内容。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越来越具有文化色彩,过去的意识形态特征,现在为更多重的历史实践所制约。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是美学的角度,不足于把当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管从哪方面看,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调和的产物,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调和,使当代文学(包括创作与理论批评)更象是一种“亚文学”,一种类似霍米. 巴巴说的“文化杂种”。九十年代文学被卷入当代文化潮流,它再也不可能象八十年代初期那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引导时代精神行进。它现在更象是捆绑在消费社会这架欲望化战车上的俘虏,只是在它勉为其难的挣扎姿态中,还保留有传统文学的流风余韵。而另一些自以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其实不过是分享剩余意义的附属品。相比较而言,前者还多少有些末路人的悲壮,而后者则徒具冠冕堂皇的外表。这种描述并不是有意贬抑当代文学,而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所具有存在方式,也由此决定了中国文学更具有复杂的隐喻和象征的(文化)意义。在把它们看成美学文本的同时,更有必要从中读出多重的文化象征意蕴。这就是文化研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更新的借鉴意义。
当然,文化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之处还在于,对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研究有直接的示范意义。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但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发展中国家,就其发达城市来说,与发达国家相去未远。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正在给疲惫的二十世纪末注入兴奋剂。世界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国关于自身的想象正在迅速展开。中国在九十年代快速城市化和消费化,使得中国的城市也迅速进入文化幻象的时代。光怪陆离的写字楼,大型现代化商场,广告,休闲读物,周末版报纸,滚动式的电视节目,卡拉OK,点歌,体育竟赛,时装以及多媒体电脑的日益普及……等等,城市生活已经完全为符号和幻象所重新结构编码。例如,中国的数个大城市的空间已经迅速审美幻想化了,过去不过是用于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完全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空间,现在却是为各种现代化的新型建筑材料所重新编码,特别是那些华丽的、魔幻般的建筑材料的广泛运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发达地区正在构筑一些超级的幻象空间。这些空间与那些低矮的平房、粗陋的阁楼、混乱的工棚等等相得益彰,使得相互间都失去了实在的真实性,如同电影的布景和道具一样似是而非。它们并不仅仅是物理时空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城市,而且以中国最新、亚洲最高、世界最大……等宏伟叙事,使这些空间打上奇特的关于中国,中国关于自身的二十一世纪的想象。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事例而已。事实上,电视的普及和印刷物等传媒的迅速扩张,使中国的大众文化正在强有力地改变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改变着人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
这一切在学术界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关于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还处在相当低级的水准上,其观念和方法不过是传统文学批评的简单翻版而已。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现实,给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关于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与新的文化公共空间建构问题,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集权特征与民众的主体重建的冲突问题,关于大众文化的寄生性与颠覆性的双重性质,关于后现代时代文化霸权与个体能动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给西方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提示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当会引起新一代文学、社会学、大众传播研究者的重视。新的知识的会聚,跨学科研究视野的建立,都是势在必行的趋势。说到底,“后-后结构主义时代”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它表明一种思想理论的趋势,表明在当代知识爆炸的情势中,人们再也不可能偏执于某个单一的视角,某种狭隘的立场展开学术实践。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来说,更没有必要拘泥于狭隘的学科限制,也不必过分执着于东方/西方人为界线,不必纠缠于中国本位还是舶来品的空洞争论,走出早已僵化的体系模式,面对中国转型期剧烈变动的现实,开拓视野,必将会创建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新局面。
注释:
【1】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Lawrence Grossberg, CaryNelson, Paula Treichler; Routledge, 1992; page,3
【2】【13】Fredric Jameson, " On'Cultural Studied'", " Social Text", No.34, 1993.中文译文可参见《漓江》杂志,1997年,第1 期,谢少波译。第111页。
【3】Richard Johnso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Text 6.1, 1987, 38-39.
【4】TerryEagleton, Ideology of Aesthetics, page 381, Oxford: Black well,1990.
【5】J·希利斯·米勒,《主席演讲,1986:理论的胜利,对阅读的抵抗和物质基础问题》,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102卷,1987年,第283页。
【6】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
【7】托尼·贝内特:《文本在历史中:阅读的决定因素及其文本》,载《后结构主义与历史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74页。中文译文参考彭加明译,路易·蒙特鲁斯《论新历史主义》,载《漓江》,1997年第1 期,第135页。
【8】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Englan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the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8, Page,1.
【9】参见《解码福科:地下笔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FoucaultDecoded: Notes from Underground",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文译文,可参见张京媛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10】【12】Stephen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Chicago: Univ.fo ChicagoPress, 1980,Page, 6.
【11】参见Frank Lentrichia:Foucault's Legacy: A New Historicism", 载 H·Aram Veeser ed, The newHistor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page235.
【8】该文最近收入《当代后殖民理论》一书,参见"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Edited by Pandmini Mongia,London, 1996.
【9】【10】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Death,Translated by LainHamilton Grant),英文版,1993年,London,第50页,第74页。
【14】参见丹尼尔. 贝尔: 《西方意识形态的末路》,中文译文可参见 《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7页。
【15】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述,可参见爱德华. 希尔斯《意识形态终结了吗?》,载《会唔》1955 年第5 期,第52-58页;关于意识形态衰落的本质与根源的分析,参看赫伯特. 廷斯坦的《瑞典民主制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载《政治季刊》1955年第2 期,第140-151页;或参见奥托. 布伦涅尔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载《研究社会历史的新方法》,哥廷根1956年,第194-210页;关于意识形态的时代正在终结的预言,参看S. 福伊尔的《超越意识形态》, 载《心理分析与伦理学》,斯普临菲尔德1955年,第126-130页。丹尼尔. 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格伦科,1960年;拉尔夫. 达伦多夫著《阶级与阶级冲突》斯坦福1959年。
【16】九十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换了一种说法。1991年日本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出版,引起绪多的争议。但大多数学院知识分子赞同福山的论调。
[17] 例如,辛普森案件就是反种族主义的一个惊人的成就,尽管其中缘由与美国的司法制度的漏洞不无关系,但这也表明反种族岐视的社会力量正在普遍高涨。试想,泰森锒铛入狱,不过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小小胜利,如果对方是一个白人妇女,可能泰森不至于遭受铁窗之苦,这就是说种族问题可以放置在妇女问题之上。而美国一个西班牙妇女割去丈夫的阳具却能消遥法外,这也足以说明妇女的地位在发达国家正在迅速提高,妇女的权益不能得到任何侵犯,而以身试法的男人却必然身败名裂。
【18】联合总部曾雇佣一名黑人女职员。此人后来解雇,理由是她工作不认真,处理不好同事关系,由此引发黑人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参见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载《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
【19】参见苏红军《第三民办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同上书,第31页。
【20】参见:The Third World Women andFeminist Politics. 《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Page, 92.
【21】周蕾:《在其他国家中的暴力: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和妇女》,参见:The Third World Women andFeminist Politic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年,Page, 93.
【22】【23】【24】【25】参见赛依德:《东方论再思》“OrientalismReconsidered”,转引自Literature, Pllitics, andTheory: 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 1976-1984. Eds. FrancisBarker et al. London: Methuen, 1986. 2100-2129.
【26】【27】参见斯皮瓦克:《从属阶级能发言吗?》(“Can the SubalternSpeak?”)载Marxism and the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1988.
【28】斯皮瓦克的有关论述参见《在教育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Machine),London, Routledge,1993. 对斯皮瓦克的批评可参见Aijaz Ahmad的《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iteraryPostcoloniality),载《当代后殖民理论》(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Theory),Edited by PadminiMongia,London,Page,279.
【29】参见《他者的问题》(The OtherQuestion),该文最近收入《当代后殖民理论》一书,参见"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Edited by Pandmini Mongia,London, 1996.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
【31】【32】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辨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145页。
【33】雷蒙·威廉姆斯:《漫长的革命》(The LongRevolution),第57页,伦敦,1961年。
【34】霍尔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Thatcherism anongst thetheorists, Toad in the Garden,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1988. 关于霍尔目前研究最详尽和最新的资料可能是1996年出版的Stuart Hall ---- Critical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一书,该书由David Morley 和 Kuan-hsing Chen 编辑,由Routledge出版,收集霍尔的主要代表作和主要研究文章。
【35】JohnFisk, Opening the Hollway -- some remaks on the fertility of StuartHall's contritbution to critical theory. 参见Stuart Hall ----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Studies 一书,由David Morley 和Kuan-hsing Chen 编辑,Routledge,1996, London, Page214.
【36】关于威廉姆斯和霍尔对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可以参见HonnoHardt的“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d the return of the 'critical' in American Mass communicationresearch: Accommodation or radical change?”参见‘Stuart Hall ---- Critical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 by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Routiledge,1996, London, Page102-111.
【37】John Fisk "Understanding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age 24.
【38】‘Popularity and thepolicies of information’, in P.Dahlgren and C.Sparks (eds.),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Page48.
【39】史蒂文生的批评可参见’Understanding MediaCultures ‘(《理解媒体文化》)
,Sage, London, 1995, Page, 94-101.
【40】1968年,麦克卢汉出版《地球村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Global Village’New York, Bantam Books.1989 年,他与B.R.Powers 合作出版《地球村》一书,应看成是他的总结性著作。
【41】【42】【43】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Sage, London, 1993, Page 50,74.
[44] 史蒂文生 Nich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Cultures’(《理解媒体文化》)
,Sage, London, 1995, Page, 153.
原载《文化研究》创刊号。第1-42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