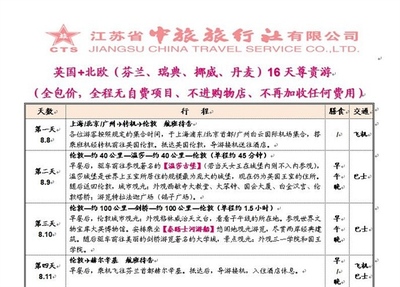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一件将军的铠甲只是铠甲,并不是将军:剥掉铠甲,将军照样呼吸。杀掉将军,铠甲依旧存在。这不是一个妥当的比喻。如若“陀斯妥夫斯基往往是被当做好像没穿制服的将军”,并不妨害陀氏之为伟大。所以铠甲不是形式,而是辞藻。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其当,增加美丽;否则过犹不及,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他或许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这只是他整个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评家唯恐冒昧,轻易不敢把这叫做“偏”,而另寻别的字样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由一个全人格产生出来的作品)根据着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谐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样一个犄角观察;是客观的,然而有他性情为依据;是主观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来驾驶。而完成又有待乎选择或者取舍;换而言之,技巧。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一致。
因为思想或者背景的同异,读者可以否认某些材料的使用,然而绝对没有权利抹杀它们的存在。
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我却偏要介绍一九三四年的一篇短篇小说,那篇发表在《学文》杂志第一期的《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的制作。我相信读者很少阅读这篇小说,即使阅读,很少加以相当注意。我亲耳听见一位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我承认他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他有的是学问,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点点想象。真正的创作,往往不是腐旧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一部杰作的存在,不仅在乎遵循传统;然而它抛不掉传统,因为真正的传统往往不只是一种羁绊,更是一层平稳的台阶。但是离开那些初步的条件,一部杰作必须有以立异。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人性上绝大的差异。根据各自的禀赋,他去观察;一种富有个性的观察,是全部身体灵魂的活动;不容一丝躲懒。从观察到选择,从选择到写作,这一长串的精神作用,完成一部想象的作品的产生,中间的经过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的;唯其如此,一以贯之,我们绝难用形式内容解释一件作品,除非作品本身窳陋,呈有裂痕,可以和件制服一样,一字一字地皍扯下来。
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我绕了这许多弯子,只为证明《九十九度中》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着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仅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自成一个绝缘的系统。所以影响尽管影响,《九十九度中》仍是根据了一个特别的看法,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

一九三五年
(摘自《咀华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