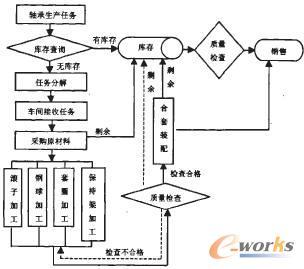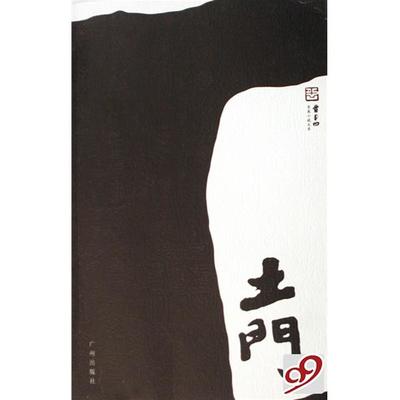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研究是个不完美的学科。人们追求的是没有疑问的确定知识,但实际上却面对着许多难以认知的对象和研究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具有社会属性和系统属性,观念因素不能直接观察,系统效应的复杂影响难以解释,因此信息的不完备和推论的不确定性不能避免。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人们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解释变量间关系的确定性,也需要解释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不确定性。解释确定性,是在既定前提下指明一定事态的属性与可能的变化范围,告诉人们应当关注的方向与因素。解释不确定性,是要说明系统中不可以观察因素的复杂构成,并推论其互动关系和对系统效应的贡献。在这两项不可以分割开的研究中,人们需要积累有关各种单一机制的确定性知识,同时也需要不断加深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确定的知识都是特定前提的推论结果,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部。有关不确定性的知识,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决策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和需要的,因为国际大环境就是不确定的,人们需要有不断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确定性;不确定性;外在现象与内在观念;系统效应;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李少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邮编200020)
【Abstract】The stud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not a perfect discipline. What scholarsseek is certain knowledge, but they have to deal with both manyfac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and with academicuncertainties. Because fa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societal and systemic properties, conceptual factors cannot bedirectly observed and the complex impacts of the systemic effectsare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refor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inference uncertainties cannot be avoided. In this regard, studies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ed to explain both the certainties of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ables and the uncertainties due tothe conceptual factors and the systemic complexities. The certaintiescan be explained by specifying the properties of specificevents and the range of possible changes within the given premisesand by indicating those directions and factors that require closeattention. Explaining the uncertainties requires revealing thecomplex systemic structure due to the non-observable factors anddeducing their interaction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systemiceffects. In studies in which the two cannot be separated, specificknowledge about every single mechanism as well as a deepenedunderstanding of the uncertainties are required. With respect to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knowledge can beinferred from the results of specific premises that cannot explaineveryth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ledge about suchuncertainties is necessary for both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uncertain and a deeperunderstanding is required.
【Key Words】certainty,uncertainty, overt objects and covert concepts, system effects,realism, rationalism, cognitivism, constructivism.
【Author】 Li Shaojun, Guest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nghai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不论是针对已发生之事实的描述、解释,还是针对未发生之事实的预测,人们所追求都是确定性,即希望形成完备的知识,没有疑问。然而,现实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尽管已有的研究卷帙浩繁,形成了许多得到相当程度认可的理论体系,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不但对于国际互动的宏观趋势有迥异的解释,而且对于具体事件的阐释与预测也往往存在争论。以冷战的结束这一标志时代转变的典型事件为例,国关学界事先未能提出准确预测受到了批评,而事后对原因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1]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状况?造成人们认知不确定性的根源是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对国际关系研究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本文认为,国际关系学并不是完美的知识体系,只有搞清楚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才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研究与知识体系有适宜的认识。
一 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概念与国际关系研究
确定性(certainty),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界定,是指一种状态,即没有疑问。确定性所对应的信息与知识,是没有错误的和完备的。相反,不确定性(uncertainty)则是指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2]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这两个概念指涉的都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说明的是研究者得到的信息和知识的状态。对研究者来说,确定的知识对应的是可以认知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对象,研究者只要有适宜途径和相应的处理能力,就能在观察中有所发现,并且通过论证得出确定的结论。如果与此情况相反,研究对象或其某些方面对研究者来说不可知,那就会导致认知和所形成知识的不确定。
对于不确定性,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是有一个认识演进过程的。英国物理学家戴维·匹特(F. DavidPeat)2002年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20世纪的科学与观念的故事》一书中,详尽地阐释了社会各界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的挑战。该书指出,在19世纪,人们是确信科学研究的确定性的,因为牛顿物理学表明,宇宙万物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钟表结构,在按照严格的规律运动,因此其进程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在1900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开尔文勋爵(LordKelvin)断言,至少原则上可以知道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然而,在科学的种子生根之前,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就打破了这种机械的宇宙论,证明我们充其量只能形成不完备的知识,而且可能永远如此。例如,对于宇宙中的黑洞,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任何信息。该书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界常见的混沌现象,表明人类在认识、预测和控制其周围世界的时候是存在先天的局限性的。虽然这样的世界观未必会被接受,但是不确定性对科学、艺术、文学、哲学和社会关系无疑都有深刻影响。在21世纪,人们已开始谦恭地接受不确定性。[3]
自然科学研究面对不确定性,表明自然科学家面对着许多难以观察、解释甚至是不可知的研究对象。对这些对象,也许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人们的认知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但也许人们在研究中会发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尽管存在这样的挑战,自然科学领域毕竟已有了巨量的确定性知识的积累,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形成了得到公认的系统性认识。这种情形与本文拟讨论的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是在发现众多规律、定理的基础上仍然面对着不确定性,那么国际关系研究则自学科正式诞生起,就没有形成过得到一致公认的规律性的东西。学界所形成的系统性理论几乎都是有争论的。
在1919年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出现之前,许多重要学者,诸如修昔底德、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等,都提出过影响深远的思想,但他们的见解还不能说对“国际关系”提出了确定性的解释。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后,理想主义曾经占居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和实施的集体安全制度就是这一思想的现实体现。然而,这一主义也面对着种种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表明这一主义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是有疑问的。卡尔在《20年危机》中就批评了这一思潮。[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思想取得了支配地位,但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也在继续。这两者一直存在争论的状况表明,无论对世界政治的属性作冲突还是合作的解释,都存在不确定性。除了这一场争论之外,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80年代出现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90年代出现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进入21世纪后出现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之争等,都没有争论出确定的结果。这些争论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关系学科中具有支柱意义的知识都存在不确定性,不但重要的理论体系在解释现实时有不确定性,在研究途径上也始终存在着范式之争。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国关学界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了。在90年代,很多学者曾密集地关注过这个问题。[5]进入21世纪后,仍不时有学者讨论这一问题。[6]关注相关的文献可以看到,虽然很多学者都认可这样的观点,即国际政治是发生于一个普遍的不确定的环境里,[7]但对于不确定性的概念、表现、原因等却有着不同看法。在这里,引用饭田敬辅(KeisukeIida)和拉斯本(Brian C. Rathbun)的综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相关研究的概况。
饭田敬辅对学界有关“不确定性”的讨论,进行了“战略的不确定性”(strategicuncertainty)和“分析的不确定性”(analyticuncertainty)的区分。前一个概念涉及的是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即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是因为了解自己的意图、利益和权力,但对互动的他方则不了解。这种情形通常被界定为信息的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并且主要是用于描述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领域的互动,例如国家实施威慑政策或是进行军控谈判,就会受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不过,正如饭田敬辅所指出的,信息不对称并非不确定性的唯一形式,在国际关系中还有其他的不确定性,比如随机型不确定性(stochasticuncertainty),即某些事件的发生具有或然性,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另外,不确定性也并非只发生于高政治领域,在其他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8]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研究是较多的,例如现实主义对国家意图的不确定,以及进行博弈研究对玩家意图的不确定。对于这一类研究,饭田敬辅认为主要涉及的是行为体的特性,即私人特征(privateattributes)。除了这种研究视角之外,不确定性还涉及到公域(publicdomain),即体系的特征。在这方面,饭田敬辅特别论述了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得到的有关世界经济体系运作的信息非常不完善,因此它们不能达成一致,即便它们在真实世界中是完全和谐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形称为“模型的不确定性”(modeluncertainty),即不同国家的决策者相信不同的世界模型,例如,可能相信世界经济的凯恩斯模式,也可能相信货币主义的世界经济观。饭田敬辅是用“分析的不确定性”替代“模型的不确定性”。这样,他就把相关的研究分成了两类:对战略不确定性的研究关注的是行为体的互动,而对分析的不确定性的研究则关注的是系统的整体。
对于这两类不确定性,饭田敬辅作了这样的对比:第一,按照战略的不确定性,每一个行为体都知道自己的真实特性,但不知道其他行为体的真实特性;按照分析的不确定性,每一个行为体都知已知彼,但不知道他们与之打交道的经济体系的真实属性。第二,按照战略的不确定性,在其他行为体行为既定的情况下,每一个行为体都知道每一行为的收益;按照分析的不确定性,由于经济结果是来自于行动的结合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所有行为体的行为都是已知的,每一个行为体对自己的收益仍然是不确定的。第三,按照战略的不确定性,行为体传递信号(signaling)要么是表明自己的真实特性,要么是假装自己具有并不具有的特性;按照分析的不确定性,行为体传递信号要么是试图使其他行为体确信自己的世界观正确,要么是试图从其他行为体所坚持的“错误”世界观中获益。第四,按照战略的不确定性,“学习”(learning)仅仅产生于对其他行为体行为的观察和推论;按照分析的不确定性,学习同时也产生于对政策经济结果的观察。因此,传递信号也可以采取促进或阻碍后一进程的方式。[9]
在国关学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除了有视角与层次的不同之外,还存在不同范式的区别。拉斯本在综述相关的研究时就辨析了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这两对四个学派的不同的不确定性观念。[10]在这四个学派中,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大体上是从客观观察的角度看问题,而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则是从主观认知的角度看问题。
按照拉斯本的说法,在战略互动层面,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都认为不确定性的产生是因为国家对于与之互动的那些行为体的意图、利益和权力缺乏信息。这一点与前述饭田敬辅所综述的情况相同,但拉斯本强调了两种主义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同反应。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现在和未来的意图都不可知,其相对军事能力难以评估,这两者有时会迅速变化,因此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和危险的。现实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对应态度是“恐惧”。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不能肯定其他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率先动手。即使他国确实仁慈,也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意图是百分之百不能预测的。[11]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米尔斯海默认为忧虑其生存的国家必须对其竞争对手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12]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意图的不确定性是造成战争的原因之一,它所导致的是结构性的不确定性。[13]
拉斯本的综述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作为一对范畴,实际上现实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也是一种理性主义,不过理性主义还包括其他学派。拉斯本在这里用理性主义是指源于微观经济理论的一种思想,即政治行为体在结构的限制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有关意图的信息)会谋求其功利的最大化。国家对于他者是否会坚持其谈判目标并且守信是不确定的。在协作博弈中,国家不相信他方不会以假象进行欺骗,而欺骗则会产生受骗结局。在这里,尽管理性主义如同现实主义一样关注意图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战略困境,但对国际合作更加乐观。理性主义不大相信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最终裁决者,认为国家不会在信息不完全的境况下预先得出有关他者意图的悲观结论。拉斯本认为,理性主义是用无知(ignorance)来对应不确定性,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黑暗之中。如果可靠的信息表明他国有意愿,并且存在共同获益的可能,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实施合作。[14]用基欧汉的说法就是,如果国家不是一贯地担心他国,就会对信息比较敏感,并且愿意收集之。这有助于发展对那些与之有战略关系的国家的意图的信任。理性主义对于意图的不确定性的反应并不是像现实主义那样主张积累权力,而是积极地评估意图。[15]
另外一对范式即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虽然都是从主观认知的角度看待不确定性问题,但它们对于主观性问题(subjectivityproblem)的确切来源有分歧。对认知主义来说,客观真实在很高程度上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与解释的。不确定性乃是决策者接收信号不清楚的结果。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信息是含糊的,因此在认知局限下信息只能被近似和部分地理解。[16]国家和政治家依赖若干认知捷径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常常会导致错误知觉和过失。与认知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则认为,主观性问题并非复杂性的结果,而是因为信息的意义取决于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由于行为体需要基于认同与规范来确定如何应对客体和他者的行动,因此在社会语境下对信息提出解释,形成自我构想的有关适当性的观念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规范与认同具有可塑性,会依行动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国际关系是不确定的。[17]
对以上观点进行总结,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不确定观念到底不确定的是什么。现实主义不确定的是对手的意图,由此演绎出对其利益与权力变化的不确定,并最终基于恐惧感推论出权力政治的结论。理性主义不确定的也是行为体的意图,但基于“无知”并不做悲观的预设,而是认为注重收集信息,就可能谋求共同获益的理性结果。认知主义不确定的是客观信息,认为人的认知局限有可能导致错误知觉。建构主义不确定的是以规范与认同为体现的行为体观念的变化。基于不同的认知视角,学界的相关阐释包括对客体(互动对手、认知对象)的不确定,也包括对主体(认知局限、认同)的不确定;包括对个体(其他国家)的不确定,也包括整体(体系结构、博弈结局)的不确定。这些多角度的阐述表明,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多方面的事实人们是存在认知疑惑的。对于这些认知疑惑产生的原因,虽然已有的研究论及了观念因素和体系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但并没有从国际关系事实的属性的角度提出综合性论证。本文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对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的不可观察性做出解释,才能够说明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不确定性的根源。
二 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的根源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获取确定的信息是离不开对事实的观察的。在研究中形成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如果是产生于抽象思维,那也需要经由经验观察加以确定。从这个角度讲,国际关系研究要形成确定的知识,其对象的方方面面都要可以观察。然而,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和系统属性,却导致人们不得不面对许多不能认知的方面。
国际关系事实具有社会属性,是指其中内含人的意图,有特定的意义。不但行为体、行为体的行为及结果有这样的意义,一些看似纯物质性的人造物,诸如核武器、航母、反导系统,也有意义。这些意义都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事实的意义是不能不解释的。在很多时候,如果不能对行为体的意图做出适宜的判断,那所做研究就没有价值。对于不能直接观察的行为体的心理活动,人们的研究通常是通过可以观察的因素进行。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观察的行为与反应,即外显行为(overtbehavior),另一类是不可以观察的内隐行为(covertbehavior),比如思考和记忆等内部心理活动。由于内隐行为不能直接观察,因此需要通过可以直接观察的外显行为来推论。就国际关系事实而言,也包括这两个层面,外显行为是指行为体的一切可以观察的行为,而内隐行为则是指行为体的内在心理活动。对于行为体来说,其内在的心理活动是一定会通过外显行为表现出来的。例如,政府的战略意图会通过对外政策行为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民意,也会通过各种媒体、舆论表现出来。由于这两者存在对应关系,因此研究者就可以通过事实的外在表现推论其内在观念。事实上,研究者也只能这样做研究。人们以问卷的方式进行民调,对政府发布的各种报告进行解读,对各种国际互动进行意图性分析,都是对观念的外在表现进行研究。在很多时候,研究者基于对经验事实的历史观察是可以对行为体的政策意图进行判断的,虽然这种判断可能因行为体的意图发生重大变化而失误,但变化通常也是有外在现象可寻的。
当然,通过观察外在现象解读行为体内在观念的做法,其结果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把内在意图完全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行为体的可以观察的言行,充其量只能部分地反映其真实意图,其中是可能包含假象的。在国际互动中,行为体把底线完全表露出来是非常危险的。由于研究者对行为体内在观念的解读不能进行检验,因此这种解读适宜不适宜是不确定的。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他者的观念完全不可知也是一种解读。也许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体的持续互动会导致一个观念不断沟通和求真的过程,并且有可能在建构主义所阐释的建构共有知识的过程中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但无论如何对观念因素的认知都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对于观念性因素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用有关“战略文化”的研究加以说明。所谓战略文化(strategicculture),是指一个国家实施战略的根本理念。这种理念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对其利益与目标、朋友与敌人以及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习惯与传统的总和。这种传统是根植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之中,对其如何参与国际互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大致的战略偏好,会使一个国家有某些比较稳定的战略模式。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战略文化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重要因素,因为不同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往往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要从社会心理的层面对这种文化传统进行解释,可以观察的东西就是历史文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献千千万万,选择哪些文献进行解读适宜,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判断。[18]由于这种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进行检验,因此即使人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识,其中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是始终存在的。
就系统属性而言,在这里是指国际关系事实的构成乃是一个包含众多因素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行为体之间、进程之间、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与互动。任何事态都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也不会只产生单一结果。为了实现利益,每个行为体都会基于自己的目标与战略判断采取行动。每一方的行动,都会构成他方行动的依据。由于行为体相互间很难预知对方的意图,而每一方的行动都会影响他方,并且会改变系统的整体环境,因此互动的每一方可能都面对着不确定的互动对手和互动环境。在很多情况下,系统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直接效应,还可能有间接效应、延迟效应,并且有非故意的效应。[19]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这种复杂效应的构成与机制,即使相关因素具有客观属性,也是难以观察甚至是不能观察的。例如,中美关系作为一个系统,所涉及的互动因素就很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超过百项,就表明双方关系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系统。[20]就这个系统来讲,发挥影响的因素一共包括哪些,每一种因素在总体影响中有多大贡献,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更复杂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联系以合力的形式发挥作用。这种合力具有单个因素所不具有的属性。就像音乐中的和弦一样,当两个以上的键被同时按下时,所发出的是不同于任何单音的合声。[21]体系中“合力”的形成机制,在多数情况下是难以认知与解释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用综合国力的研究为例。人们进行综合国力研究,目的是要表明国家的力量并不是单一要素,而是多要素的组合。然而,由于“综合国力”的概念不能观察,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得到验证的答案。人们设计衡量综合国力的方法,包括构成要素与计算方式的确定,都是基于自己的偏好与主观判断。这样的计算,即使所用数据是客观的与准确的,也不能证明计算结果就是综合国力。在这里,最根本的认知障碍是国家综合力量的构成不能观察,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合力的形成几乎是不能认知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是可能得出各种不确定的评估的。实际上,只要根据主观意图变动要素的选择与权重,研究者就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结果。
以上所讨论的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和系统属性,可以说构成了影响人们认知的客观因素。实际上,对认知造成影响的还有人们的主观因素。由于研究者认识世界是一种主观活动,涉及到对信息的选择,以及基于背景知识对理论视角的选择,因此在特定偏好的作用下,是有可能对相同事实做出不同解释的。特别是研究对象存在不可知要素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难避免了。在很多时候,研究者对世界的观察还会受到认同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有可能左右人们的判断与认知的。尽管从规范上讲人们进行学术研究应当尽可能地做到客观中立,但研究者做为有主观意识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排除这些心理活动的影响的。
三 不确定性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国际关系事实具有社会属性与系统属性,决定国际关系研究不能避免不确定性。关注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研究现状,就可以了解这种影响。不论是解释国际体系的属性与趋势的大理论研究,还是解释现实问题的一般理论研究,只要前提条件中含有不确定的因素,其推论就可能有疑问。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几种主要的体系理论的演绎做简要讨论。
现实主义作为体系理论是一个理论群。它内部的不同分支有不同的演绎逻辑。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其推论的前提是“无政府”和“人性恶(自利)”。“无政府”表明不存在高居于国家之上的管理者,国家要生存就只能靠“自助”。人性的自利表明国家必然相互冲突。在冲突的背景下国家要谋求利益就必须追求权力,因此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22]古典现实主义的这个推论要站得住脚,作为前提的国际体系就必须是不存在任何管理者的状态,而国家则必须是纯粹的自利者,完全不考虑他者和共同的国际利益。然而,考虑到系统因素与观念因素的复杂性,就会发现这样的推论有不确定性:在国际体系中虽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国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管制国家行为的作用。由于国家在体系中必须与他者共存,在互动中会发现共同需求,也会考虑共同利益,因此并不是纯粹的自利者。从这个角度看,讲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国际政治还包括其他的互动形态,权力互动只是其中之一。只有在国际制度几乎不起作用,行为体的行为都是以自助和自利为原则的时候,国际政治才会表现为权力政治。
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改变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推论逻辑,不再考虑人性,而是基于国际结构和忽略掉个体属性的单元这两个前提要素进行推论,认为结构会决定单元的行为,即国家为了生存与安全,会适度谋求权力,因而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新现实主义把国家视为只存在权力差别的谋求安全的理性行为体,并且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纯客观的构成与进程,目的是通过科学推论发现客观规律。[23]然而,现实的国际体系与单元都是存在复杂构成的,国家在体系中不可能只受到单一影响,它们有不同的意图就可能有不同的“理性模式”。在系统效应的作用下,体系的均势能不能形成,在什么时候能形成,都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一点,沃尔兹也有过解释。他指出,结构制约行为和结果,这种解释是不确定的,因为单元层次和结构层次的原因可能同时起作用,难以确定哪个更强。这是体系理论的局限所在。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可以确定结果的范围并提示总体趋势,可以指引我们注意那一类行为和预期范围的结果,但不能奢望预测具体的结果。[24]
新古典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演绎都增加了前提条件。新古典现实主义增加了政府对决策的影响,认为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经由政府实现的。这就考虑了国家“理性行为”的不确定性。[25]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环境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考虑有不同,对力量的掌控有不同,因此对体系压力的反应也会有不同。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则增加了国家对安全的判断(安全感)。进攻现实主义对理性行为的推论是以“恐惧”为前提,即由于对他者的意图完全不可知,因此只能做最坏打算,以“进攻”为政策底线,而大国只有争得霸权才有安全。这样的推论结果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26]防御现实主义则认为安全并不稀缺,国家的防御行为可以平衡威胁实现安全。[27]就后两个分支而言,带有主观属性的意图因素即“安全感”都构成了演绎的前提条件。由于国家的安全感存在复杂的情形,不能观察和检验,而且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作这样的推论也是有不确定性的。
以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承认“无政府”这个大前提,但强调的是体系中不同行为体或事件的相互影响。该理论的推论出发点是“复合相互依赖”,认为这种关系会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和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高政治问题地位下降。由于行为体的相互依赖会导致共同利益的产生,因此会促进合作,并且会推动规范的建立和国际制度的发展。[28]与现实主义相对照,自由制度主义对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做了更具积极性的演绎,即会寻求合作而不是冲突。这一推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全球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国际互动中的相互依赖也是有复杂情形的,例如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情形。现实主义所看到的权力对抗,作为互动乃是消极的相互依赖,就像冷战时的美苏、当今的以巴一样。只有积极的相互依赖,诸如全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才更有可能推动合作与制度化。从这个意义来讲,相互依赖作为理论前提是有不确定性的。只有限定前提,即行为体间存在积极的相互依赖并且在互动结构中居主导地位,才能够得出合作的结论。
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思路不同,建构主义的演绎是以“社会事实”作为逻辑起点,认为决定国际关系属性的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行为体的观念。行为体是相互为敌、为友还是为伴,会建构不同的共有知识(文化)的结构。这种共有知识反过来又能够以社会化的方式建构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与利益。[29]在这里,由于“共有观念”是不可以观察和检验的事实,因此判断行为体具有何种观念认同,其互动构成了何种文化,这种文化对行为体发生了何种社会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认知的,人们的解读都存在不确定性。
除了大理论研究,国际关系学科中以假设检验和文本诠释为形式的理论问题研究,也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对于这些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学科方法的分析进行讨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案例法是运用较多的方法。由于案例都是基于特定目的选取的,不具有代表总体的客观属性,因此用以证实全称命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通常,人们可以进行单一案例研究,做出适宜解释;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新的变量关系,提出新的假设;亦可以用案例作为反例,证伪一个命题。不过,鉴于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用案例证伪可能也具有不确定性:在存在系统效应的背景下,由于事实原本就存在复杂多样的变量关系,并非只存在单一的因果或相关关系,因此即使发现反例,通常也不能简单地证明原命题是错误的。
与案例法相异,定量法是基于大样本事实进行研究,通常被认为可用以检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选择这种方法,前提条件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被统计的事实必须在整体上具有同质性。然而,受限于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能够获取大样本的研究对象非常有限。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研究者的通常做法是只关注少数变量而忽略其他要素,并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然而,事实的差异是不可能避免的: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不能重复,国际环境在不断变化,事实的发生总是在不同的环境里,每个行为体都有特定的客观属性和主观诉求,因此再相近的个案也存在差别。即使事实具有某个相同属性,但同时可能具有更多的不同属性。事实的这种复杂性特点,一方面导致变量的控制难以进行,因为被忽略的因素可能对不同的进程有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导致研究者难以通过观察确定变量间的互动机制,因为国际关系的进程很可能是复杂的原因导致复杂的结果。如果真实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且不同的进程有不同的原因合成,那么即使发现某个因素出现的概率高,也不能确定该因素就是导致结果的主要原因。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数据处理得出的以概率为体现的相关性,本身就是有不确定性的。更重要的是,变量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研究者可能难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相关关系。实际上,进行定量研究最重要的不是数据处理,而是对变量间关系的解释。[30]不能对变量关系作出解释,进行数学计算就没有道理可讲。再者,由于在定量研究中人们完全忽略掉行为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把变量关系视为完全的客观进程进行计算,因此事实的社会属性是可能带来意外的不确定性的:人的观念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一旦行为体的重要观念发生变化,可以观察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改变,依据客观数据作出的结论也就没有意义了。
用形式方法进行研究,途径是把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实简化为便于演绎的数学模型。这样的简化可以使问题一目了然,使演绎逻辑严谨,但因为忽略掉了复杂系统的大部分要素,因此其推论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以最简单的博弈研究为例,研究者排除了道德、情感、责任等社会及心理因素,把行为体简化为对规则、得失有相同认知且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玩家,把复杂的外交选项简化为两种选择,由此来推论各方的收益,判断最终的结局。由于被忽略的多元的影响因素和政策选择都是可能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的互动结果是有更复杂的情形的,简化的演绎只能代表多种进程之一,而且是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从这个角度看,形式方法尽管演绎具有严谨性,但对真实互动的解释却是不确定的。
用诠释方法进行研究,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事实,即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背后的意义。由于意义不能直接观察得知,必须通过可以观察的文本进行解读,因此这种研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对相同的文本,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做出不同的诠释。即使诠释者通过互动达成了一致,也不能确定所做解释就是最适宜的,因为这种解释不能被检验。
以上所评述的四种方法,用于进行国际关系研究都不能避免不确定性。在这里,原因不在于方法不完善,而在于事实本身有不可以观察和认知的内容。虽然人们在研究中适宜地运用方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但不可能完全克服认知局限并消除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是不能避免不确定性的。人们必须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知识有适宜的看法。
结论:适宜地看待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知识
国际关系事实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系统属性,决定国际关系研究既面对着可以观察的客观因素,也面对着不可以观察和难以认知的观念因素与复杂的系统因素。由于研究者针对可以观察的因素能够得到相对确定的认知,针对不可以观察的因素的认知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从整体上讲既具有确定性,亦具有不确定性。
国际关系研究的确定性的一面,是指研究者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可以认知变量间关系,解释特定机制的发生和作用,并且可以预测事态演进的大致方向。对国关研究者来说,要对复杂世界的运作做出解释,就必须知道要解释特定现象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这种针对单一或少数因素的研究,其实质是选取国际关系的复杂系统中的特定机制进行论证。从限定的前提条件出发,研究者不论是在观察大样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归纳研究,还是通过抽象思维进行理论演绎,其宗旨都是要提出有关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的解释。就这样的研究而言,只有通过对变量的控制排除其他因素,集中观察某一对关系,才有可能对相关机制有确定的认知。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是这样做的。[31]
然而,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这种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的解释,其实只涉及国际关系的系统构成的一部分。由于在实际的互动中各种因素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任何事态几乎都是复杂原因的结果,因此用单一机制推测事态的发展是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就是国际关系的实际演进往往存在多种可能。为了更好地对国际关系作出解释,我们在对国际互动单一机制的确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同时进行不确定性的研究。
进行不确定性研究,就是通过可以观察的事实,尽可能地推论不可以观察的因素的作用机理。这种研究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但可以增进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并且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例如,研究者可以推断存在哪些不可以观察的影响因素,分析它们的复杂系统的构成,解释它们的互动关系和作用,并且说明它们对系统效应有怎样的贡献。做这样的研究,重点不在于预测,而在于解释各因素的作用机理。由于国际关系事态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其演进有不确定性,因此没有人能确定地预测未来。对于研究者来说,在解释不确定影响的基础上能够列出国际关系演进的多种可能变化就很了不起了。
鉴于国际关系研究有确定的一面,也有不确定的一面,我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也应有适宜的看法。在这里,知识的确定性是指国际关系理论在既定前提下的推论能够指明一定的国际事态的属性与可能的变化范围,告诉人们应当关注的方向与因素。这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更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解释。不过,由于这样的知识都是特定前提的推论结果,因此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部。如果把这种研究的结论视为普遍性理论,那就带有不确定性了。由于国际关系系统具有结构的复杂性与观念的不可认知性,因此任何既定理论提出的解释,人们都可能找到反例。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理论争论其实都是由而来:明明只能解释某一类国际现象,但却以普遍性理论自居,并且批驳解释其他现象的理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些理论来说,只有在符合其前提条件的时候,其结论才是确定的,一旦超出这个逻辑范围,其解释就可能是有疑问的。
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要增进研究的确定性,就需要深刻认识不确定性的影响。为此,学界需要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系统因素和观念因素的研究。如果说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端,那么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则可以构成国际关系研究的另一端。这两个方向的解释都是必要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解释单一性机制的确定性,除了说明其机理之外,还需要说明其可能的复杂变化。反过来说,人们解释事实的复杂变化,也需要以确定的单一机制解释为基础。在这样的解释中,人们可以积累对各种单一机制的确定性认知,同时也可以不断加深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对不确定性的认知的深入,也是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推进。
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不确定性,对学科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由于现实中的每一个行为体都需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政策判断,因此各种“不完美的”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需要与必要的。对研究者说,不确定性代表着疑问,而存在疑问恰恰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有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这一点也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1] 可参阅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58.
[2] 可参阅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 Merriam-Webster Inc., 1991,pp.223, 1284。
[3] 可参阅F. David Peat, From Certainty toUncertainty: The Story of Science and Idea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Joseph Henry Press,2002,特别是前言部分,见pp.ix-xiv。本文的相关陈述参阅了出版社对该书的介绍。
[4][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5]例如,可参阅以下文献:Thomas R. Palfrey and HowardRosenthal, “Voter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ic Uncertainty,”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1 (Mar. 1985), pp. 62-78; Barry Nalebuff, “Brinkmanship and NuclearDeterrence: The Neutrality of Escal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and Peace Science, Vol. 9, No. 2 (1986), pp.19-30; RobertPowell, “Nuclear Brinkmanship with Two-Sided Incomplete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 1 (Mar. 1988), pp. 155-178; James D.Morrow, “Capabilities,Uncertainty, and Resolve: A Limited Information Model of CrisisBargai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3, No.4 (Nov. 1989), pp.941-972; D. Marc Kilgour and Frank C.Zagare, “Credibility, Uncertainty and Deterr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2(May 1991), pp.305-334; Keisuke Iida, “When and How Do DomesticConstraints Matter? Two-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 Journal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7, No. 3 (Sept. 1993), pp.403-426; Keisuke Iida, “Analytic Uncertainty and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7, No. 4 (Dec. 1993), pp.431-457。
[6] 可参阅:David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Studies, Vol. 12, No. 1 (Autumn 2002), pp.1-40; Brian C.Rathbun, “Uncertain about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Meanings of a Crucial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3 (Sept 2007),pp. 533-557;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Knowing the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Jan.-Mar. 2011),pp.2-35;田野:《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性的理论探讨》,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马骏:《不确定性及其后果——国际制度的认知基础》,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1期;牛长振:《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等。
[7]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Jan.-Mar. 2011),p.5.
[8] Keisuke Iida, “Analytic Uncertainty and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Vol. 37, No. 4 (Dec. 1993), pp. 432-434.
[9] Keisuke Iida, “Analytic Uncertainty and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Vol. 37, No. 4 (Dec. 1993), pp. 434-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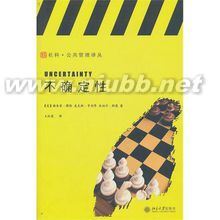
[10]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3 (Sept. 2007), pp.533-557.
[1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10.
[1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3] 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L. Schweller,“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 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1 (Jan.-Mar. 2011),p.8.
[14]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4 (Dec. 2007), p. 541-542.
[15] Robert 0.Keohane, “Institutionalist Theory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p.276.
[16] 可参阅James M. Goldgeier and Philip E. Tetlock,“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67-92。
[17] Brian C. Rathbun, “Uncertain about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 Crucial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3 (Sept. 2007), pp. 534-535,549.
[18]例如可参阅江忆恩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他以中国的明代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中国古代的兵书并分析明代的对外关系,得出了“文化现实主义”的结论,即中国古代王朝在对外关系中是倾向于使用武力的,而且这种战略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仍有影响。见Alastair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5.
[19]关于系统效应,可参阅[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33-80页。就现实的事例而言,伊斯兰国(IS)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非故意的结果。
[20]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共116项。见新华社相关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2/c_1111579285.htm。
[21] Reuben Ablowitz, “The Theory of Emerg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6, No.1 (Jan. 1939), pp. 2-3.转引自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10页。
[22]对古典现实主义推论的概括,参考了[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8页。
[23]对新现实主义推论的概括,可参阅[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4,154-156,168-170页。
[24]参见肯尼思·沃尔兹著,张睿壮、刘丰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2页。
[25]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可参阅Gideon Rose, "Neoclassical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 No.1 (Oct. 1998), pp.144-172。
[26] 可参阅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5-66页。
[27] 关于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讨论,可参阅Glenn H. Snyder,“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2002), pp. 149-173。
[28]对自由制度主义的概括,可参阅[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9页。
[29]关于建构主义,可参阅[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8页。
[30]关于相关性与变量关系的解释,可参阅一个有趣的事例:2012年一位学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消费的巧克力越多,该国人均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便越多。不过,该学者没有办法说明这两者的关系,只能解释为巧克力可能有助于促进人的认知功能。该学者承认,两者的关系也可能是反向的,即获得诺奖多的国家消费巧克力多。研究者没有获奖者个人消费的数据,只有国家平均数。他认为也有可能是一个未知原因促进了这两者。这个事例说明了解释对于数据计算的重要性。参阅FranzH. Messerli, “Chocolate Consump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NobelLaure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67, No.16 (Oct. 18, 2002), http://www.nejm.org/toc/nejm/367/16/。
[31]可参阅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Leaving Theory Behind: 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Vol.19, No.3 (Sept.2013), p.431。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