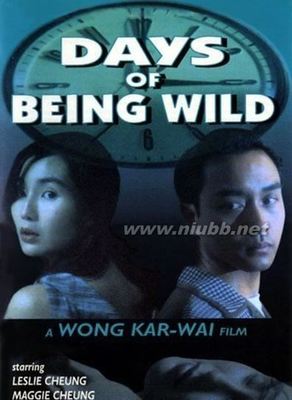关于电影《春光乍泄》:(转自网络)
阿根廷,布伊洛斯艾利斯。探戈吧门外,黎耀辉(梁朝伟饰)与老情人何宝荣(张国荣饰)重逢。两人度过一段共同的日子,又告分离,没能实现结伴同游大瀑布的计划。另一位流落阿根廷的台湾青年(张震饰)来到美洲最南端的“世界尽头”,许愿将“不开心”留在那里。黎耀辉独自游览了瀑布之后经台北返回香港。
那支歌叫做“CucurrucucuPaloma”,高低盘旋,像歌中吟唱的鸽子,忧伤地俯视着蓝色的瀑布。沦落天涯,都为这无尽的蓝。两个浪子曾经见过它的影像----在灯罩上,波涛倾泻,镜花水月般,美得不可思议。“到过瀑布就回香港,”他们出发了,为了回家而远行。他们迷失了,不知道自己去了什么地方,只觉得在一起的日子过得好闷。梁朝伟无法抵挡张国荣那“极具杀伤力”的祈使句:“让我们从头开始。”再度投降。拥有,使黎耀辉感到满足。黎耀辉最快乐的时候是何宝荣卧床不起的日子。他扣留了张及其护照——从身体到身份。不幸的是,相濡以沫的生活并非何宝荣的梦想。在居所的天台上,黎耀辉埋头修整房顶,何宝荣却仰望蓝天,似乎振翅欲飞。暖巢可以变成牢笼,情爱何尝不是束缚。
在王家卫系列电影里《春光乍泄》显得像《阿飞正传》的续篇。《阿飞正传》中旭仔(张国荣饰)自命为无脚鸟”,因为没有脚,必须不停地飞,直到力竭而死。《春光乍泄》的三个男人好似“无脚鸟”投胎转世的堕落天使,张震的台词可以概括这类自我放逐者的心态:“没有去过的地方才好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迷离朦胧的蓝色充满了“无脚鸟”的梦幻世界,笼罩着巨大的瀑布。这是浪漫主义者的颜色,象征着与生俱来的疏离感、青春的忧伤、对无限的渴望以及注定失落的命运。浪漫主义文学中常见的“局外人”形像,在王家卫电影里被赋予特异的感知能力。
梁朝伟在《东邪西毒》里边是游离于东邪西毒北丐群侠之外的角色——盲侠;具有台湾/日本背景的金城武在《堕落天使》里是哑子;《春光乍泄》的台湾客张震患过眼疾,听觉异常敏锐。临别的时候,梁朝伟要张震闭上两眼,说他活像盲侠。只有读过《东邪西毒》的观者才能悟出,盲侠就是梁朝伟本人的前生。《春光乍泄》对此作了大面积铺张,既刻画同性之爱(张国荣与梁朝伟),也刻画友谊(梁朝伟与张震)。同性爱的特点在这里并未得到突出表现,黎耀辉与何宝荣的同居生活不乏赌气、吃醋的花絮;同一舞台上,房东夫妻的家庭生活充斥着没完没了的争吵。这是公平的表现。张震如愿以偿来到世界尽头的最后一座灯塔下面,在那里埋葬“不开心”。“不开心”物化为一段录音——过去时的思想/语言的磁记录。这令人想到王家卫电影关注的时间与记忆的问题:录音是怀念的手段,把录音留在“世界尽头”的举动却是彻底遗忘。为了忘却的纪念。王家卫习惯用时空错位来强调情感失落,《春光乍泄》亦不例外。黎耀辉独自面对瀑布的时候,何宝荣住进了黎耀辉寄居过的屋子,占据了他们在过去时共同拥有的空间,此时他面对着的只能是灯罩上的瀑布影像。瀑布之于何宝荣成了永远不可及的镜中花水中月,之于黎耀辉却是业已完成的目标:看过了,该回家了。
《春光乍泄》绝对是王家卫技术上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所有玩了技术的地方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些招牌的摇镜头、慢镜第一次跟电影本身贴的那么紧,完全是跟着人物的情绪去展示王家卫自己的电影语言。每一个镜头都似有所指,每一个镜头都似乎在说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那些光影里的温暖和黯然可以一路穿过面前的映画,直入你的心里。
《春光乍泄》一开始长达数分钟的同性镜头,让很多人感到尴尬和不适应。经过艰难的几分钟之后,才开始了王家卫风格,人物一般的寂寞,情感还是那样隔离,相互拒绝又相互吸引,风景一样的美丽,摄影一样的飘逸凌乱。《春光乍泄》是人之间的事,他们的关系是寻求欢悦。当他们中的某个人厌烦了这种关系,就要离开。剩下的人难免寂寞。可是寂寞就要回归,回到香港却难免还是有一种怅然若失、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绪。
其实同志题材绝不是本片的重点,虽然未必如王家卫本人所言,只要不看前5分钟,都不会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许这只是对敏感题材的一种介入姿态;也许只是王家卫赶在九七之前遂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许这只是为了非异性恋者那份更为难言的孤独吧。内容上仍是让人不敢轻易触碰的拒绝与被拒绝,仍是边缘生活的落寞滋味,仍是那些易碎的敏感和细密疼痛的挣扎。影片中所流露出的,还是那种无根的寂寞,那种渴望、期待与害怕面对的挣扎。
在《春光乍泄》中,王家卫彻底显露出九七年回归前香港人的困境:香港人如同何、黎二人一样,他们发现了他们唯一的身份,就是没有身份,什么港英护照根本不肖一提。王家卫在一次访问中亦谈到《春光乍泄》的一些主题构思,“我自己也如同剧中的黎耀辉和何宝荣一对恋人,厌倦不断地被问及到九七年七月一日后香港将变成如何?想离开香港,来到世界另一头的阿根廷逃避现实,却发现越想逃避,现实越发如影随形的跟着自己,无论到哪儿,香港都存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