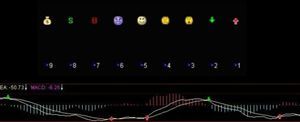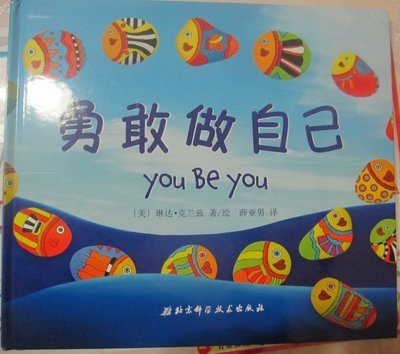“就这么定了,回公司我再找你。”我下车别了谢伟,径直走进大厅。
谢伟是我的老同学,三年前我俩从化工系毕业,谢伟由于成绩优秀被送往加拿大继续攻读MBA,我则不安分守己,在家爬了三年格子,可惜最后连李渔和李昱都混为一淆。这种境况直到三个月前他从那边融资回来叫我当CFO。谢伟曾云自己具有谢灵运的遗风,我玩笑他说称遗孀更贴切些。但现在,我该叫谢总抑或谢CEO。
时过境迁了。
人当了官就有股消遣的心理,有种驾驭世俗的欲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每逢闲时,我都到大学听讲座,即博览群识,又广识鸿儒,有种一箭双雕的快感。
股东们不会有这种快感,他们只体会得到收钱和裁员的快感,对我则是我不屑一顾并认为我在浪费时间。碍与中国人的中庸,传统的我不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又不太愿受金玉良言之劝诫,只有在心里憧憬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过眼烟云的潇洒。谢伟则说我双重性格,具有变态倾向。
在每次听报告或重要讲座时,都能看到一位齐肩发的女孩,着白色长裙,穿着一件海蓝色上衣,很纯,很淑女,有着第一眼看见林徽因的感觉。但这只是一种感觉,瞬过便逝。这可引温源宁在《二十今人志》中形容吴宓的话来形容:“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常有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之所以有这种不该有的忘性感觉,因为我受不了海蓝色上衣和白色长裙,多年前,我也曾经拥有过海蓝色上衣和白色长裙。
我进了多功能厅,找僻静的地方坐下,翻开我的书,便听边看。这里不允许吃东西,而在我身后的两位小姐——或女士却嗑起了瓜子,并不时讥讽这种教育。其实忍受不了的往往不是声音,而是巨恶的神态。我回头礼貌的说:“我接受这种教育时你还是细胞呢?别太牛了。”语毕,转身走出,不经点地看了一眼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少女,四目一对,彼此尴尬。我快步走了出去。
出了校门,我长舒一口气,回忆着刚才骂人的畅快淋漓,平息着刚刚撩拨起来的心痛。我扬手要打车,听见后面有人在喊“喂喂”。我回头一瞥,原来是那个海蓝色。
我心中一颤。
“你刚才的话真是太精彩了,他们太不像话。”她一下对这么恭维,着实让我感到十分窘迫。为了把窘迫还给她,我问道:“你是谁?”她一下愣住了,转而羞赧。
“你早应认识我的,每次报告会都能看到你。”
“能见到不一定认识,就算我天天看到清华四大讲师,我也不会认出他们的——况且,你告诉过我你的名字吗?”
她脸上的红晕又多了一圈,默不作声,以缄默加羞涩代替无畏的抗议。我怕她再过一回儿脸就成年轮了,便先自我介绍:“我叫楚宸,楚国的楚,宝字盖下一个清晨的‘晨’去掉日,你呢?”
“我……叫许蕾,言午许,蓓蕾的蕾。”
“唔,那这样,改天在谈吧,我要回……回家,有些事,能把电话给我吗?”说着把笔递了过去。
她的脸红扑扑的,仿佛对迅速却务实的身份介绍感到莫名奇妙,但又迅速的把电话号码写在我手上。
“你还上车吗?”司机有点不耐烦。我说了声再见便上车了。从车镜中我看到她还傻傻得站在那儿,一条白裙随风轻扬。可爱可亲可人温文尔雅这些词忽的涌了出来。“我有一种要占有的欲望。”我自言自语的说。司机用恐惧的眼神瞅着我。“我不缺车,去伟天公司。”
“这么快就回来了?”谢伟问道。
“一点小插曲,报告会终止了,不过我已经把它摆平。”
“你没说是伟天的CFO吧?”谢伟开玩笑的说。
“你怎么不说你是伟哥的代言人?”我诽谤他的名誉。
“对了,那个女孩和我说话了。”我不失时机的告诉他。
“嗯?”谢伟眼里写满嫉妒,“人长得如何?”
“温碧霞是左,周慧敏是右,两边开区间。”
我感到谢伟的语气不对,脱口道:“你的幻想到此为止,你没机会的。”
“是吗!?”谢伟怪怪的喃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