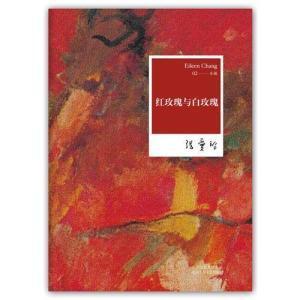■伊北
提到黄逸梵,大家总说,这是张爱玲的母亲。其实,作为一名标准的女旅行家、不到位的女画家、颇有风采的女社交家,黄逸梵在民国时代轰轰烈烈的出走女性群体中,有其鹤立鸡群处……
1
从最初的离家,到最终的客死,黄逸梵是游走在时代边缘的奇女子,她亦中亦西,又非中非西,她以敏识东方人情世故的心去交结西方,又以西方式的对自由的狂热来抵挡东方给予她的束缚——东方给了她一双小脚,西方给了她以小脚走天下的勇气。
在民初自由而又混乱的空气里,黄逸梵扮着精致的妆容,穿着翩跹的服装,迈着轻倩的步伐,在地球的纬线上历历而过,她有一百多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全新的自我,最关键是,精彩也好,无奈也罢,她都认可这种生活,并坚信这是唯一能使她快乐的方式。
在新旧时代撞击的片刻,黄逸梵的出走,有种石破天惊的味道,名门之后叛逆起来,比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要来得壮烈。可能因为从小见多识广,黄逸梵眼界颇开阔,她没有遗少们身上那种依赖传统的惰性,加之父母早逝,无顶头上司的管束,她更是做得了自己的主。
“五四”的风有没有吹到黄逸梵身上,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吹到了,究竟吹到多少,我们也不敢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她曾订购过改良版的《小说月报》、《文学季刊》、《西风》、和《良友画报》,并且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二马》看到笑出声来——新文艺与她想必是亲近的。她喜欢朝气蓬勃的东西,她是学校迷,在封建文化的沉积地带里,她需要呼吸新知识的空气。她爱钱,分家产分来一大批古董让她有足够的资本去寻找理想(这是她旅行的最重要支撑),但我想她应该更注重精神生活,钱很重要,可钱只是支持精神生活的后备军,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则永远是生命前端最耀眼的前驱者,她的这种金钱观,似乎也影响了张爱玲。
2
黄逸梵和张志沂的离婚,与其说是一对性格不和的夫妻的分手,不如说是两个迥异时代的分裂,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黄逸梵不是不曾被张志沂的真情感动过,那首朴质动人的七绝,也曾将大洋彼岸的黄逸梵召唤回家,离婚的时候,她还逼着他去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没有情还有义,她从不是把事做绝的人。可站在新文化的空气里看旧文化,那种无法磨合的冲撞,让黄逸梵无法忍受。张志沂也未尝没有痛苦,未尝不想挽留,可根深蒂固的思想背景的无交集,让黄逸梵和张志沂,仿佛两棵距离过远的树,因为最初的错过,而终究无法站在一处,更何况,她又是一味把他关在门外。
黄逸梵婚姻破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过程中,女方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五四”之后的离婚案件里,多以外出读书的男子抛弃原配包办夫人为主。可黄逸梵的离婚,却全然反转,不是男人休了她,而是她休了男人,在这场婚变中,她自认为不是受害者,她还曾交代张爱玲不要怪你“二叔”(张家大房没女儿,张爱玲口头上算是寄养在大房名下,所以喊亲身父母为二叔二婶),她利落地走出家门,留一个悲戚的男人在身后,这个转身,不能不说是漂亮。
当然,这个转身,也可能是因为爱。假如我们姑且承认张爱玲自传体小说中描述的部分情况属实,那么黄逸梵的离婚,大概与某个留学时代的同学有关。
1924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出国留学,黄逸梵就手搭上顺风车,以小姑监护人的身份,偕同前往。如此这般二婶三姑连袂留学的情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少之又少,称一句绝代双娇,不为过。在这里,我们看重的,是两个女性并排前驱的姿态——黄逸梵出走的同盟者,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女性情谊,让人暖心,也容易造就精彩。
3
黄逸梵身上有种梦幻文艺气质。她或多或少有精神洁癖,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道:她母亲这样新派,她不懂为什么不能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九莉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乐林”?她不肯说“快乐”,因为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此外还有“坏”字,有时候也忌,这倒不光是二婶,三姑也忌讳,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也是多年后才猜到大概与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黄逸梵始终给人一种少女般的印象,永远不老似的,在那张最经典的照片里,她梳着微卷的发式,笑容淡定,眼神深邃而有光,俨然一派女学生风情——学校里那种积极向上的多情空气,正对了她的胃口,再加上天生小脚的黄逸梵,没有在适学年龄进新式学校念过书,好奇心的驱使,更是不能不敦促她下定决心回炉再造。
她学油画,在外人看来,她是画家。1933年,徐悲鸿蒋碧微去欧洲举行画展,路过巴黎时,曾和黄逸梵同住一所房子,徐蒋住二楼,黄住四楼,蒋碧微称黄逸梵为画家黄女士,可见她学画坚持了很多年。可在国内外油画界里,我们到底没怎么听见过黄女士的名头,她爱学校的空气,可真学起画来,黄逸梵明显懒散。国外的风光都还没看够呢,阿尔卑斯山滑雪,大脚的小姑子都滑不过小脚的嫂子……
她学唱歌。当然也是半途而废。张爱玲曾这样写母亲唱歌: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如果有人要问,黄逸梵走后到底怎样,我们只能说,她勉强和生活打了个平手,也算胜利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