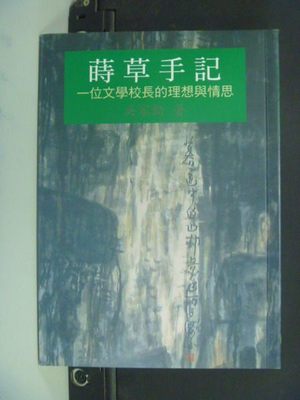“僧敲月下门”敲的是谁的门?
刘有培
高中语文第5册有朱光潜《咬文嚼字》一文。文中说:
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成“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字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先生极其武断地把“僧”推或敲的门当做了寺门来理解。并且按照现代人的习惯,把这和尚看成习惯于晚饭后出门散散步,然后再回到自家寺院休息的极富生活趣味的和尚。朱先生称他为“步月和尚”。这样的情景,在我看来,怎么也“冷寂”不起来。
贾岛的原诗为: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首诗歌题为“题李凝幽居”,诗中明白地写道“闲居少邻并”,则四周有寺庙之说自然无所依凭。诗歌中的“僧”,无论是贾岛自己,还是别的什么僧人,显然都不是要去推或敲寺门,而是要去推或敲李凝幽居的大门。诗歌的情调是“幽”,而不是“冷寂”,这一点,朱先生也读错了。“僧”去李凝幽居推或敲门的时候,是鸟儿刚栖息于枝头时(可见),月儿刚上云空时。(“鸟宿池边树”除了写景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表明“僧敲月下门”的时间,即刚好入暮)进得门后,“过桥分野色”,景致不同于门外了(门外是草径与荒园);“移石动云根”,宇宙在这里显示了另一番“幽”的景象。诗人最后对李凝说:“我还会来这里同你一道隐居的,我这就暂时同你告别吧。”
韩愈和贾岛显然比朱先生更懂得唐代的生活情趣,显然比朱先生更知道“推”和“敲”在文学上的韵味区别。贾岛经常造访李凝幽居,既可以“推”门入见,也可以“敲”门待见,这是生活中都能出现的情景。写成诗歌,自然就有用“推”好还是用“敲”好的分别。两位唐人的推敲,不仅给我们展现了他们的学识修养,而且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语言丰富的魅力与精美的表达。咬文嚼字的朱先生咬不到“幽”而是嚼出了“冷寂”,并且从“冷寂”上去作文章,自然就和韩贾二人有了高下之分了,也就和古人有了“古今之别”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