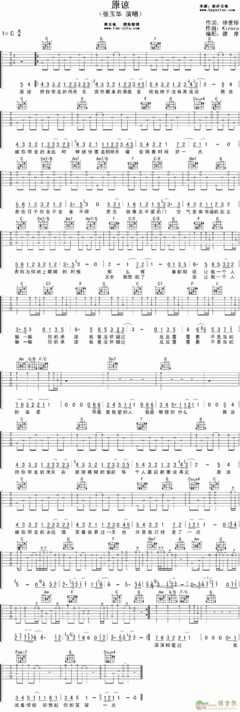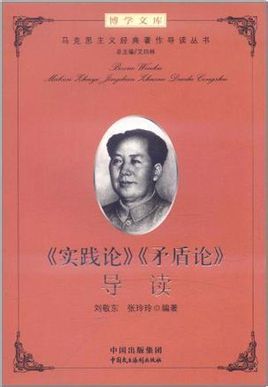读邓运华《疤痕》有感
李永芬

像是池莉说过的,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事物,不管你怎么说,它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在十几年,某部作品某个作家一直拥有读者,那就是一种摸得着的事实。
记得那是一个初夏有月亮的晚上,几个文友在公园边散步边谈,有远方的飘飘和雯,公园还远没现在有人气,现在锻炼的人在这里,象是在广场。我记得夜晚,朦胧的月色,微微的风吹过来的青草味。我那时还是菜鸟,听她们谈着所写所看所想,与文字有关的一切在我看来是神圣的。我记不清具体谈的内容了,只记得邓运华说到自己手中完稿的小说《疤痕》时的意气风发,他说这个长篇是用一两个月时间,日以继夜写出来的。那段时间他不停地写呀写,或者是在屋子里不停来回打转,完全处于“狂思”和“狂写”的状态,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漂浮了起来。
十年之后,这部小说出版了,出版之前因为还校对过,所以不止一次地又读到它,静静地再次阅读,月下谈论意气风发的一幕,又浮起来了。一些东西,写了也就写了,包括一些所谓的名人名篇,更多的还只是一些好的际遇让他们混个脸熟,十年之后还能再看的作品就很难得了,《疤痕》十年之后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就是好小说了。这是一本迟来的小说,十年前,2002年,邓运华就获得了新浪原创小说大赛前二十名,这部小说还得到过鲁迅文学院执行副主编井端老师的青睐,本来新浪原创小说大赛前二十名都是在当时就可以出版的,只因题材问题,出版才一拖再拖。如果不是这样,一心写小说,他很可能就不一样了。
生命中,痛不是常态,痒是常态,无聊,虚无,都是生命之痒,都是抓痕。抓着抓着的,人就在虚无中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抓着抓着,一生也就安然度过了。小说,也是抓痕。在邓运华的小说里,最塑造生动的一个人物是江自清,就是讲述他几十年经历的人生沉浮,命运选择他只能做一个乡镇驻队干部,官场的种种勾心斗角,各种派系的明争暗斗,情场上的痛与痒,是横截面,也是放射状的多层次的截取。
江自清是个农村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城一类大学,分配到县城的城关镇做了一般办事员,享有硬当当的学历,吃着国家的皇粮,涵盖了城乡两地的城关镇,工作人员之多,各自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之复杂,即使江自清再使出十二分黄牛拉梨的劲儿,也不过是任人差遣。十几年过去了,江自清还是农村总支的一个副职干部,成天面对丢鸡丧犬结扎上环防汛抗旱收税调解的琐事。他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也不具备当官的条件。转而往培养女儿方面,却又遇到老婆的嘲笑。老婆并不坏,甚至有着许多优点。当初江自清工作之后,食无定所,经人介绍和老婆小芹成了家。老二勇利,当过兵,精通社会上人情世故,上上下下都能闹得水浑,退伍后在贩城托舅舅关系成立了建筑公司,一步步为营,滚大了雪球。也娶到了心仪的美妻。有钱就生外心,勇利有了外遇,也走上了金屋藏娇的老路。老三德凯是潇洒的,在社会上,打得开收得拢,巧舌如簧,他电大毕业后,当了记者,娶了同学为妻。
整个故事既有官场的诡异,也有生意场上的巧取豪夺与重重机关,还有对传统婚姻的思考,生存,出轨,车祸,一些事件的呈现,写出了复杂的人性,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的男人?不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生存的困惑,职场的权衡,情感的纠葛,传统与现代的一些理念,在新经济时代的裂变,人心的浮躁,小说挥洒出的一幅幅大时代与小人物的众生画卷,真实呈现当今一代乡镇普通干部在官场、商场、情场生存状况,他们的沉浮可以作为一个阶层的样本。我们可以从小说人物名字的上,看出作家对人物命运的特别寓意。比如江自清,江水为何能自己澄清?胡德凯,胡乱都能凯旋而归么?何永利,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总是尽享利益?世界如此浮躁,社会如此不公,只能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读这部小说,需要我们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去读,人物的命运有时是与国家的一段历史密切相联的。我们审视小说中的人物,也仿佛是在审视自己,这样多少会读出一种“生存的痛楚”.让我们意识到人性之中也有最丑恶最粗糙的一面,生活的不平静,和谨慎的活着带给我们的思考。这也让我想起女作家翁想想对《疤痕》的感言:“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总在旧疤与新痕中马不停蹄。几千年农耕大国,注定绕不开最基本的生存命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目光向下,可以望见泥土;挣扎向上,也是一种姿态。即使是最底层的声音,也有存在的意义。”
曾跟邓运华开玩笑说,因为《疤痕》被认为是乡土作家,这个标签不好,去掉乡土,留下作家。作家只是在用一个介质说话,并不是受介质限制。他的小说着墨并不土气,笔墨之间,深得古典文学的精髓,语言节制,简洁,是继承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传统,在叙述、描写、刻画中,可见十足的笔力。他之后写的散文随笔,上百家报刊上几十万字面世,也是可以看到这个笔力的。
《疤痕》一书,不仅描绘了农村和城市的“疤痕”,也揭示了人自身精神深处的“疤痕”。我认为,作家就应该敢于直视社会“疤痕”、人生“疤痕”、精神“疤痕”。一部好的作品,拂去时间的灰,依然有生命的质感。它不再疼痛,以疤痕的印记醒目地存在。其实,好的作品一直在那里,经过时间的洗礼,看得见,摸得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