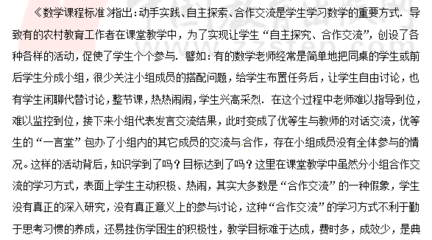忽然想起,明天是什么节日,不知道谈泓姐姐是否有感知收到,我们为她预订的礼物。
追忆谈泓,就像追忆我臆想中的初恋情人,虽然好多具体情节都模糊了,但是抽象出来的人却那么有棱有角活蹦乱跳,富有生命力,俨然脱离了她真实的衣着的修饰或者彩妆的装点,犹如我这个艺术家擅自在谈泓的素描画像上点红了唇描了眉,别人不会觉得惟妙惟肖,但我却觉得笔法如神。
追忆谈泓,就不得不想起我们如何认识。看见她是一个女孩子,初听谈泓的名字,一般会认为是谭虹这两个字的几率比较大,倘若她听见你这样记忆她的名字,她就会为你校正,直到你真的记住了谈泓这两个字,我在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被她纠正过。但那个时候,我还坚持认为那是她的笔名,心中暗想,哪有这样女生名字呢?
那是1990年8月,我们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从北戴河散营以后,连续从北戴河经历了与闫旭、胡海泉和王栋他们的分别、在秦皇岛火车站经历了与贾纳、张宇雷他们的分别、在北京站送走了口称不哭却泪如串珠的张榕、伟岸的曾清生……他们,我从单文忠兄长手中接过北京-重庆(9/10次)回家的车票,那一刻,才真正接触了谈泓。
记得那个时候,我身量未足,在人群中显得异常袖珍,似乎单文忠兄长牢记了边司令国政老师的嘱托,要确保我们平安的归程。单兄递我票的时候,特地把一个漂亮女生拉到我面前,告诉我,那就是谈泓,跟我一个方向一个车次并在同一个站下车。那漂亮女生笑呵呵地对我说,她早就注意到我了,因为她查过通讯录,我们是老乡。心中窃喜,这么可爱的女生一起归乡,岂不是丰富了这一次已经很特别的夏令营之行?
就这样我们上了归途之车,三个人,陪同谈泓一起来的还有她那个比较帅气的哥哥。那个时候,她的哥哥已经成年了,由着我跟谈泓叽叽喳喳的说话,一路上为我们买饭或者倒水,谈泓则专门负责削苹果。谈泓削苹果的姿势很美,一边谈笑一边走刀,神色看似认真,其实未加思考,因为她削水果的时候就是不断拷问我对问题的理解或者解释的时候。
渐渐地,列车过了石家庄,我们渐渐地从营友分别的感伤情怀中舒缓过来。我开始怯怯地打量着身边的这个同龄的女孩子。谈泓留有三十年代上海时尚女生额前有刘海的那种发型,凤眼,长长的睫毛,鼻子笔正但鼻尖偏高,薄薄的嘴唇,她似乎很瘦削。车过石家庄以后,夕阳西下,车厢里的气温渐渐低下去,谈泓在洁白的衬衣外面套了一件粉红的网眼罩衫。淡淡的夕阳阳光照在谈泓的脸上,车窗的风拂过,她那额前的刘海有些乱,但是谈泓却是满眼满脸的宁静。
谈泓问我,喜欢大海还是喜欢天安门?我讲,都喜欢;她问为什么,我讲,因为他们都很开阔,我们都是山区的孩子,没有见过海,想海的时候就只有仰望蓝天,但是蓝天又太遥远;谈泓讲,她其实更喜欢大海,喜欢北戴河海滨那沙滩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因为这样的海才真正纯自然地显得雄壮和开阔,天安门尽管也曾经,但某一建筑物挡住了她远望的视线,所以她已经不太喜欢这样人为的破坏。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奇怪,一个看起来温顺和善的女孩子,干嘛有这样挑剔的想法呢?这个问题多次困扰着我。
这样的旅程在与谈泓的交谈中慢慢缩短。谈泓和我说话困了,就头枕双手躺在桌上眯一会,我睡不着,靠着车厢望着车窗外,观察那些被列车丢下的城市或者村庄,在谈泓熟睡或者醒来的时候。一般地,遇到两列火车相遇,呼啸而过的声音总是会吵醒她,她会用手慵懒地揉着眼睛问我时刻,然后又躺下;或者遇有站停靠的时候,谈泓也会醒来,邀请我一同下车去走,记得有一个车站停靠的时候,正下小雨,谈泓非常开心在雨中行走,笑称那是我们难得的雨中漫步。记得那时候,从北京到重庆需要经过两个夜晚,大约在中午时分停靠在达县车站。
也是正午时分,我与谈泓分别在达县中巴车的小红旗桥站台,她先从我的身边站起来,第一个冲下去,她的哥哥跟她的后面,她匆忙地绕过车头,走到我靠窗的那一边,把那双修长的软软的手递给我,我赶紧把手伸出来,尽力的够到车窗外,希望能与她紧紧一握,但就在我们两只小手快要接触的时候,车已经发动,我的手已经够到不到她的手,于是我和她的手都慢慢伸起来,作出再见的姿势。那一年的元旦节,谈泓在贴有卡通图片的明信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真后悔当初那一次不曾紧握你的双手/纯真的友谊必然不忍他们分开。
我与谈泓就慢慢分开了,疏远了,因为紧接着我们的就是高中那红色的生活,从高二开始到高考结束的压抑,禁锢了我的思路,密闭了我的情感,我差不多跟营友们失却了联系。黑色的七月以后,我在某所高校报名的时候遇到谈泓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后来的同班同学,我打听她的消息,兴致勃勃地。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那同班同学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答案。
似乎天旋地转,又似乎又千万只银鱼吞噬着我的耳膜,我只觉得这个世界就只剩下嗡嗡嗡嗡的声音,她已经在高考前微笑地走了。同班同学告诉我,他从没看见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死会给全校师生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噩耗传来,谈泓的同学和老师无不泪流满面。谈泓那个时候,在我心中,仿佛如仙女,刚刚从我的面前升空,她的衣袖长长地飘散着,在空中舞动着,她与她洁白的裙裾化作白云或者粉红的朝阳,停留在我的天空。
同班同学告诉我,谈泓在学校成绩并不是门门都好,但却是每个老师都喜欢的女孩,每个同学都愿意亲近她,只因为在她那里总可以找到不同的观点和理由,同学们都不敢相信谈泓会是他们的同学。谈泓住院的那些日子,曾经多次昏迷,在她告别这个世界的头一天深夜,她已经昏迷过一次,一起守候她的女同学用哭声把她唤醒;第二天中午时分,谈泓原本可以轻声讲话了,她看见身边的同学,还流了眼泪,就在刹那间,谈泓转过头去,就停止了呼吸。同班同学告诉我,他们理解,那个时候谈泓流泪,是因为她敏感地意识到她那生命的状态。
我原以为,只有我跟谈泓走的那么近,如今想起来,自己却是那么地浅薄。臧彦钧、曾清生……陈捷他们,都是那么地喜欢她,以致于我们集体相约在这个深夜,这个情人节的早晨,写一篇文章,作为送给谈泓姐姐的礼物。姐姐的生命,在14年前,她刚刚跨过18岁那年定格在那里,永远美丽成一幅图片,以她对师友真挚的情怀和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眷恋,当然也包括与我短暂的同行中留下的如梦的记忆,飘动在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头顶上的天空,一如她在我纪念册上那看起来十分温暖宽松且四方的签名一样,通过阳光的映照在我们的心中,鼓励我们珍惜一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