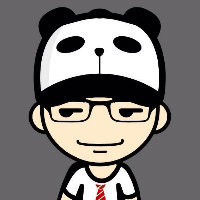二十一
石矮子、虎子和糊涂虫三足鼎立,撑起红砖厂一片天。除了把握住销售市场,我显得像个多余人。但我人闲心不闲。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等待着我去完成;我必须摆平那个大写的花和尚——螃蟹——对舞儿的控制。

螃蟹可不同于花和尚。一个真老虎,一个纸老虎。这真与假的区别其一在于螃蟹跟我一样,差不多是个亡命徒。我因为心中的女神亡命;而他因为上帝说这世间需要补充一个亡命徒而亡命。我一个人造的杂种!他一个天生的杂种!其二在于我捏住了花和尚的软肋(从而每每在较量中得心应手),而我对螃蟹几乎一无所知。螃蟹跟前老总一样,肯定是瓜分金属材料公司的巨蠹之一。这个,似乎可以成其为我击破一个堡垒的突破口。可是我手中并不曾掌握他半点贪污挪用的证据,因而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剩下的只能是硬碰硬较量,准备一场搏杀。我并不害怕一个小小的黑道。黑道算什么!我是一个没机会上战场的行武者,自命武圣的弟子!我只怕手中无兵可用,反之,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杀他个螃蟹们人仰马翻。我会用脑子杀人,而螃蟹不过匹夫之勇。如今,我有了自己的雇佣兵或黑道——虎子手下不是囤着一些个城乡结合部的地痞流氓,可以下打花和尚,上击螃蟹的吗?难道我让虎子组建这样一支队伍的初衷原本不是蓄意而为的吗?有了钱,就能买到兵!就能买到意气风发!反之,你屈死吧!狗日的世道!
我决定通知舞儿:两个男人要为她了结一场恩怨。或者,我准备失物招领,我对她说过的。
我约舞儿在阳子关市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见面。我的高贵的舞儿只有经常出没于那些个高贵的场所,才能活脱她高贵的气质。她是我的女王。而我至此只让她扮演了一个灰姑娘的角色,不,我让她与禽兽为伍!我让一只白天鹅与一头河马混迹!
我要了一个最好的房间,我准备着一个国王与王后同床共枕。这以前,国王与王后身边总要见到几个伺者之类穿来穿去吧,所以,我包下酒店的空中花园做会客室。
舞儿来了。流光四溢!
她显然生产过,腆起的肚子不见了踪影,代之以一身米黄的丝质旗袍紧紧裹了平复的腰肢。她向我走来,那贴近肉色的流光在丽日下刺目地闪亮,几近让我目眩。她溶化在那团摄魂的光焰中。
光焰在闪耀,跳跃!
不可以止止的深度诱惑!舞儿整个一浓妆艳抹。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我敢打赌,她这副打扮肯定是凭生第一次,因而也是精心的。我一直设想她是一朵冷冷的出水芙蓉,却不曾想她同样是一朵火火的骄人牡丹!那高高挽起的发髻,那浑然天成的美额,那深邃如穹的眸子,那微微翘起的鼻头,那肉感十足的嘴巴,那裸露无遗的耳朵,都经过蓄意的修饰,一扫昔日的羞怯,大胆地宣布说:我来了!
我想触摸那香水丛中的乌丝,我想舔过那写下梦境的额头,我探问着那呓语喃喃的目光,我吸吮着那甜美如汁的鼻息,我要蹂躏了那小嘴儿到支离破碎,我要对着那小耳朵儿窃窃私语。我的舞儿!你还是我的!
我差点喷血而亡!舞儿有着一对何等杀伤力的巨乳啊!它们几欲撑破那多此一举的遮羞布,像一对贪吃的小白兔那样破笼而出。它们是白的,白得那根根青筋儿在皮层下若隐若现,我见过的;它们也是嫩的,嫩到不会输给一个含苞未放的少女,尽管舞儿已近二十七岁。这会儿,它们肯定将一份傲慢肆无忌惮地大写了!
一对哺乳期的乳房。肿胀得让我心惊肉跳!我曾经悄悄告诉舞儿,除了乳房小了点,她完美无缺。其实,她的小咪是适中的,只是我偏爱一个拥有波霸的美人而已。她这就携了两只沉甸甸的果实而来,洋洋自得的样子,是什么意思?是要问这样子好看吗?她日后会用五花八门的丰乳剂让她的美乳定格在眼下的样子吗?我是会这样子建议的,但不是现在。我差点窒息,我只能让我光芒四射的眼睛说话。舞儿肯定读懂了我!一棵椰子树,挂果在丰年里,这不是魔鬼身材是什么?我要死了。
见我一开始就陷入昏昏然,舞儿肯定感觉不错。她在我对面不足一米远的一把木椅上款款而坐,优雅地伸直两腿,以免那开口不算高的旗袍弄出皱褶来。她的美腿裸露无遗,但她不显得害羞,因为我是她如胶似膝的情人呀!她的嘴角挂满微笑,甚至有点儿放肆,因为她自知这会儿无可挑剔。那对高耸的乳房俯冲过来了,竟然突出身子画了一个钝角强的抛物线!我恨不得撕烂那片破布。
但我急冲冲抽身而出。我假装看风景,跳出舞儿那对糖衣炮弹的射杀半径之外。我的意思简单得很:我不想这就被舞儿射杀掉,我先要跟她说说话儿。但我的举动显然吓坏了舞儿。远远地,我发现她怔怔地望了我,脸庞抹过一片乌云,然后,像黑云蔽日般垂下眼帘。
那垂下的眼帘俨然电影里的埃及艳后。
我又是激动、又是心疼地回到她身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