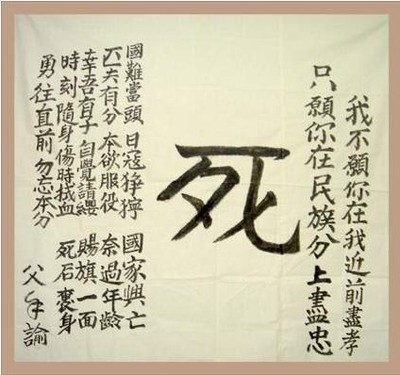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片名是出自赛德克语“seeddiqbale”的译音词句。seediq有两种词性,当做普通名词时有“人、别人、众人、人类”之意,作为专有名词时则属本族的自称用语──赛德克;bale是“真的、真正的”,因此“seeddiqbale”直译时为“真正的人”。实则seeddiqbale(真正的人)常用于称赞、敬佩有作为的人,凡对族群、社会、国家有卓著贡献者且受到大家的肯定都称做“真正的人”。
2009年底,魏德圣导演筹拍近十年的《赛德克·巴莱》终于开镜。由于该片的对白主要是以本赛德克语(以下简称本族语)来发声,且本族语几占整片的九成左右(包括插曲、旁白等),这也是导演与剧组人员为忠于历史现场所做的决定。
因此,开拍以来我就亦步亦趋地跟在拍片现场“倾听”该片赛德克语的对白,因我受邀担任本片赛德克语的指导员及历史、文化顾问。开拍三天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撰写一本《随拍札记》,除分享我随拍的心得与感触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告诉我部落的族人──“在电影《赛德克·巴莱》所演绎的剧情中,有哪些桥段是与我清流部落遗老的‘口述历史’有相违背之处。”因在拍摄现场我看到了与我所认知的“雾社事件”不同的情节,意识到影像的力量不容小觑。值得庆幸的是,在导演及剧组同仁的鼓励与支持下,本拙著“《真相·巴莱》──赛德克·巴莱的历史真相与随拍札记”,于2011年10月间顺利完稿付梓,并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
赛德克族
赛德克族是由德固达雅(SeediqTgdaya)、都达(SediqToda)、德路固(SeejiqTruku)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移居地花莲县秀林乡、卓溪乡、万荣乡以及宜兰县大同乡与南澳乡等。台湾光复至今,赛德克族与台湾境内的各族群,包括本省籍、大陆籍或台湾其它原住民族群通婚频繁,其子女于户籍族别栏中,注记为原住民籍者亦不在少数;另因就业之便逐次迁居城镇、都会区者渐增,目前赛德克族的人口约略估计为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只因初获正名,注记族别名称之户政作业尚在持续进行中,故较确切的人口数以相关单位所公布者为准。
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
赛德克族的传统部落是以Gaya/Waya为主、部落意识为辅所建构的传统农猎社会。Gaya/Waya是赛德克族的律法、是赛德克族的社会规范,该律法与规范是历代祖先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故亦称之为祖训,部落意识则建立在Gaya/Waya的基础上。
赛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领导人,即俗称的头目。除部落领导人以外,部落长老、各传统祭仪的主祭司、巫医及文面师等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并非世袭制,部落长老常是部落领导人的举荐者。其次是狩猎团及猎首团的解梦者、善猎的男子以及工于织布的女子等亦颇受族人们的敬重,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她们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上流社会群。
赛德克族语“alang”──有部落、区域及邦国之意。因此,赛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单一的部落群体,而常常是由二个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两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两边的缓坡地,绵延1~3公里可能散布着数个部落;通常会以该地区最早开发之地名为区域名称,但不一定是部落名称;或以主部落名作为该地区的名称,此时的部落名也代表着地区名称。
强烈的“部落意识”是赛德克族传统部落生活的核心,部落型态的组成基础及部落族人的互动模式,都由部落意识的凝聚而形成。传统部落的初始型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紧密关系之中,人与人的依存关系逐形成部落的集体意识,这样的集体意识发展为强烈的部落意识。
赛德克族虽属父系社会,但很多现象却透露着赛德克族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例如赛德克族人的传统名字,在子女与父母连名的族规(Gaya/Waya)中,可“子父连名或子母连名”,亦可“女父连名或女母连名”。又若家中无男嗣则可招赘为婿。赛德克族的家庭结构看似男性作主,但在为新生子女命名时或在子女论婚嫁的场合,女性长者的意向往往凌驾于男性长者之上。
汉族“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型态,并不完全适用于赛德克族的传统家庭状况,因在赛德克族的家庭乃至社会的互动模式中,除较粗重的工作及纯男性(如狩猎)性质的庶务以外,几乎已很难再细分一定属男性或属女性的生计工作。在婚姻制度上,赛德克族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在族人恪守族律之下,赛德克族的社会几乎杜绝了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违犯祖训的男女异常关系。尤其有血缘关系的男女,至少要经过五、六代之后始可论及婚嫁,这与汉族“亲上加亲”的表兄妹联姻观是完全不同的。
文面:至高荣耀
赛德克族人坚信“人身虽死,但灵魂不灭,不但不灭,‘他们’还要回到祖灵们永久共同居住的地方去。”这是赛德克族代代口耳相传的古训、祖训,也是赛德克族的“宗教观”与“生命观”,有人称之为“祖灵信仰”。
赛德克语“Utux”,今汉译为“祖灵”,其实Utux是泛指一切超乎自然的力量,所以Utux是神也是鬼、是灵魂也是鬼魂;有人就以此观点将赛德克族的传统信仰视为“泛灵信仰”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当外来宗教尚未传入赛德克族的部落之前,Utux是他们唯一的宗教对象,他们既不拜天叩地,也不祭祀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山川溪流等自然界的任何事物或现象。
不过,尽管Utux是赛德克族唯一的宗教对象,但并未形成因Utux的信仰而产生任何宗教派别、固定的祭拜仪式以及固定的祭拜场所。
在赛德克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强烈族群特质的就是“文面文化”,赛德克族人深信唯拥有文面者,往生后灵魂才能回到祖灵(UtuxRudan)的身边。换句话说,男子若要回到祖灵身边就必须要文面,要文面则一定要成功猎首而归。猎首成功者手掌必留有血痕(呈血红色),手掌的血痕是辞世后灵魂要回到祖灵身边无可取代的烙印。女子也有相同的意涵,善于织布而取得文面资格的女子,其手掌上会因勤于织布而留有血痕,这手掌上的血色是永不褪色的,但在阳世间时“人眼”是无法辨识的。唯手掌上拥有血痕者,在他/她们离开人世后,始能通过“祖灵桥”头守护神的检视,她/他们的灵魂才能够安然行过祖灵桥回到祖灵的国度。这是赛德克族的祖训,也是赛德克族人终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文面是赛德克族人成年与族群的标记,男子表示已具捍卫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维护家庭生计及冷暖的织布技能,没有文面的族人,将难立足于赛德克族的社会。文面是赛德克族人在世时的荣耀、是赛德克族人的成年礼,更是赛德克族人自我认同的族群标记。
消失的祭仪
赛德克族主要的传统祭仪有播种祭、收获祭、祈雨祭、狩猎祭、捕鱼祭及猎首祭等,任何祭仪的意象无不祈望族命得以绵延、族运得以顺遂发展,其诉求的对象即崇信的Utux,各祭祀团体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祭祀团体的主祭司皆颇受族人的敬重,其社会地位不亚于部落领导人(俗称头目)。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是自古人类求生存的自然法则,因此播种祭与收获祭可说是赛德克族的重点祭仪,两祭仪的主祭司都采世袭制,传男不传女、承继者的顺位依家中男子之排序而定。
赛德克族的主要作物中,播种祭与收获祭的祭祀活动仅及于小米(macu)及黍米(baso),其它作物不需通过播种或收获的祭祀仪式,两祭仪同属赛德克族农猎时代的重大祭典,是同一区域内赛德克全体族人都要参与的祭祀活动。因居住区域的不同,赛德克族三语群的族人是各自举行区域内的祭祀活动。
但以上所列之传统祭仪,随着时空背景的转换、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今已不复存在。我以为,人类的文化会随着所处环境背景的不同而转移默化,如何掌握文化固有的本质是我们的责任,如何赋予文化以新的时代意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赛德克族大事件
1895
4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8月25日桦山资纪发表“欲拓殖台湾,必先驯服‘生番’”的谈话。
1897
1月“深崛大尉事件”──探察台湾横贯铁路中部路线的深崛陆军大尉一行14人在德路固(Truku,今仁爱乡合作村静观部落)附近被杀;日人对雾社地区展开全面封锁行动。
1902
4月“人止关事件”──埔里守备队与雾社群(SeaediqTgdaya)在人止关附近发生战斗,中村中尉以下18人轻重伤。
1903
10月5日“姊妹原事件”──雾社群被日军封锁多年,在急需补充物资的情况下,日人趁唆使布农族干卓万社(今仁爱乡万丰村)假借物资交换之名,诱骗雾社群至两族交界之地进行交易。布农族人将他们灌醉之后,趁夜展开攻击行动。雾社群赴约交易的百余名壮丁中,仅有五六人死里逃生返回部落,造成雾社群惨重的伤亡。
1910
开始实施“五年理番计划”。马赫坡驻在所巡察部长近藤仪三郎,娶头目莫那鲁道(MonaRudo)之妹蒂娃丝鲁道(TiwasRudo)为妻。12月“雾社方面讨伐行动”。
1911
1911年1月9日“雾社方面讨伐第二次行动”。2月“撤废南投厅内各社之头骨架行动”。7月“雾社一带原住民企图反抗”。8月15~9月23日因上述发生于7月的企图反抗事件,日方“招待”雾社地区各群头目至日本「观光」一个月。
1913
9月“南投厅全面禁止刺青”。
1914
2月实施“断发”、禁止“凿齿”。
1916
12月近藤仪三郎在花莲港厅任内失踪,蒂娃丝鲁道(TiwasRudo)独自返回故乡。
1920
9月18日“纱拉茂抗日事件”。起因是泰雅族纱拉茂(Salamaw)群的族人,袭击当地合流分遣所与扪冈驻在所的日警及眷属。
9月20日“讨伐”行动开始,除了日警之外,雾社、都达、德路固、白狗、马烈巴、万大等群亦被煽动参加。
10月16日日人出动雾社群斯固社、荷戈社、波阿仑等社400人包围纱拉茂群,激战后双方互有死伤。
10月30日日人出动雾社群马赫坡社、荷戈社、波阿仑等社150人进行搜索,发生战斗后双方互有死伤。
11月10日部分纱拉茂族人交出枪械,停止反抗。
11月18日雾社群出动125人,砍得25颗人头后凯旋返回雾社。
1924
3月1日泰雅族眉原群(Baala)各社及南阿冷社被集体迁居至今日的部落所在地(新生村眉原部落)。
1925
2月23日花冈一郎通过台中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成为雾社地区第一个原住民师范生。
1929
10月27日花冈一郎与川野花子结婚,花冈二郎与高山初子(高彩云女士,原名ObingTado,荷歌社头目塔道·诺干/TadoNokan之女)结婚。
1930
4月5日花冈一郎担任马赫坡驻在所勤务,并任教于番童教育所。
8月8日花冈一郎转任至波阿仑(Boarung)驻在所值勤。
10月27日爆发“雾社事件”。
11月5日“一文字高地”战役──此役日人受到教训,开始以部落间传统仇恨煽动,并以提供赏金和枪枝弹药为条件,威胁利诱附近各部落协助日军的行动。
11月10日都达群总头目铁木·瓦力斯(TeymuWalis)在立鹰牧场附近的哈奔(Habun)溪中伏,被起事之原住民击杀。
1931
4月25日“第二次雾社事件”。
5月6日“雾社事件”生还者112户、298人被强迫移居川中岛(今互助村清流部落)。
纱拉茂抗日事件

发生于1920年9月间的纱拉茂抗日事件,并非如外传所说的──莫那鲁道趁纱拉茂地区的泰雅族部落壮士入山狩猎之际,率领本族勇士屠杀其妇孺。事实上,爆发“纱拉茂抗日事件”时,日警以其惯用的“以番制番、以夷制夷”之卑劣手段,唆使、煽动本德固达雅(雾社)群、都达、德路固、马斯多邦、马烈巴、万大等所有雾社地区(今南投县仁爱乡)泛泰雅族群的部落族人参与“讨伐”行动。自9月20日至来年(1921年)的10月间,轮番袭击“纱拉茂”地区部落的泰雅族人有15梯次之多。依当时的交通状况,雾社到梨山地区仅能翻山越岭徒步前往,且要通过属泰雅族领域的马斯多邦(今仁爱乡瑞发祥村)、马烈巴(今仁爱乡力行村),若不经日警的从中布局,其他族群是无法通过该地区的。因此,莫那鲁道绝对不可能率领本族勇士,恣意进出梨山纱拉茂地区妄杀其部落妇孺,更何况本族与纱拉茂地区的泰雅族几乎不曾往来;“纱拉茂抗日事件”之前,两族之间也不曾留下有争战的口传轶事。
土布亚湾之役
“雾社事件”爆发后,在日本人的唆使利诱下,都达群的族人开始协助日方进入山林搜索、猎杀赛德克族的起义战士。1930年11月10日,都达群总头目铁木·瓦力斯(TeymuWalis)率领56名族人,发现并尾随赛德克族12名战士,准备予以猎杀,于是双方在雾社东北方哈奔(Habun)溪上游的土布亚湾(Tbyawan)溪谷发生战斗。对战之际,铁木·瓦力斯阵亡。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以番制番”之毒计所酿成的“兄弟对战”的战祸,而赛德克族战士完全是出于自卫。
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文献资料上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亦称“集中营屠杀事件”),事实上还是日人“以夷制夷”狠毒阴谋的再得逞。略述如下:
赛德克族起义战士经与日军警对战近50日,既遭受不人道的化武攻击之后,原计约1300人的起义六部落族人,余生者516人(日方诱降或逮捕者)分别被监禁于两处集中营,一处设于Drodux部落(今仁爱乡仁爱国中现址),另一处设于SipoSuku部落(今仁爱乡春阳村境内台湾大学实验林),而美其名为“保护番”收容所。不幸的是,余生者陷落日警两手策略的操弄——他们右手安抚监禁于两处集中营的幸存者,左手却怂恿利诱都达族人袭击两处集中营。1931年4月25日约凌晨4点左右,都达族人兵分两路同时夜袭已解除武装的两处集中营的族人,两处集中营顿时成为人间炼狱。于“集中营”内遭到袭击的起义六部落幸存者,因无力(已解除武装)反击而在昏暗的夜里四散逃窜,大都避难至其他部落(含都达群)的亲戚家,但日方又将逃散的余生者由各部落押回,再次“收容”于今仁爱农会附近临时搭盖的帐篷内。
所幸都达群与本德固达雅群,虽因族群猎区之争时有龃龉,但两群之间的通婚、往来从不间断,所以袭击两处“集中营”之际,他们有枪(刀)下留人是清流事件遗老们的感受。清流遗老温克成(TadoWalis)、傅阿有(TiwasPawan)及蔡茂琳(PawanNawi)等就表示:“NasiinilhalingkaseediqTodaciidagenakatawadamthedu,kiyatanaqmtraima,seediqTodakaalangtaBoarunghiiduri。汉译:若都达人当时真要赶尽杀绝的话,我们两处集中营的族人有可能全部遭害,还好我们双方一向有通婚之谊,而且我们的Boarung部落也是由Toda人所建立的。”事后,日方却对外声称为“本族群内部的冲突”,自恃可一手遮天以掩天下人之耳目,称“第二次雾社事件”;起义六部落的余生者经日方“保护”收容之措施后,由516人锐减至不足300人。
“集中营屠杀事件”一夕之间震撼整个雾社地区,即刻引起同属德固达雅群的巴兰(Paran)及多岸(Tongan)部落族人之悲愤与骚动。若非当时日方在埔里及雾社地区驻扎有一定优势的兵力,以及巴兰和多岸两部落头目的忍辱负重,力劝族人相忍为族群的未来着想,否则我德固达雅群有可能会因而付出族群存亡的代价。
眉原部落族人之再造之恩
当幸存者们再次被“收容”于今仁爱农会附近临时搭盖的帐篷内时,期间有今眉原部落(alangMbgala)的头目尤给夫·那威(YukihNawi)、帖木·西雅兹(TemuSiyac)及一位副头目来到该“收容所”探望幸存者。事实上,他们来到雾社最主要的任务是,说服起义六部落的幸存族人迁住川中岛”,以顺利达成日方之所托。以下是清流部落族老的说法:
迫迁川中岛之前,眉原部落有三位头目来到雾社探望我们,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派来游说我们迁往这里(清流)的。当幸存的族人听说“desuntanatheruyqurihunac。汉译:日本人要将我们迁离雾社地区”时,没有一位族人愿意搬离祖居地而他迁。以前的年代,部落之间的事务都由双方头目处理,远从眉原来的三位部落头目,我们当然要给予尊重,族人们推派以巴卡哈·布果禾(BagahPukuh,嘟洛度呼部落头目)及莫那·西内(MonaSine,马赫坡部落副头目)为首的部落代表与其协商迁住事宜。眉原来的三位头目大概逗留了两个晚上才离开。据说,巴兰(Paran)部落的大头目瓦力斯·布尼(WalisBuni)及其他本群的部落头目也为这次的协商结果背书,至此我们要被迁离故土的传言似乎已成事实。果然没过几天(笔者按:1931年5月6日),我们幸存的族人分两梯次迫迁至川中岛。
在这一过程中,幸存者除携带着简单的衣物外几乎是空手来到这里(清流部落),即使是族中男子从不离身的猎刀也没人佩戴(被没收),男子后来所拥有的猎刀都是后来才添购的,女子用的织布工具也都是慢慢稳定下来后才重新制作添置。幸存者们初迁至川中岛时可谓一无所有,于是眉原部落的族人伸出了“同胞大爱”,供给物资为他们解决吃的问题,拨出人力协助我们建房筑屋。幸存者们起初的耕作用具、作物种子、种苗也都是他们提供的,举凡食、衣、住等日常生活所需都尽其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幸存者。期间更以一户对一户或两户类似“认养”的方式,辅助他们在艰困中自立更生。
幸存者们之所以能在这块土地上“浴火重生”,除了他们坚忍不屈的精神外,眉原部落族人的“人间大爱”,是身为清流子孙者一刻不可或忘的“再造恩情”。当然,自起义失败被逮捕、禁于集中营以致流放川中岛,尚且能提振当时灰心丧志、绝望求死之人心,除眉原部落族人的适时援助外,不能忽略了巴卡哈·布果禾(BagahPukuh)头目有形与无形的影响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