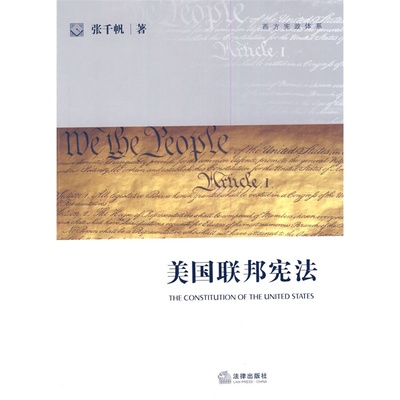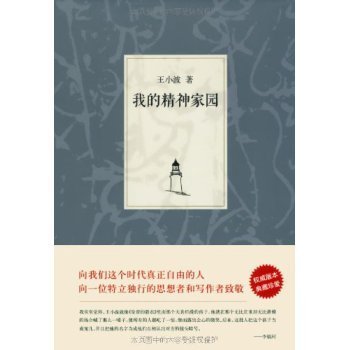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
——昭通女作者散文综论
黄玲
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基本同步,昭通文学的热潮涌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表,在小说、诗歌、散文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客观地说,女性写作者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对文学活动的参与上,都没有体现出和男性并驾齐驱的可能。即使在80年代那样的文学大潮之中,女性因为家庭、事业等因素的束缚,她们的身影也还显得比较孤寂零落。在小说、诗歌领域虽然也有一些参与者,但并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取得突出的成就。倒是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在女作者们的默默耕耘下,开出了一片绚丽的花朵。

也许散文文体更适合女性,它以行云流水之势书写内心情怀、诉说岁月感慨的特点,它以平易近人之态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恰恰切中了女性之所长。从含苞到盛开,女作者们笔下的散文已经走过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昭通女作者文集·散文篇》:高原女性的集体发声
1999年编印的这部《昭通女作者文集》虽然外形简朴,又是内部资料,但它在昭通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具有开创、奠基的意义。是有史以来,昭通女性写作者的第一次集合亮相。其中收入5位作者的小说12篇,14位诗人的诗歌43首,33位女作者的散文80篇。虽然文体芜杂,但单就散文部分而言却是进入女作者们心灵世界的重要通道。从数量上看,散文的作者队伍和作品数量也远远大于小说和诗歌。这是否可以说,女作者们更擅长或更青睐散文这一文体。
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写作和女人无关,她们的任务不过是生儿育女,为人妻母,她们的生命象沉默的流水无声流向远方。如笔者的散文《高原女人》所言:“历史的碑石只记载高原汉子的雄姿和豪饮,女人们则被挤压成小小的斑点,如明月身旁的星星,永远保持沉默的眼。”但是,“高原能有久远的厚重深沉”,也是因为有一群绵软如水的女人,用她们的血汗和乳汁哺育着高原的土地,用她们粗糙有力的手指撑起高原明亮广阔的天空。”走进这些散文,也就走进了高原女性的精神天空,可以聆听她们深情的咏叹。
单是从题目这一角度,就可以初步领略到女作者在散文写作上的审美理想与追求:“渴望爱情”,“真情永驻”,“高原女人”,“雨中母亲”,“钟爱的天空”“唱给新生命的慢板”,“抓住生命的这缕阳光”,“平静,恬静过人生”,“亲情如云”……女性情感的温润细腻如行云流水般进入读者视野,诉说着她们对待生命、爱情、家庭、事业、亲情的期待与追求。
在高原女性获得文学话语权之前,我们无从走进她们的心灵世界,感知她们的生命内蕴。但是现在,通过散文这一形式打开了一道与世界对话的门窗。女性追求自然率真的天性与散文文体之间找到了一种默契。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散文最好的篇章,无一不是质朴、清澈的。写散文的人,大抵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和自由心性,并没有哪个人,端着写作的架子而能把散文写好的。散文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见写作者容貌和心思的。”[1]
散文写作的冲动首先源于生命对世界的感动与感悟,这一点与性别无关。只是女性对世界的观照与领悟更具感性色彩,心性更加自由率真。尤其一但放下俗务走近高原壮美的自然存在,更容易激发出她们生命中潜藏着的浪漫基因,从而萌发出散文写作的灵感。李萍的散文《匍匐在大自然怀里》正是心灵与自然撞击之下的收获。旅行途中的风景在作者内心勾起的是儿时在大自然怀抱成长的记忆,正因为这种记忆拉近了作者和自然的关系,让她找回一份重回自然怀抱的喜悦。她在用心倾听,所以听到了“天的呢喃、水的低语、草木的心声”,在这个瞬间作者的身体和灵魂都进入了与大自然现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她期待“在自然的优美和声中,还会有我的灵魂在娓娓的浅吟低唱”。今天回首再读这篇散文,仿佛可以感知早逝的李萍灵魂依旧在大自然的怀抱轻徊低旋。
作为生活于地处偏远的高原小城昭通的女作者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着许多关于乡村关于大自然的美好记忆。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培养了她们的审美视野,所以她们的散文中不自觉地出现了许多描写高原风光的篇章。这些散文的可贵在于她们不仅仅单纯地写风花雪月,而是在与大自然亲近的同时也在感悟思考人生的意义。宋兴菊的《大山包的黑颈鹤》中,在描写大山包的美丽风光与与黑颈鹤这一自然精灵相融相谐的存在时,还向纵深继续开掘散文的内蕴,感悟着黑颈鹤身上的精神对自己人生的启示:鹤在艰难条件下的勇敢飞翔、鹤的团结友爱精神、鹤对爱情的忠诚……无一不感动、影响着自己。所以作者在散文的结尾自然升华自己的心灵:“当你失意而迷惘时,痛苦而沮丧时,不妨想想头顶严寒、苦苦繁衍的黑颈鹤,你会觉得太阳变得明亮了,人生充满希望了。”
杨莉的《峡谷行》《火山》中,对高原壮美的自然存在进行了充满诗意的赞美咏唱,视野大气而开阔。袁梦夤的《黄连河瀑布游趣》则表现了在大自然怀抱的快乐与情趣。
这些描写高原自然美景的散文,有不同的视角与开掘,但都体现了女作者们身居高原而养成的独特的精神境界。热爱赞美是写作的基调,但也在对外部世界的表现中不断审视与思考,追求精神和艺术的升华。这样的追求使这些散文呈现出一种大气的精神气象。
作为在历史文化长河中长久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写作者群体,一但获得话语表达的权利,她们会自然承担起为女性代言的责任。在文学的天空下她们由被言说而变成自我言说,第一次有机会用文学书写女性生命的丰富内蕴。所以,即使没有加入任何文学潮流,没有女性主义理论的明确导引,她们的散文也会不可避免地会把笔触伸向女性的生活、心理、情感等领域,为读者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姿的独特空间。她们写自己的童年、成长记忆,写对亲人的怀念,写对女性生命的感悟。没有刻意去展示性别,但性别的因素又无所不在,女性在生活中承担的各种角色潜在地影响、制约着她们的写作。面对社会她们有事业的追求,面对家庭她们需要扮演女儿、妻子、母亲的多重角色。性别,是一种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真实存在。也正是她们身上承担的多重角色的互相转化,拓展了女性心灵、情感的空间,使她们的散文呈现出姿态繁复的审美倾向。
散文是直抵人心的文体,它需要真诚、坦率地传达出作者心灵的声音。“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2]这一点在昭通女作者的一些散文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李新文的《贫贱童年》《我心深深处》都是写童年成长的记忆,贫穷、曲折、苦难,构成了特殊年代生命成长的背景,它赐给一个女孩子的是坚韧、顽强的品质,还有朴素的心灵。文中所写的生活具备了特殊年代的特色,和同时代人有大至相同的记忆。但这两篇散文在平常的生活表象后面隐藏的却是作者不平常的精神空间,它所传达出的是当代女性对更深层的情感的期盼与诉求。《贫贱童年》中,“贫与贱”是无法逃避的人生苦难,而支撑作者走过苦难之途的却是质朴无华的亲情。母亲活着时五孩子虽然生活艰辛但还有母爱的呵护。失去母亲之后他们在生活的风雨中挣扎、成长,依赖互相间的亲情支撑起人生的风帆。作者的叙述中回旋着一缕淡淡的忧伤,也有苦难中收获的一份执着与坚韧。《我心深深处》这篇散文更有一份深沉的意蕴,它所传达的是一个女儿对父爱的渴求与追问。它超越了对生活表象的平面记叙,笔触直指心灵深处的伤痛与缺憾,是女儿对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父爱的呼唤。沉重的生活让父爱变得坚硬,女儿对父爱的渴求似乎成了一个不现实的梦想。这篇散文的意义就在于,它传达了特殊年代“女儿们”的共同心声,具有时代生活的代表性。
昭通女作者们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她们似乎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引导下,不自觉地进行着女性历史的回溯与建构。那些关于奶奶、母亲、女儿的散文,无意之中建构了一条女性生命的血缘之链,也表现出无法割断的精神传承和内在联系。曾焱的散文《回忆奶奶》,夏吟的《奶奶的故事》,不仅是成长过程中温馨的生活琐事的记忆,更是在回顾总结奶奶的人生给自己的启示。黄玲的《雨中母亲》、黄德琼的《母亲的泪》,是女儿对母爱的感激与学习。夏吟的《唱给新生命的慢板》则是从母亲的角色,为孩子唱一曲希望与祝福之歌。女作者们在不同角色的变换中更深入地感悟生命,丰富和拓展着女性生命的内蕴。
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昭通女作者群的散文很快便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它们如天上的白云,自然、飘逸,展现了高原知识女性丰富深沉的心灵世界,传递出她们在现实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审美追求。
二、《山花烂漫》:女性心灵之花的绽放
这部由夏玲主编,2007年出版的散文集共收入昭通8位女作者的64篇散文。在时间的流逝中,当初那些站在散文写作队伍中的身影发生了一些变化。来来去去之间,文学也由80年代的辉煌逐渐走向平实与坚守。但散文依旧是女性倾诉心声的最好方式,在日常生活平庸琐屑的磨练中为女性生命保持了一份可贵的精神之域。让我们得以窥见她们丰富广博的心灵世界,听到她们生命深处传来的律动之音。
和第一部散文合集相比,《山花烂漫》的作者数量虽然少了许多,但却体现出更整齐的态势,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文学视野,和80年代作者群的创作相比较,都有着新的提升与进步,集中展现了90年代以来昭通女作者散文创作的可喜成果。从中可以形象地感受到女性生命的涌动和女性主体精神的成长。这和当代中国女性散文的发展也形成了某种呼应,在文学众声喧哗的格局中坚守着一份宝贵的精神家园。
首先这部集子的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体现了女性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进步,她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目前正在高等教育、新闻传播等领域从事文化工作。其次,因为现代化科技的引领,她们的生活领域和精神空间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体现出更新更高的精神追求。更重要的一点,她们是在比较明确的文学观念指引下从事散文创作,并将其视为构建自己精神空间、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如本书作者之一的杨琼所说:“文学首先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寄托,一种安慰,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花朵,文学同时也是我们以善良之心关注更多生命、生存的一种载体,它应该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真、善、美”。[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女作者们在文学观念上的自觉,她们不仅仅把散文视为自己倾诉情感的手段,不满足于心灵一隅的窃窃私语,更希望能借助文学之光去烛照更多的生命,为世界送去关爱与温暖。这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入领悟和思考,也使这部散文集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审美支点。体现在艺术风格上,则因为女作者们在生活阅历、工作性质、个性特色上的诸多差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因为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一一解读,只想从中提炼出几个关键词,作为走进这部女作者散文的路标,以期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山花烂漫的境界,去品味、感受女性生命之花盛开的美丽。
情感。这是散文写作永恒的追求,原本应该和性别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女性更擅长、重视对心灵内部的开掘,以及对生命的自我体察和省悟,对生命历程中的苦难、孤独、脆弱等内蕴有着比男性更敏感细腻的感受。女性温婉如水的心性和散文自由率真的天性相结合,女性体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将盛开出别一样的散文花朵。
在人类的情感领域有一些主题会常写不衰,代表着人类情感的基本走向。诸如爱情、童年、亲情,它们既是人类生活体验的结晶,也蕴藏着个体生命成长的密码,记录下她在人生旅程中的欢乐或者痛苦。在昭通女作者的审美视野中,这些主题也是她们的散文中常见的主题,体现了她们丰富的心灵蕴含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而且会因为女性意识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所谓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在体察世界、生命时独特的眼光、视觉和心理感受,不自觉地会受到自身性别的潜在影响。“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由于我生而为一个女人,女性主义就不可能不是我内在的组成部分。”[4]著名学者戴锦华的这段话道出了女性写作的真谛。无论写作者承认与否,性别因素都会潜在或者显在地对她的写作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任继敏的《前尘》《彩色的梦》《穷形尽相》等一系列散文中,就以略带惆怅的情绪回望着家族历史中行走的一系列女性身影,她们是一代代的女儿和母亲,她们如花的生命和曲折的人生道路之间形成巨大的审美落差,引人感叹。而作者的生命也正是在一代代女性的身影映照之下成长,父爱的缺失让她只能汲取着母系的精神养份走向成熟。文中那些不乏琐碎的生活场景和细节,浸润的是作者成长的心血。这些散文既是作者个体生命的印记,也再现了一代女儿成长的曲折与艰辛。
曾焱的散文,擅长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对女性生命的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建构。她笔下出现的奶奶、母亲、女儿,形成了三代女性的生命链条,既在文化的浸染中完成女性性格的塑造,也在无形中传递着母性精神的博大与温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为女儿的她开始对女人的品质、内涵、理想、愿望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探寻。在《茶室闲话》中,她以品茶般的淡泊心态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只想做一个“平凡幸福的女人”,回到传统的光阴里过简朴温馨的人生。她也在追问着婚姻爱情中女人的命运、甚至还有对待生与死的思考。在她的散文中既可以感受到女性生命的种种快乐,也能领会到那种深刻的疼痛感,对女性情感之域的两极都有独到的表现。
张英、杨琼、陈卓、陈允琪等人的散文中,也有一些表现女性情感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对女性的婚姻、爱情、生命内蕴进行深入开掘,让我们得以洞见女性生命的多姿多彩。
情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动因。昭通女作者们散文中的情感表达,因为女性意识的影响和制约,多了一份阴柔之美,也多了一份丰富的内在意蕴。如同一条潺潺溪流一路咏唱着温婉的歌,真正实现了“我手写我心”的散文理想。
行走。这是近年来出现于昭通女作者散文中的一个新词,它传递出的信息是丰富的,意味着现代知识女性生活领域的扩大,精神疆域的拓展。在历史的记忆中,女性的生活空间一向狭小,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此也因此而受到局限。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为知识女性在理想和事业上的飞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山花烂漫》中就有几位作者从事的是新闻工作,为她们在大地上的行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收获了独特的审美内容。王冰关于“行走”的散文已经形成一个系列,她行走的大多是滇东北比较偏远贫穷的地域,诸如大山包、威信、彝良、鲁甸,但她的散文却能超越新闻纪实的视角,把目光聚焦于高原壮美的自然存在,通过行走实现精神世界的审美升华。行走中遇到的凡人小事,则进一步丰富了散文的内容,使作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和谐的互动。也使精神的翅膀不至于因为飞翔得太高而失去大地的气息。
陈允琪的行走似乎对历史中的人文气息情有独钟。她到石门坎《寻找柏格理》,到鲁甸寻找《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乐马厂古银矿》,到荒冲感受乡村的宁静和民族生活的魅力。面对岁月沧桑中的历史尘埃,她的心灵在品味中波动、感悟、提升。柏格理的传说留给她的是对信仰的思索,对生命的大悲悯和大热爱的感叹;历史深处的古银矿则让她领悟到岁月变迁中沉重的沧桑之感。这些散文中充满了理性的精神,也体现了知识女性对世界的审美高度。陈卓的行走疆域在都市,《我在广州“飘”》一个“飘”字载起了当代知识女性的另一种生存际遇。广州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浓郁的商业氛围,也在无形中拓展着作者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让她从现实中的“漂”朝着另一种境界“飘”,后者既代表着轻盈的姿态,也意味着飞翔的高度。
行走这一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女性生活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联系。也为女作者的散文写作增添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思辩。散文的思辩色彩是女作者散文中最有意味的内涵,它体现着写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散文可以表现家常里短的琐碎,让岁月的浮光流云从窗口飘出灵动的光影,也应该还有更高的审美追求,由生活的表象向着更深层面去追索生命的价值、意义,才能立体地呈现出女性生命的丰富,完成女性主体精神的建构。让读者形象地感受她们由曾经的精神依附走向精神独立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山花烂漫》中的一些篇章为读者呈现了当代知识女性智性的一面。
夏吟把自己在诗歌中的某些精神带进了散文创作,她的散文既有对生活中爱与温情的描绘,也不乏对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的思考与掘进。《在小城市孤独的生活》是一篇回顾她所走过的文学历程的散文,既是对现实中时间流程的回顾,也是对自我精神历程的一份文学总结。其中对生命中所经历的理想、追求,痛苦、忧伤,写作中的孤独寂寞,都有生动的描述。生活空间的狭窄和心灵追求的广阔所导致的矛盾冲突曾经一度困扰作者的心灵,让她深深陷入痛苦与挣扎。幸好现代科技手段下的网络和阅读,为她提供了走出狭窄的途径,而文学则是她彻底走出心灵束缚,实现灵魂飞翔的重要手段:“我没有自生自灭,写作把我从生存状态的封闭中彻底解脱了出来,灵智洞开……”。
在都市繁忙中生活的陈卓为自己《虚设书屋》,目的是提升生命的内涵,不让自己失落于滚滚红尘。虽然是“虚设”,但也传达了作者心中对“书香”的尊崇,对精神的坚守。张英虽然曾经《辛酸地成长》,但是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她也在思辩生活对生命的馈赠。杨琼在《地震》中对生命的朴素、渺小和无所不在的坚韧进行思辩,力图从中获得生活的信心。曾焱的《茶室闲话》充分体现了“闲话”的特色,从生活琐事到古代的墨子,从女人到怀旧,看似散漫的思绪串起的却是女性对世界的思辩,对意义的追问。
文学中的思辩,是对形而下生活的形而上思考,也是对散文艺术品质的重要提升。《山花烂漫》中的思辩虽然还不够成熟和深刻,理性的空间尚需提升。但还是体现了女作者们在文学之域的可贵探索。意味着她们的主体精神已经觉醒,在成长中不断壮大。文学既给了她们敞开心灵的窗户,还提供了升华理性的天地。可以让世界谛听到发自女性灵魂深处的智慧之音。
三、长篇散文《巾帼乌蒙》:拂去岁月尘埃
夏吟2011年创作的长篇散文《巾帼乌蒙》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它首次对乌蒙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事迹进行集中扫描,以突出她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这本书的意义体现于它选材的独特,作者力图拂去岁月尘埃,把被历史遮蔽的人和事呈现于读者视野,犹如干花在温水中复现,重新绽放她曾经的光彩。让我们得以了解在乌蒙高原坚硬的男性峰峦后面,女性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所作的贡献。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段历史,女性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但历史是由男权文化的主宰者书写的,女性无论做出多大贡献,她们的身影注定了只能以闪烁的方式点缀其中。即使是贵如吕后、杨玉环、则天武后那样的人物,也难以避免被历史篡改、被不同文化视角根据需要加以利用的命运。所以女皇武则天才会在自己身后留下一块巨大的“无字碑”,一切留待后人评说。这就是女性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宿命。
夏吟是一位21世纪的当代女性写作者,也许正是这个文化身份让她对故乡那些被岁月尘埃遮蔽已久的同类们心怀一份向往,她们虽然不能像男性那样驰骋疆场、彪炳史册,但也曾经努力参与到历史的过程,以自己之所能试图去改变、创造、推动历史的发展。她们中有的人所创造的业绩,甚至比七尺男儿还要恢宏,还更值得赞美。如昭通政协主席熊启怀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昭通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开发较早,历史悠久,自古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底蕴深厚,又由于社会制度与中原有一定区别而富有特质,为昭通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正是因为乌蒙边地开放、包容而不乏原始古朴的文化氛围,才会有和中原不同风格的一批乌蒙巾帼的诞生。她们人数不多,却如一条涓涓细流,汇进乌蒙历史的长河。从公元前六世纪杜宇时代,和望帝杜宇共同创造“杜鹃啼血”美丽传说的梁利起,到晋朝的少女将军李秀、起兵抗元的彝族女首领奢节、明朝维护祖国统一的彝族女首领奢香、实卜,到现代造福桑梓的龙志祯、四十年代就任云南省女参议员的张守义、南箐中学女校长张邦珍,到早期参加革命的女地下党员,到当代首位世界乒乓球冠军邱钟惠……一条乌蒙巾帼文化的长流被夏吟的文字勾勒得生动而鲜明。
这本书的历史跨度很长,作者用四辑巧妙地把岁月裁剪成不同的版块。
第一辑“传奇芝兰”主要写古代历史中乌蒙女性的身影,传说与想象结合,描绘出了古代乌蒙文化孕育出的巾帼风采。在认真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文字浸透了作者的女性意识和视角,既对笔下人物充满诗人式的激情,又对史料有理性的节制与把握,避免了对历史的“戏说”。第二辑“荣曜秋菊”中的人物更加贴近读者,她们主要生活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其事迹和传说在昭通民间史上曾经流传甚广,给民众留下的印象可谓深刻。比如云南省主席龙云胞妹龙志祯女士,人称“龙三姑太”,她婚姻的传奇性在民间曾有多个版本的演绎。她还因为对家庭、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国家褒奖的“贞节孝女”。更重要的是她对昭通近代女子教育作出的贡献,在她力主下昭通20年代末即开办女子中、小学,对昭通女性知识者的成长作了重要铺垫。这一行为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某种思想的超前性,值得大加颂扬。作者所用的篇名“造福桑梓的贞孝女”,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龙志祯的人生。第三辑“含笑冬梅”,是对革命历史之页中本土女性的描写,在近代革命号角的召唤下,女性也开始投身解放事业,谱写出全新的人生篇章。比如1930年就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女战士白宗华、滇东北妇女运动的先驱马冰清、为理想而奔赴延安的罗文英……。第四辑“华茂春松”介绍的是昭通籍文体、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巾帼英才代表。
面对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如此繁复的人物、事件,夏吟在写作上颇费了一番心思。除了按生活的时代和人物的贡献来划分类别,她在写作中还做到把历史资料的考证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尽量保持人物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又尽力体现出她们身上拂去岁月尘埃之后的鲜活与生动。因为她们的加入,在昭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又多了一份特殊的内容。让读者从中感知到乌蒙大地虽然没有物华天宝的优势,却不乏人杰地灵的独特。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并非由男性独领风骚,女性也曾贡献过自己的才华甚至生命。而且她们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之间从来都是密相联的关系。
《巾帼乌蒙》对复原历史和激励当代女性的奋斗精神,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昭通女作者们创作的散文,是昭通文学中一笔重要的财富。它体现了当代知识女性对社会、文化的参与,也是女性独立的精神品格和智慧的结晶。它所体现出的细腻、内敛的审美特色和智性的光芒,为昭通散文增添了异彩。
(作者简介:黄玲,女,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已经刊于《昭通学院学报》2013年1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