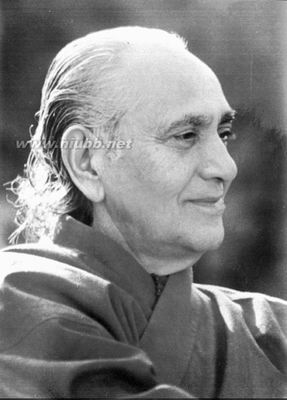是我很久没看电影,也是很久没看到这样触动心灵的电影了。以至于,看完以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想与所有人来分享这么一部简单朴实,又是如此震撼内心的片子。
要不是乐琳在微博上与我分享音乐《Himalaya》,我都还不知道它。没看电影以前,光听那节短短的藏密音乐,就觉得魂都被牵了进去。“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这颗心,只在当下。”如乐琳所言。遇到倾心的曲子,习惯性就是单曲循环播放。重复又重复。停不下来。该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啊,当时就在想。单听主题曲都这样被吸引。
是在一个心情并不晴朗的状态下,打开《喜马拉雅》。当藏密梵音响起,尘烟弥漫的粗犷大地,奔腾的牦牛群,和那片欣欣向荣的麦田出现的时候,纷杂的头脑立即自动安静下来。只消三分钟不到。有人曾说过,如果一部电影在开头十分钟以内,无法向观众清楚的传递想要表达什么,那就不是一部成功的电影。那么如果一部电影在开头三分钟以内,就能够让心彻底平静下来,且充满观影兴趣,一定是部不可多得的好电影。
《喜马拉雅》故事简单,朴实。却给人感觉别样干净。干净得足以荡掉你心内所有的污晦。整部片子贯穿始终的大气。纯粹。辽阔。自然。深远的。且冒险。粗犷。荡气回肠。
不知是因为先听过了主题曲,还是因为亲身涉足过那样的土地,影片从头到尾都感觉可亲可敬。那样雄伟的山、那样壮丽的雪、那样洁净的湖、那样淳朴的人。故乡一般的亲切熟悉。
我们没法及时干完了——这要由神决定,我们不用决定,只要去做就好了。
你害怕了?我不害怕去拒绝。
我们总是联系在一起,我们总是那么像。
要懂得聆听整体的节奏。
如果你要选一条路去走,那么就选最难的一条。
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对白,可是简单的话语句句闪闪发亮。盐包掉地,年迈的老头人蹲地悲怆,及时赶到的诺布扶盐而起,父子俩沉默的眼神交流,生长群山深处的生命,所有的情感,喜乐,哀愁,皆如群山一般沉默默。还有诺布与母亲头碰头,是血浓于水的默契,会心的微笑。每个镜头都衔接得,那么恰到好处,那么温暖人心。
诺布与父亲荒原夜话,“要走就要选最难的路走。”听了心头微微一颤。其实人生又有那条路更容易走些?行路难,行路难。也只有在步步惊心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更加认真、更好专注,更用心踏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也会更珍惜并临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活在每个当下的清明觉知中,因为一步即是一生。屏弃安逸之路,选择最艰难的道路前行,才是生命真正具备的精神与力量之所在,因为最难的路会成就最好的自己。
而影片中所谓的“魔鬼之路”。其实是美得令人眩目的、慑人心魄的湖光山色。换成是我,我也会和帕桑一样高兴着,能亲眼见到“恶魔幽灵”了呢。老头人的坚强意志,始终向前不畏艰辛的精神,虽是固执与天马争强好胜,可是那股坚恝不倔的力量,却也无时不刻感染着人们始终向前向上。
跋涉,只为去到梦中的麦田。去到有小麦生长的地方,用盐包换回麦子。那里是富饶的土地,那里有生活的食粮,有生存的希望。那里还有参天绿树,爬上树就可以看得很高很远的,那是诺布与帕桑共同的憧憬。你能想象么?生活在喜马拉雅深处,世界屋脊的人们,一辈子难得见到一棵树。
一部好的电影让观者的心灵升华,意识也大大的扩张。连日来,沉陷在一股情绪里无法自拔,终于在将近两小时的《喜马拉雅》里被冲刷干净。在观影后心清月朗。我想所有的创作,所有伟大的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某些时刻,给予相遇的人以之生命最纯净的感动,给予阴郁的心灵空间注入敞亮的光吧。
《喜马拉雅》最大的闪光点也就在于拍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连接,真实不造作,精神力量的传承,还有坚持,勇敢,善良,淳厚的生命品质。
《喜马拉雅》拍的也就是导演EricValli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的导演,才能拍出这样的片子。我敬佩这样热爱生命、热爱天地,谦卑又勇敢的,了不起的创作者。
心平。2013.10.30
电影简介:
《喜马拉雅》是法国电影人雅克·贝汉奉献给我们的“天.地.人”三部曲之一,雅克•贝汉担任该片的制片。其他两部是《迁徙的鸟》和《微观世界》。
仙境一般的喜马拉雅人迹罕至、一队雪山行旅风雪凛冽中缓缓行来,藏密梵声如仙乐般在耳边响起……本片是法国、尼泊尔、瑞士和英国四国合拍的剧情与纪录大片,获2000年度第25届凯撒电影节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和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它的拍摄队伍是《点虫虫》的原班人马,他们历经长途跋涉1万3500公里、深入海拔2万7千米高山、忍受高达65度C的日夜温差、历经9个月难以言喻的艰辛拍摄而成,片中的全部演员都是在临时在当地选出来的藏族同胞。影片内容蕴含了深刻的寓意和启发。展现了藏族人独有的崇敬天地、与大自然合作的信仰及生活观,以及人与大自然间循环相生的真谛。制作本片音乐的仍是《微观世界》的布鲁诺古雷,他凭借本片的音乐再次获得了法国凯萨奖及影艺学院最佳原声带大奖,藏族民歌与藏密梵呗的神秘气息,再加极具气势交响乐,使喜马拉雅山的风光与人情更显无穷魅力。
附录:《活在我的故事里》专访导演Eric Valli
文:尔尼http://weibo.com/cozurlovely
2月刊Mind艺术美学:http://weibo.com/mindmagazine
他是Eric Valli,作为《国家地理》、世界新闻摄影一等奖摄影师;奥斯卡提名、法国恺撒奖以及柏林电影节获奖电影《喜马拉雅》导演;爱马仕、路易威登合作艺术家,他拍摄我们从未梦过,甚至不知其存在的人生与风景,他与他的镜头一起,经历暴风骤雨,雨雪冲击,跌入过悬崖,高山严冬的冰湖,炎夏热辣的沙漠。他听得懂一草一木间大地与天空的语言,在他的镜头下,讲述着天地之间被自然耕耘的人们,血肉之躯下与自然神迹紧紧相连的故事。“
突然,Eric感到脚下的积雪在持续颤抖。此刻的他站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积雪抖动的声音越来越响,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雪崩。
山顶的积雪倾斜狂轰,雪势已经下来了。
Eric震惊地站在那里,他的身影已经在无边的雪山上即刻浓缩成一个黑点,即将被吞噬埋葬。可当他以为死亡到来的时候,崩裂的白雪突然在他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分开,他被下落的积雪成人字形夹在中间,人字两边的积雪持续下落。
目瞪口呆看着眼前瀑布般分流的雪,雪崩仿佛是为了他而分开。
他活了下来。
“不骗你说,其实我觉得要是这么死了就棒极了,我喜欢这样死去。总比死在这儿好。“
Eric身着棉麻衬衣和我围坐火炉边,他爽朗地笑出声来,眼前的火炉里木头与火花在嗞嗞作响。”这儿“指的是他在巴黎的家,是他在现代社会的痕迹。偌大的客厅里种着一棵高大的树,整排明亮的落地窗外的后院里放着一扇藏族木雕大门,是从他以前尼泊尔的家里搬运来的。饭厅里挂着他的好朋友TenzingNyima喇嘛画的唐卡,画的是电影《喜马拉雅》里的藏族村dolpe的景象,我们仿佛不再是在巴黎,而是在喜马拉雅山脉里某个古朴的藏族木屋里。
身后传来尼泊尔厨师做饭的声音,饭桌上刚刚邮寄到的水电气单还没有来得及收,Eric双眼望着远方继续说:“因为我在这里只是存在着,而在那里我活着”。
一个月前,我打通了Ericvalli经纪人的电话,提出这次采访要求。经过两周邮件和电话联系和等待,终于获许了此次采访,从一开始的邮件采访到后来的电话采访,原本以为这会是奥斯卡导演一贯的大牌作风,直到Eric接通了电话,他在那头爽朗地笑起来,“哈哈,尔尼吗,我知道是你,我一直在等你电话,你不能来巴黎吗,我觉得我们必须坐下来慢慢聊一聊,这些问题多么有趣。如果住宿不方便,可以住我家,完全没问题。“这场采访忽然就变得像一场冒险,一次奇遇。我坐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就像在他的故事里,无数冒险与相遇的开始一样。
他是Eric Valli,作为《国家地理》首席摄影师;奥斯卡提名、法国恺撒奖获奖电影《喜马拉雅》导演;爱马仕、路易威登合作艺术家,他拍摄我们从未梦过,甚至不知其存在的人生与风景,他与他的镜头一起,经历暴风骤雨,雨雪冲击,跌入过悬崖,高山严冬的冰湖,炎夏热辣的沙漠。他听得懂一草一木间大地与天空的语言,在他的镜头下,讲述着天地之间被自然耕耘人们,血肉之躯下与自然神迹紧紧相连的故事。
害怕是件很有趣的事
天空是我的屋顶,土地是我的床
草木是我柔软的耳朵,
就像流水和云朵一样,
我,独自,穿过这无边的荒漠。
——佛教僧人河口慧海
17岁的Eric第一次告诉父母他想去旅行的梦想时,他的父母,就像许许多多的父母一样,带着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对孩子的担忧拒绝了他。少年Eric不忍放弃,不久后,鼓起勇气问父亲“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做“。“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告诉我如果换做是他,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Eric说。这次谈话是一次妥协,一种了解,父母同意了他的计划。他前往中东,在黎巴嫩,利比亚,土耳其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旅行。那是在1970年,正是”黑色九月“发生的时候,慕尼黑惨案引发整个中东地区国际恐怖活动的狂潮,美国出动军舰战机轰利比亚。”我在利比亚,没有感到一点危险。“Eric笑着说,“所以这就是生命为什么美妙的地方。”
“我看见了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方式,一切都和我之前熟悉的不同,突然这些未知都在我眼前展开。你必须要冒险,从未知悬崖跳下的那一刻,生活的魔法就会发生。从此以后,世界不仅仅是存在着,他们新鲜地活着,你在那里,清醒又锋利地活着。”说到这里,Eric环视了一圈他舒服的房子,“而在这里,我就像个僵尸,被文明操纵。”
冒险继续,二十岁的黄金时期,他的脚步穿越非洲金黄的纳米比亚沙漠,穿过战乱与争纷不断的中东及阿富汗,他到达尼泊尔——此后在这里居住20年,在这里他开始用父亲送给他的莱卡相机拍摄他的旅程,并在这里遇见他的前妻,也是在这里养育他的两个孩子。
用他的话说,在尼泊尔,他开始了“讲故事“的生涯。
他的第一个故事“绝壁上的采蜜人“,讲述了在喜马拉雅山崖间古老采蜜者的故事,这套图片登上了《国家地理》封面并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一等奖。他的镜头对准了大千世界里遥远的角落:泰国岛屿上攀登洞穴的采燕窝者,尼泊尔公路边的流浪人,喜马拉雅森林深处的母系部落,喜马拉雅山脉里的藏族运盐村落……他的故事总是提醒着人们在文明以外的地方,有一个未知的古老世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要讲一个好故事,需要时间和耐心。现代人很喜欢用‘知道’这个词语,我们有电视机和各种各样媒体不停播放世界各地的新鲜事,我们觉得好像知道这个知道那个。可我们知道什么呢?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候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空洞“
“那你觉得你‘知道’你拍摄的人和风景吗?”我问他。
“我不能说我知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Eric回答我。
“有一天,我被困在下雨的山崖间,一个当地人邀请我去他木屋避雨。在那里我发现了挂在他木屋里的藤梯,他指了指木屋外几千米的山崖,告诉了我已去世父亲的故事,他是一位绝壁采蜜人。于是我用几年的时间走遍了喜马拉雅的大小山路去寻找尚存在的采蜜部落,机缘巧合下终于找到世界上现存的最后一名古老采蜜师。那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并没有时间浪费在我这个外国人上,于是我告诉他,如果你去世了,你的采蜜技术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除非你有一个徒弟——而我就是那个徒弟。”Eric说,“然后我拜他为师,在与世隔绝的村落的悬崖间学习了两年,拍了这些照片。我很小心地用知道这个词语,我会谦虚地活在他们的命运里,为他们见证,然后我才会说‘噢,我知道他,那个绝壁的采蜜人’。”
“悬挂山崖间,野蜜蜂在眼前飞舞,你难道不害怕吗?”我问。
“你知道,害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害怕什么?未知的冒险,当我到达恐惧的边缘时,我就到达了我从来不知道的世界,然后我们感叹,看这个世界多美妙多神奇啊!”
选择最难的一条路
“巨大的雪花落下,覆盖着缓缓行走的我们和用力呼吸的兽类,5000米之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我们行走在先人走过远古道路,成群的牦牛在雪白的陡峭山间仿佛一道墨印,牦牛,人,雪都在天地间移动,多么震撼人心。”
——法国探险家André Migot 《Caravans versbouddha》
1951年,法国探险作家André出版了他在喜马拉雅徒步的旅行书。12年后,年仅12岁的EricValli把这本书读得熟烂至心,书中描述的山脉景色,藏族传统,人性的坚韧在幼小的Eric心里形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冒险画卷。20多岁的他来到这片野性的土地,徒步在陡峭山间的每一条小道,他来到了雪山下的Dolpe——世界上最高的村落,在这里拍摄了由当地藏民出演的剧情片《喜马拉雅》。随着冬虫夏草热潮,他跟随原本住在喜马拉雅山间的一家人背乡离井去高山挖虫草,拍摄了纪录片《喜马拉雅大淘金》。
电影《喜马拉雅》讲述的是小村落Dolpe的故事,是Eric在徒步喜马拉雅时发现的原始村落,由于粮食不能自给,世世代代靠运盐为生,远处运盐的牦牛在雪山间像一条漂浮着的黑丝带,好像他小时候在André书中读到的那样,他在这里住了下来,和当地藏民成为好友,一住就是20年。“当地文化已像冬雪一样慢慢消融,如果我们并心合力拍摄出这部电影,那么以后我们的子孙就可以通过它了解祖辈曾经有过的生活”,Eric说。
在这里,他遇见了村庄的部落首领Thilen,一个血性方刚,满头白发的倔强头人,20多年前,还是青年的Eric找到已经是他好友的Thilen,向他询问生活中自己面对选择的困惑。“他告诉我说,‘任何时候当你眼前有两条路时,总是选择最难的那一条,因为最难的那一条路会压迫出最好的自己。’”Eric说话时双眼发亮,“最难“两个字仿佛给他带来了活着的力量,突然他站起来,挥舞双手,大声说道,“于是我就在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给予你的全部,你不实现你的梦想,如果你不去尝试,还有什么意义?就像在面对无数自然人为的困难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团队完成这部电影。
‘最难的一条路’总是鼓励我勇敢坚定的活着“这句话也被编写进了电影的剧本里,这部故事片几乎是另一种形式的纪录片,而Thilen在《喜马拉雅》里的角色就是演他自己,在这部电影里Eric几乎没用专业演员,演员们都是Dolpe的村民。”还有谁能比他们自己更适合演自己呢,在电影里的每一幕,就是他们的一生。”在电影里还有一位喇嘛——Tenzin他演的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现实中他是头领的儿子,自小在寺庙里画唐卡,从未出来过,Eric敲响了他寺院的门说“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在描绘佛像之外,你愿意描绘你的村寨你的人民吗?“Tenzin喇嘛跟着Eric踏出了寺院,参演了电影,在两条路之间,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最后他画了一副Dolpe的生活画卷,现在就挂在Eric家的客厅里。
《喜马拉雅大淘金》是另一部Eric在喜马拉雅的作品,一部关于虫草的纪录片,去年在中国向观众播出。“真菌寄生在虫体内变化成植物,大自然多么神奇!“Eric感叹。在这部电影,他跟随虫草采集者一家人爬到海拔5000米的高山,跟随中级收购商在喜马拉雅山脉探访一座座高山,最后一路跟去虫草销售地中国。他跟着尼泊尔农民一家生活几个月,为了一个远景他可以不顾危险爬过几座山。”你不担心危险吗?“我问,”不。危险从来不是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喜马拉雅20年里,他度过无数致命的危险时刻,跌下高山悬崖,经历为他分流的雪崩,活过村落突然流传的瘟疫,“如果活得饱满,活得充满生命力,死就没有什么可怕。“他气定神闲地说,“最难的路“仿佛是喜马拉雅这20年来教会他的,像藏族人民那样朴质,像雪山那样透明,像大地一样安定。
永远不会拿走比我需要更多的东西
“我喜欢活在他人的生活里,活在我不存在的命运里。我拍摄的人物都是我的老师,我悄悄地潜入他们的人生,去学习,去记录。去学习原始森林里的阳光雨露,去学会在文明世界里我遗忘的道理。“
——Eric Valli
在Eric的镜头里,人类以一种我们不曾相识的远古方式与自然相惜:他们有粗制的发辫,古铜的皮肤上是太阳的颜色,带着野性十足的自信与勇气。这样的生命,是被文明绑架的都市人没有的,我们双眼只看得见楼房的高度,丢失了与天地自然相融的信仰——一种来自生命真正灵魂中的对话。
在Eric刚刚完成的旅途里,他去探访了在流行文化侵蚀的美国,一群背离城市,栖息在自然中的人们,他给他们取名《相遇在时间之外》,他们离开城市,来到自然中栖息,与鸟兽同坐,看山野唱歌,钻木取火,砍柴建屋,活得像荷叶间的露水,自然通顺。
Eric在这时间之外相遇与美国快速文化背道而驰的各种“古代原始人“,和他们一起在荒野中生活了三年。“我觉得我活着”,说起自然中的生活,他如是说,“我们活在一个人口不断增加,资源不断减少的年代。然而大多数的人的欲望却在增加,我们消费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吃的用的越来越奢靡。而当我们在自然中生活,我永远不会拿走比我需要更多的东西。“
用中国的说法,盲目又贪心地活着,就像是佛家中的“贪”、“嗔”、“痴”,分别是指对欲望,情绪,喜好的偏执,这是现代人的通病。而对治方法分别是”戒”、“定”、“慧”,是道德的规范,内心的专注,生命的真意。翻开历史,如是陶渊明,庄子,去自然中寻找自己的“戒定慧”,躬耕一片心绿。在Eric讲述的故事里,在自然中生活的人是活着,而城市中的文明人却一直在为了如何活而伤脑筋,我们依靠着无数社会环节链,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生活。
Eric说起他们的时候,满眼敬意。“我欣赏通过手工劳动自给自足的人,他们知道怎样活着。反而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Eric叹了一口气,摸着额头感叹道。“我们发明了电灯,却忘记夜晚有满天星辰。我们用着高效率的手机节约着时间,却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
如今的Eric暂住在巴黎的家为了自己下一部电影做准备,平衡着自己流浪者与城市安稳的生活,直到今天他还有现代文明的“文化冲击”,无法彻底适应城市生活。我们的采访从中午一直到进行到傍晚,喝掉两壶藏茶,烧掉了十多根木头。虽然非常不适应城市生活,但他对他周围的同事和家人充满了感恩。“我觉得很感激”,他真诚缓慢地说,“因为身边的人总是对我很好。”
相信他随时做好准备出发,前往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前往黑暗与恐惧的边缘,前往文明的光亮未曾触及的地方,那里的天空有老鹰追逐月亮,那里的大地有神灵眷顾,那里的人有涉世之初的淳朴,他们的双眼可以照耀太阳与月亮。EricValli的镜头把世界未知大门打开,活着让他人的故事里,让我们遗忘的自然之光照耀进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