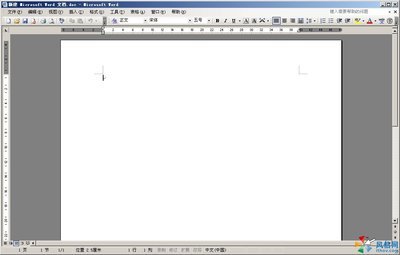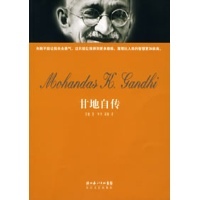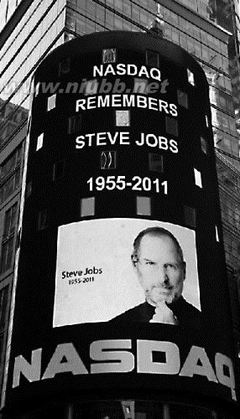让译者写两句啊,Slash,伟大的吉他手,他的自传英文版前一阵子,346的Slash给我的,当时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我是节奏吉他,可是我也忘不了看他们那首《NovemberRain》视频的时候,Slash在小教堂前独奏的一幕,每次看到都会浑身冰冷,眼泪涌上眼眶,所以我打算花点儿时间把这本书翻译了。纯粹为了学习和交流之用,如果侵犯了什么,赶紧通知我,也鼓励大家购买正版,如果中国上的话,我计划买一本,不过ebay上卖的,现在看来还是有些贵。
因为里面有图片,在这里编辑成原来的效果,实在太难了,所以就把图片版贴到了图片区,估计得点开看吧,我在电脑上试了一下,没问题。
ok,let‘s go
“致我可爱的家庭,为了他们对我所有的支持,无论时光好与坏。”
“并且致所有枪炮玫瑰的歌迷,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新与老,没有他们永恒的忠诚与无限的关怀,这里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Slash
序
已然考虑了所有的事儿
那种感觉就像有根棒球棍当胸给我来了一击,而另外一根在我身体里面搅和着。一个清晰的蓝色光点在我视线的角落里升起,那是一个生硬的、苍白的、无声的痛苦。你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坏了,也没什么东西眼瞅着有了改变,好在这痛苦我还能挺住。我仍然在演奏,并且完成了歌曲。听众们不知道我的心脏在演那solo之前已经折了个儿了。我的身体遭受着折磨,这也算是种因果报应,我在台上已经有很多次故意把它演奏成跟loop-de-loop一样。
那种痛苦很快变成了一种缓和的疼痛,这让我觉得舒服些了。无论如何,我能觉着自己还活着,至少比起刚才经历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更像活着。我心脏里的小机器在提醒着我生命是多么的宝贵。这样的时刻简直没的说了:在我面前有无数的观众,我演奏着吉他。只是在那一晚,我得到了清晰明确的暗示(指心脏的反应—punk),有好几次。并且,在巡回演出接下来的每一次登台,我都得到了那个暗示,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将会真的来临。
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医生给我的心脏里植入了一个心率转复除颤器(ICD)。那东西大概三英寸长(1inch=2.54cm--punk),用电池驱动,从我的腋窝切口处植入,它会持续的检测我的心率,当我的心脏跳动过快或者过慢,它就会释放一些电击来进行调节。十五年的酗酒和毒品让我的心脏差点就爆了,当我被送到医生那儿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还剩六个礼拜能活。从那次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年,我身体里这个小机器好几次救了我的命。我同时还“享受”一个大夫没跟我提及的方面:就是当我的心脏跳的太慢的时候,除颤器就开始工作,让死神再晚那么一两天找到我的家门,不过同时,除颤器让我的心脏跳动加快也会导致心跳过速的心搏停止。。。。
还不错,我在第一次丝绒左轮儿(VelvetRevolver)的巡演前进行了调整。在那场巡演中,我在绝大部分都是清醒的,清醒到足够和一个乐队一起演出,那些乐迷让我感动之极。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感到过那样的灵感了,我在舞台上四处奔跑,我享受着乐队集体的力量。我的心脏激动地跳动,这让我那台小机器每晚都在启动。虽然依旧不令人愉快,但我渐渐开始能够接受那些暗示了,我开始正视它们。那些奇怪的恍惚的时刻,那些回溯的,浓缩着一生智慧时刻。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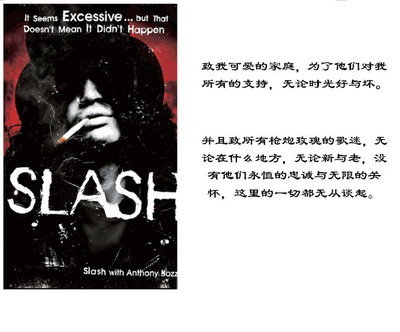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英国特伦河畔斯托克城(Stoke-on-TrentEngland),摩托头”(Motorhead)的莱米·凯尔密斯特(LemmyKilmister)也出生在那里,不过他比我早二十年。那些年正是摇滚乐蓬勃发展的日子,一些特立独行的乐队永远的改变了流行音乐。那一年甲壳虫(TheBeatles)乐队发布了他们的《RubberSoul》专辑,滚石(the Stones)则发布了《Rolling StonesNo.2》,那些正是他们最好的专辑。在那些伟大的专辑中,一些创造的革命酝酿其间,我很高兴也能称得上是那些专辑的副产品。
我妈是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我爸是一个英国白人,他们六十年代在巴黎相遇,堕入爱河并且有了我。他们的交流穿越了人种与洲际的界限,也激发了无限的创造力,我很欣慰他们是那样的人。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经历了那些十分富有、缤纷而独特的环境,这些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当我能站起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父母就开始平等的对待我,他们在飞机上教我如何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当时也就知道那么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爸妈相遇的时候,我的母亲欧拉(Ola)十七岁,我爸托尼(Anthony("Tony"))二十岁。我爸天生是一个画家,就像画家经常会做的那样,他离开了无聊的家乡,来到巴黎找寻他自己。我妈是一个早熟的人,年轻又漂亮,她离开洛杉矶去看看世界的样子,并且希望在时尚界有所发展。当他们的旅行出现交点的时候,他们相爱了,并且在英国结了婚,之后有了我,于是他们开始共同开创新的生活。
在一九六六年左右,我母亲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开始了,在这一时期,她的顾客里面有诸如福利普-威尔森(FlipWilson),林格-斯塔(Ringo Starr)约翰-列侬(JohnLennon)这样的人,其他的还有Pointer Sisters, HelenReddy, Linda Ronstadt, and JamesTaylor等等。西尔维斯特也是她的客户,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他曾作为一名迪斯科明星,就像SLYSTONE一样。他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超级大好人,他给我一个黑白花纹的小老鼠,我叫他米奇(Mickey)。米奇是个混账,当我拿它喂我的蛇的时候,它竟然不害怕!它被我的小弟弟从卧室的窗户扔出去,跌倒地上,而且活了下来,三天后它出现在我们后门的时候,一点儿事没有。还有,当它被我们的沙发的底盘(估计是金属加强物—punk)切掉了一截尾巴的时候,它依然还是幸存了下来。就算基本上一年没喂过吃的和水,它还是活着。。。那是有一次,我们不小心把它留在了一个储物室,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件事,知道后来我们去那间屋子取一些盒子的时候,米奇若无其事的跑过来,就好像我只是离开了一天而已,它当时的样子好像在说,“嘿,你刚才去哪儿了?”
米奇是一个给我留有比较多印象的宠物,其他还有很多,比如我的山地狮子—科提斯,我养过的成百条的蛇等等。基本上来说,我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动物园管理者的料,而且我敢保证,我与我所饲养过的动物的关系,绝对要比大多数我所知道的人要好得多。那些动物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大多数人已经忘记的观点:在最后一刻,生命就是生存。当你了解了这个意义,去赢得那些在野外没准儿会吃掉你的动物的信任,将是一种值得的体验。
在我出生以后不久,我妈回到了洛杉矶去发展她的事业,并且建立了我们家赖以依靠的经济基础。我爸把我交给了他的父母,查理斯和西不里哈德森(Charlesand SybilHudson),大概四年时间,这件事对托尼(slash他爸)来说,很不容易。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有着很强直觉的孩子,不过我还是没太看明白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程度。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他们有着很不好的关系。我爸是三个孩子中中间的那个,他也有着所有排行中间孩子的那种傲慢自负。他的小弟弟,伊恩,和他的大哥大卫,就更加遵从家庭观念。我爸去上了艺术院校,他和他的父亲一丁点儿一样的地方没有。托尼是一个六零后,他一心一意的追随自己的信仰,尽管他的父亲告诉他那整个儿都是错的。我爷爷查理斯是一个斯托克城的消防员,一个一生像流星一样滑过不会想有任何改变的人。绝大多数斯托克城的居民从没没想过离开过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像我的爷爷奶奶,连去一次几百英里外的伦敦的念头都没有过。托尼那种坚定的参加艺术学校、靠画画或者类似的什么而谋生的信念,是查理斯完全不能忍的。他们观念上的冲突经常就演变成大打出手(老子打儿子—punk)。反正据托尼说,查理斯在他青少年时代,随随便便的就把他打得失去意识。
我爷爷是英国五零后的典型人物,而我爸代表的则是六零后(估计这里指的是行为方式,不是出生日期,因为slash本身就60年代生人的---punk)。查理斯就乐意看见所有东西呆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而托尼想的是重新码一遍并且都再漆一遍。我猜想,当我爸从巴黎回来,还带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美国黑人姑娘的时候,我爷爷一定惊了。我正经很想知道我爷爷说了些什么,就是当我爸爸告诉查理斯打算和那个美国姑娘结婚,并且希望他能帮着抚养这个新生的孩子,直到他们的生意上了轨道以后那个时候。
我爸当我刚能坐火车的时候就把我带去了伦敦,当时可能我也就两三岁的样子,但是我好像本能的知道那有多远,从斯托克城有绵延无数英里的褐色砖墙和精致的房屋,到那种波西米亚风格的风景,我想我们很可能许久都不会回去了。那里有蜡烛灯和黑色的灯,在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Road)还有灯火闪耀的货摊和许多的艺术品。我爸从没觉得他自己受了那些影响,但是他的生活模式被不知不觉得渗透了那些元素。好像他自己挑选了那生活方式:爱的冒险、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的在街上流浪,寻找那些充满了有趣人们的栖身之所。我的父母教给我很多,但我很早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没有什么样的生活能像旅途中的生活一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