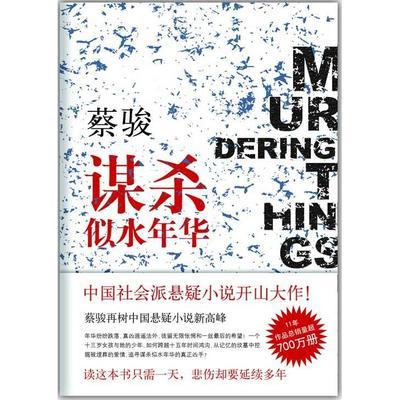[似水年华·转帖]
曾是洛阳花下客
——回忆我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片断(节选)
XueZ.J.
2014年,是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当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毕业四十周年。感谢我队的魏苏豫、程学务和张乖民等同学发起并组织“解放军外院三大队三队同学毕业四十周年母校聚会”,使我再一次有机会回到洛阳,面谢母校培育之恩,追溯昔日同窗之情,回顾青春风华岁月。
命运的眷顾我的人生由此改变
我到外院上学是一件极其偶然和幸运的事,甚至可以说当时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1970年,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令人心酸的年代,全国已经是连续五年没有举行高考了,何时恢复大学教育仍是未知数。那一年,我17岁,参军已近两年,是四川省军区独立一师步兵一团二连九班班长。10月初的一天,连长通知我下午到团部参加一个座谈会,谈谈学习“九大”的体会。主持会议的是团政治处宣传股的股长。他首先介绍了参加座谈会的两位领导,一位是总部的李参谋,一位是军区政治部的王干事,说是下基层听听战士们的学习体会。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总部来的高参,比较拘谨,谁也没有贸然讲话。在宣传股长的再三引导和启发下,我连一班长周彪首先发言,打破了沉默,随后大家陆陆续续发言,气氛渐渐活跃起来。记得那次座谈会上我讲的是,“九大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好全班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外,我还谈了一些争创“四好”班的体会。大家发言时都比较紧张,绝大多数讲四川方言。李参谋和王干事听得十分认真,时不时地做着笔记。他们在总结时称赞大家学习“九大”精神很认真,鼓励我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会后,大家十分激动,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有总部高参出席的座谈会。
几天之后,连长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一班长周彪、文书曾德富和我调到总部工作,接到命令三日内出发。一个连同时选调三名战士去总部机关,在我连甚至我团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一时间全连上下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猜测三人去做什么,怎么选中了这三个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天的座谈会为我们转变角色提供了机遇。事后,我想起了一个细节,那天李参谋看似随意地问过周彪,你是老初二的?我猜想李参谋参加座谈会应该是负有使命的。连长后来对我说,早知道是来调人的,我就不让你们几个都去了。不过他马上又说,这是大的进步,一定要珍惜。我们连长最爱对战士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我到了外院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放暑假时回部队专程看过连长,他告诉我,在我去学校前不久,连里和营里已研究过提拔我为三排排长。虽然我没有机会和我的老营长、老连长一起工作,但我不会忘记他们,是他们的培养和教育铺就了我以后发展的路。
军令如山倒,我们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临出发前,团长栗振武为我们召开欢送会。会上,栗团长说了不少勉励我们的话,希望我们为团争光。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上级通知你们到洛阳报到。不过,据我所知,洛阳没有总部的重要机关。”这更让我们感到这次调动的不寻常了。就这样,我们怀着既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无奈的选择 从五大队到三大队
好消息往往是姗姗来迟。在成都军区第二招待所集合整队时,正当大家相互询问和猜测去向时,李参谋宣布,“经过考察,你们被选调去洛阳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学习,即刻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火车,我们于10月12日到达了目的地——河南洛阳。十月的洛阳,秋高气爽,天空湛蓝,与成都常年潮湿多雾的天气大不一样。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跨入了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代号是总字790部队。进入学校大门,一条平坦笔直的大路展现在眼前,路两旁的杨树高大挺拔,运动场比我们师部的操场大许多,宿舍楼比我们部队营房气派。我被分到五大队一队。
自接受命令由部队到学校,有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一直闪现在我脑海里:我们为什么来?我们为什么能来?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学员没有人能回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渐渐知道,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从全军的基层连队选取200名优秀士兵到外院学习,培养成为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是这些幸运者。
我所在的五大队一队共有100多人,来自全军7个大军区的100多个连队。参加我们座谈会并带领我们一路走来的李参谋叫李家吉,是学校图书馆教员。我至今都十分感激李参谋,他的观察和挑选让我的人生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到校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进行劳动锻炼,随后转入为期半个月的“政治野营”。野营的地点在偃师县寇店公社,离学校大约八十里路,来回都是步行。这点路对于我们在连队摸爬滚打过的战士来说算不了什么。在寇店,我们参加劳动,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接受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进行作风整顿。其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是让我们树立信心,迎接专业学习。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的题词,如:“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不怕难,只怕不干”,“打破难关,光明就在前面”。这些题词我以前在毛主席语录中从未读到过。
政治野营结束回校后的第三天,包括我在内的六个学员被叫到了队部,指导员宣布我们被调到三大队学习英语。我们这几个学员都是1953年或者1954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此后基本没有再上学,直到参军入伍。经过领导的启发教育,我们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当天就去三大队报到了。
1970年11月9日,我们来到了三大队三队。当天下午,队干部就给我们开会,主要内容是亮思想,斗私批修,每个人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一直开到晚上。针对我们的“活思想”,刁贾碧大队长亲自给我们作了总结。他给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什么?二、能不能够学好外语?三、学了以后怎么办?他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地讲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学好外语的信心。
我们到三大队三队报到时,当时只有一个班,称为一班,由从五大队来的学员和从学校警通连来的战士组成,其中来自五大队的有:张金星,杨学平,沈理理,黄国中,张冬柏,高新,张成,阎学剑,曲斌,薛增建;来自学校警通连的有:林根生,候殿元,许兆平,张和万,王大军,穆榜(后来改名为穆育学),李传训,张守瑜。第二天,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又来了白琳,她是我们班唯一的女生,报到那天拎着一个红色水桶。我们班开班时19人,几年中不断有一些人员变化,有进有出,毕业时共有22人。班长是由武汉军区高炮团调来的张金星担任。他为人友善,态度谦和,也很聪明,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的综合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都很好,在校几年长期担任班长,深得同学们的信任。一直到1974年,也就是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们被拆分成两个小班,我到了二班,班长换成了沈理理。在校期间,我分别给张金星、沈理理当过副班长。毕业多年了,同学们现在仍然习惯把我们班称为一班。
……
难忘的第一堂英语课
1970年11月12日,是我们正式上课的日子。教我们第一堂课的是杨荷英教员。课文只有一句话,杨教员在黑板上把它写了下来并大声读给我们听:“Long liveChairmanMao”。她指着黑板对我们说:“我们的英语学习从现在开始,我教你们的这句话,你们要永远留在脑海里。”她先读了三遍作为示范,然后带我们一起读。由于大多数同学从来没有念过英语,所以一开始声音都很小,发出的声音也不整齐。杨教员耐心地启发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是我们每个革命战士心底的愿望,大家这样想,声音就洪亮了,发音就准了。”还说:“毛主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这是全世界人民祝愿的声音,你们一定能念好。”她带领我们反复大声朗读。看到我们有了一些进步后,她又让全班每个同学一个个站起来单独朗读,并给予指导,纠正发音。每个同学读完后,她都大声地说“good”或者“verygood”。来自学校警通连的李传训平日比较腼腆,朗读时声音很小,最后这个“Mao”发音基本听不到,听上去像”Mo”。杨教员让他重复了几遍,效果都没有明显改变,传训自己也很沮丧。杨教员一边讲解示范,一边鼓励,李传训按照正确的方法,连念几遍,不仅声音大了许多,发音也很准了,到后来都不肯坐下还想读。看到李传训进步明显,杨教员及时给予表扬,说:“学习英语就要像李传训这样,敢于大声说,敢于克服困难。大家一起来,带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来读。”她继续带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我们越读越整齐,声音越读越洪亮。杨教员在这堂课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激情,以至于下课时,她红光满面,声音略带嘶哑,在初冬的季节里,额头上都渗出了莹莹汗水。这堂课结束后我们就进入了语音阶段的学习。多年来,杨教员讲第一课时对毛主席的感情,讲课时的激情和认真态度,仍时常萦绕在我的记忆中。
和杨学平同台表演
1971年春节,大队举行迎新春文艺表演,要求各队的节目都要用英文表演。我们队学习英语时间不长,比高一年级的一、二队同学水平差了许多。谁也没有把握能够表演成功。我更没有想到队里会安排我和杨学平说一段对口词。这是我们第一次上台表演节目。虽然心里七上八下,怕砸了台,但领导的信任,还是让我激动。对口台词是乐瑞夫教员写的:
The Sun isred,The Sun is bright,
The Sun is ChairmanMao,The Sun is our party;
We love ChairmanMao,We love our great party.
乐教员为我们亲自把关,并且指出表演时要我们注意的三个要点:一不要紧张,二是发音要清楚、准确,三是两人一起朗诵时一定要同步。他花了很多时间辅导我们,从朗诵台词到相互配合,从发音吐字到上台时的步伐,一一示范,不厌其烦。为了确保质量,我们把课余时间都用于排练。经过五天紧张的排练,我们终于站上了舞台。
我和杨学平自毕业分别后,一直没有再见。得知他转业后去了南京外贸系统,工作十分出色,曾经是南京市最年轻的局级领导干部,后来去了美国。我曾多方打听他的消息,只听说他在纽约。一直到2012年,辗转多人,从同学何小东那里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2012年6月16日,上午9点(纽约时间晚上9点),我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结果老天不负我的期望,果然是杨学平,他不在纽约,而是在洛杉矶。电话中他告诉我就在这天早上,他还在想,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薛增建。我们俩聊到外院的学习生涯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了那次表演,而且都能够把台词背诵下来。这么多年了,白发增添了许多,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情形犹如发生在昨天,永生难忘。
诲人不倦 恩师之情深似海
在学校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先后有十来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乐瑞夫教员。乐教员是上海人,当时也就二十六、七岁左右,白白的国字型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戴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的军装总是平平整整,干干净净,鲜红的领章更是始终像新的一样。他站在讲台上,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从入学到毕业,乐教员一直陪伴着我们,他教的课程包括语音、精读、泛读、听力等,是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乐教员在教学中很注意鼓励我们。有一次他让我们用“tellfrom ”造句。杨学平说:“I can tell it’s a T-34 from the familiar roaringengine”(我能从这熟悉的引擎轰鸣声中判别出这是一辆T-34坦克)。乐教员对他大加赞赏,夸他坦克开的好,更能用实际工作经历的体会来学习英语。乐教员板书写得很好,汉字十分隽秀,英文略带花体,在黑板上写下长长的一串文字,笔直的一行像用尺子量过一样。乐教员还擅长画画,配合上课的内容,在黑板上为我们画出航母、战机等各种插图。有一次上课,他利用我们吃早饭的时间到教室画了一幅画。画面是欧洲地图,在华约成员国与北约成员国的分界线上,骑着线站了一个人,此人双手叉腰,头偏向一边,耳朵特别大,十分夸张地听着什么。乐教员画的画,对我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也起了很大的帮助,如:飞机的起落架,降落时的尾钩,航母的指挥塔,弹射器等等,都是通过他画的图让我们对实物有了立体概念。很多次他上完课后,大家都舍不得把画擦掉。乐教员的歌也唱得好,他教我们合唱《国际歌》、《歌唱祖国》等歌曲,《歌唱祖国》的第一句是:“Seethe five-star red flag flyinghigh……”。全班同学唱得热血沸腾。他时常轻轻哼一些美国歌曲,也个别教我们唱一、两句。我现在记得的有:《老人河》中的:“Oldman river, old man river ,you must know something ,but you saynothing……”;还有《 Home on the range 》中的“give me a home where thebuffalo roam, where the deer and antelopeplay”。后一首的歌词我记在我的日记本里,时间是1974年12月11日,并特别注明:“Taught by TeacherYue”。乐教员提倡读英文原著。有一次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Tracks in the SnowyForest》(《林海雪原》的英译本)。他看到后,摇了摇头说,“对学习英语本身来说,这个帮助不大”,并向我推荐几本英文原著。
1993年,我回到母校去看他,他对我说:“你们这个班,我记忆最深。一个原因你们是我教的第一个班,其次是从头教到尾。”那一次看他,他身体已经很差了,由于有事我到他家已经比较晚了,他拖着病体一直等着我。乐教员因患肝癌于1999年不幸去世,终年55周岁。乐教员英年早逝,我每每想起总觉得十分难过,他的才华和睿智,儒雅的风度,对学生的关心和耐心,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女儿叫乐闻,衷心地希望她生活幸福。
2012年,我无意中在网页上看到有关张培基先生的介绍。我脱口而出,“这是我的老师”。我女儿万分惊讶,“张培基教授教过你啊?”看她一脸十分敬仰的样子,我说,“是的,那时都称教员。”张教员教我们时,已经50岁出头了。他矮矮的个子,黝黑的脸,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一看就是个老学究。讲话时,普通话里夹杂着闽南口音。张教员是真正的大师,他博学多才,当时已有不少的译文和著作发表了,可惜我们对他知之甚少。教学中,他善于循循诱导。有一篇精读课文,题目是“AnApple”,描写上甘岭战士没有水喝,其中一句是:“Lips split, blood oozing out”(嘴唇裂开了,血渗了出来)。他讲这就是独立主格的用法,虽然叫做独立主格结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它还是一种从属分句。让人听得明白。他对英语语言的内涵把握的游刃有余。有一次,他让大家翻译一道题,“薛宝钗体态丰满,林黛玉身材苗条”。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不紧不慢地说,XueBao-cha is on the plump side ,Lin Dai-yu is on the slimside。大家齐声地“哇”了一声,有同学说这也太没有味道了。他说英语的韵味就在这里,看似简单的词组却能表述相当丰富的内涵。后来才知道,张教授是著名的红学翻译大家。张教员十分严格,经常出题考我们。记得有一次考试,我们在埋头苦思,他坐在最后一排的桌子上,双手抱在胸前,两条腿在空中晃荡,说:“难不难啊?”听得出他颇为得意。大家一起叫,“难死了,没讲过的,也出题。”张教员说:“考试做不出来的才会促使你们去学习。学习为什么?学习为考试嘛!”他马上意识到这句话没有突出政治,似有不妥,随后又补充说:“考试为什么?考试为革命!”那时候我觉得他一点不书呆子,反应真快。
再来说说我们队的教研组长陈道芳教员。她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举止十分优雅。她的声音甜美柔润,听她读英语真是一种享受。陈教员给我们上课不多,每次要进行新的阶段学习时,都由她上第一课,对下一阶段学习的重点、难点、总体要求、大致规划,以及要达到的目标,阐述得十分清楚明了。她很注意听取学员的建议和意见,每个学期的评教评学活动,她都一个班一个班地听,尤其重视收集教员的讲课情况和对教材的修改意见。有一次,陈教员给我们代课,课文是《EscapefromVientiane》(逃离万象)。陈教员对我们说,“精读的课文都是教研组精心编写的,你们要尽最大努力背诵课文。”在一次课堂上,张教员要求翻译“大街上除了‘咔嗒’‘咔嗒’沉重的军靴声音,一片寂静。”高新被点名回答,高新抑扬顿挫地答道:“Thestree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clop’ ’clop’ of heavy militaryboots.”张教员对高新大加称赞。其实这个句子就是那篇课文里的。陈教员和曾肯干等教员编写的教材,可谓费尽心思。那时,所编写的课文,既要按照进度满足语言训练的需要,更要突出政治,反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实属不易。记得我们的精读课文有:《AKoreanGirl》,《An Apple》,《The Wooden Gun》等等,这些课文对我们学好英语起了很大的作用。读课文收了不少原著,如《Operation Overflight》,《Second inCommand》,《G.I.Joe》等。MarkTwin的作品特别受欢迎。那时候没有版权问题,教材都是学校自己印刷,封面不是蓝色的,就是白色的。泛读课文中有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是,“Thelesson is over. You aredismissed."多年后才知道这是法国大文豪都德的《最后一课》。教材还选编了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的《回忆录》(Memoirs1925-1950 George F.Kennan)的部分章节,我曾经反复阅读其中德军突袭捷克时,美国大使馆应对活动的有关内容。我对乔治.凯南能写出如此翔实流畅,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十分钦佩。
曾肯干教员是湖南人,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战俘营里工作过,担任翻译。他的口语非常好,还掌握大量的英语俚语。他在讲课中经常引用美军的一些习惯用语,让我们获益匪浅。曾教员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学特别耐心,循循善诱。我们班一个同学原来是个炊事员,学习非常努力,但他的方言很重,在英语发音中也夹带着地方方言,且难以纠正,这让他抬不起头,多次流露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还想回去掌大勺。曾教员耐心地帮助他,经常在课下辅导他,帮他找回了学习的自信。我们班的张成,非常聪明,学习轻轻松松,一点就通,规定的教材他掌握得非常快,考试成绩每次都名列前茅。他经常到图书馆借书看,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教员对他有时上课看课外书有意见。曾教员很肯定张成的学习潜能,鼓励他多读,多思;也提醒他要注意场合,把握好课内外学习内容的关系。张成毕业后是同学中最早晋升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和最早担任科长的人之一。
海澄波教员教我们汉语言文学课。海教员身材不高,头发略微花白,讲课时中气十足。海教员讲课很生动,尤其是讲人物,她讲过的祥林嫂,侯小手,“皮袍下的小”,至今令我们不少同学都难以忘怀。她讲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时,就指着自己的头发说“大概如此”。她讲到毛主席评价鲁迅先生“会杀回马枪时”,就在讲台上比划双手握枪,往前急趋几步,然后突然一个急转身,右手用力刺出去,左手向上伸展开,做出一个恰似京剧亮相的动作,说,“这就是回马枪。”海教员不时要求我们写作文,对我们的作文,批改十分认真,好的作文她会在讲台上充分肯定,有缺陷的文章她也会指出不当之处。她曾对我暑假期间的一篇作文批了长长的一段话:“既然前面讲了‘太阳把人晒得毛焦皮燥’,后面却又说,‘热得我大汗淋漓’,这是前后表述矛盾;引用方言要加注释,你用的‘安逸’这个词,没有到过四川的人,就不懂得你此处是要表达‘舒服’这个意思”。她的这段批语,使我受益匪浅。
姚乃强教员教我们《美国概况》。他讲课条理分明,语言生动,讲到激情时,普通话、上海方言、英语一起上,令人捧腹。他很擅长用“三”来归纳,如:美国政治是三权分立:立法、司法和行政;经济有三大支柱产业:钢铁、建筑和汽车制造;人口构成是三大主要人种:白人、黑人和印地安人;地理有三大山脉:东部有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落基山脉、西部有内华达山脉;三大河流:密西西比河、康涅狄格河和赫得森河。姚教员的归纳方法让我受益很大,我后来讲话也喜欢讲三点,多一点人家烦,少一点显得自己没水平。那时讲这种课很难,因为有政治标准来衡量。所以姚教员讲过,美国有三个党欺压人民:共和党、民主党、三K党;美军的特点:政治反动,武器先进,士气低落。我那时对美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对美国的50个州的州名和州府名可以做到张嘴即来,幻想着有一天能去美国,看看美国,特别想去美海军基地,亲眼见见美军的先进武器以及报纸、广播里宣传的“一打仗就投降”的美军长什么样。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很幼稚,但在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年代,非常符合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
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教过我们的还有陈怀杰教员、陈树裕教员、张朝宜教员、韩振荣教员、吴苹教员、吴长镛教员、毛培君教员、吴用可教员、潘永梁教员、周冠德教员、吴晓梅教员,以及背后默默为我们付出辛勤汗水的许许多多喊不出他们名字的教员,是他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的恩情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学校,教员们负责我们的专业学习,队长、指导员负责我们的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他们也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尹家发指导员个子不高,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是一圈一圈的,讲话带有明显的苏北口音。尹指导员待我们学员很平等,也很和蔼,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1971年初春,队里召开军人大会,主题是征求对队领导的意见。有些同学(包括我)也提了一些建议意见。尹指导员认为学员的意见都是善意的,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作为领导,应该虚怀若谷,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他从不整人,对学员的不足,他总是个别谈心,循循善诱,耐心做思想工作。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1970年底,我们开课不久,我班同学小J到五大队偷偷拿了人家的存折(存折上有10元存款,相当于一个半月的津贴),犯了严重错误。事后,队里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不时对小J讽刺挖苦,拍桌子瞪眼,在会下还用脏话辱骂他。有一天深夜,我听见小J被窝里传出抑制不住的“呜呜”哭声。尹指导员发现了这个情况,坚决制止了我们这种错误做法,并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他对我说:“你身为副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我现在回想起对小J做过的事,感觉十分内疚。尹指导员带了我们一年左右就调到了四队,令人十分怀念。2013年7月18日,年近七旬的尹指导员从上海到北京。得知消息后,张成、白琳夫妇和高利宁组织了同学们欢迎他,还请到了陈道芳教员和她的老伴刘基法政委。那天,在京的同学几乎悉数参加,共来了20多人。张金星、王玉仙、鲁路群、项建平等同学还冒着酷暑分别从河北和天津专程赶到北京看望老领导。聚会期间,李力、叶京辰在网上传了大量照片,让我们在各地的同学都能实时看到老领导的风采。
尹家发指导员调走后,张建生担任我队的指导员,一直到我们毕业。张指导员的个子有1.78米,体型较瘦,十分精干。他管理水平很高,各项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除了上课,别的时间他几乎都和我们学员在一起。他的小孩那时候刚出生,他基本顾不上,全交给他的爱人罗老师。张指导员各项运动都很在行,尤其是足球。他踢前锋,速度很快,过人时上身晃动,脚下盘带,假动作十分逼真,我们两、三个人都看不住他。他要求我们很严,也很能以身作则,无论是出操训练,还是劳动锻炼,他都走在前面。当时担任我的队领导的还有:王金兴队长、杨永龙副队长和刘载宗副指导员。他们对我们这些学员倾注很多的关爱和心血。从思想教育到政治进步,从专业学习到全面发展,他们帮助我们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发生在食堂里的那些人和事
学员食堂位于学校图书馆的东西两侧,是红砖建筑的平房,十分厚重结实。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厨房,还有配套的地窖、储藏间和堆煤的场地。餐厅有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摆了十五、六张饭桌。饭桌是八仙桌式的方桌,四条长板凳,每桌可坐八个人。
为了保障我们的学习,队领导下了很大功夫搞好食堂。我们的伙食标准每天是5角5分钱,算是比较好的了。那时每天都要吃小米,比如小米粥,小米发糕,小米饭,有时把大米和小米掺合在一起,做成“二米饭”。有些南方来的学员对小米饭难以下咽,似乎比吃药还难受,幸好每天有一顿大米饭,才能让他们“大快朵颐”。海军班的一个同学第一次看到“二米饭”时说,学校的伙食不错嘛,还有鸡蛋炒饭,就盛了满满一大碗,结果一吃,咽不下去,他以前连小米见都没有见过。食堂的小饭车是用木头做成的小箱子,饭放在里面,保暖。小车两面都有把手,方便拉动,一圈可以围上十来个人同时盛饭。若是馒头、包子之类的面食,笼屉就直接放在小箱子上面。有一次劳动回来,大家都很饿了,晚饭是肉包子,男同学们一拥而上,围着小车抓包子。一个同学把笼屉向自己这边拉,车对面的另一个同学则拉住小车的把手拖过去。两边都在使劲,结果小车是被拉过去了,一边的笼屉把手还攥在这边同学的手里,剩在笼屉上的一些包子“哗啦啦”扣在地上,食堂里顿时一片寂静。争抢的那两个同学站在那里颇为尴尬。后来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王队长和炊事班的同志把地上的包子检了起来,又重新下了一锅挂面给大家。那顿饭食堂里静悄悄地,一个个像做错事的孩子,埋头吃饭,没人出声。后来听说掉在地上的包子,被曹修成司务长和炊事班的同志把脏的外皮剥去后吃掉了。为此,队里进行了专题教育。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在部队吃饭有其特色。每次吃饭全队集合整队前往,路上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到食堂门口,还要合唱一支歌,才能就餐。集体唱歌通常由鲁路群担任指挥,他的动作刚劲有力,节拍分明,有“指挥家”的风范。吃饭过程中,各班经常会朗读一些短小精悍的稿子,表扬好人好事。游凤岭写的穆榜劳动受伤的表扬稿,在食堂宣扬后,还被学校广播室采用了。
1973年2月2日,是农历的大年三十,我和沈理理、张冬柏三人早上被派到食堂帮厨。凌晨的5点半,天蒙蒙亮,北风呼呼吹,校园内一片寂静。我们三人到了厨房,在两名炊事员的指导下,干了起来。我在冰冷刺骨的水中洗笼屉,油腻腻的蒸笼,怎么也洗不干净,手却被冻得麻木了。揉面团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也没揉软。炊事班长体贴地说,去烧火吧!等做好早饭时,觉得腰都快断了,累得不想吃。那一次帮厨后,真的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温暖我心的蜂窝煤炉
洛阳地处黄河南岸,冬天大约从11月下旬开始,到次年的3月初入春。在三个多月的冬季里,气候干燥,风大、天冷,南方来的同学尤其感到不适应。有些女生每年都要生冻疮,夏维的冻疮甚至长到了脸上和耳朵上。白天在教室上课还好,有暖气。晚上回到宿舍,就只有靠煤炉来取暖。每个宿舍有一个烧蜂窝煤的煤炉,上面有一个烟筒通到窗户外面。每个班配发一定数量的蜂窝煤饼。不要小看这烧蜂窝煤,那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因为晚上睡觉时,为防止煤气中毒,必须把上面的盖子盖上,下面的风门要开一些,以便让煤气从烟筒里排出去。下面的风门如果开大了,煤饼很快会烧完;下面的风门如果开小了,煤饼没有足够的氧气,很快会熄灭。这两种情况都导致后半夜整宿舍的人被冻醒。黄国中对烧炉技术掌握的可谓是炉火纯青,每天晚上封炉子的活儿都是由他来完成。别人向他讨教,他总是嘿嘿一笑,从不将技巧告诉别人。有时候煤饼的质量不行,他夜里还要起来加煤,调整风门。每天的炉灰清理,也基本是他来完成。别的班的炉子灭了,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取火,但是取走一块燃烧的煤饼,必须用两块新煤饼来交换。可见,那时,我们班的同学就有商品经济头脑了。国中对煤饼的管理很细致,使用也很有计划性,每天烧几块,烧到什么时候,他都心中有数。甚至哪个班来“偷”煤,他都知道。在洛阳的四年,每个冬天,我们班的炉子从来不灭,宿舍里总是温暖如春,而且没发生过任何事故,那种温暖感,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洋洋的。
“阿波罗”带我走进神奇太空
1971年,学校放映有关“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的纪录片,这是我第一次观看美国的原版片。内容基本没听懂,只觉得很震撼,很新奇,尤其是看到代号为“土星5号”的火箭升空和Armstrong登上月球表面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同学在看电影的时候问乐教员:“阿波罗今年多大年纪了?”乐教员不解地问他:“什么意思?”那个同学很认真地说:“我在想,阿波罗如果年纪大了,登月不是有困难吗?”乐教员于是给他解释,阿波罗不是人,是古希腊的太阳神,美国人把它用于登月飞船代号。那个同学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正是通过这个影片,我了解了太空的神秘,科学的伟大。我相信凭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走向太空,探索宇宙,造福人类。现在,我们飞船早已上天,坐在家里就可以观看我国的宇航员翱翔太空的场景了。
瑕疵 衬托了我平凡的人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处于青春骚动的我们,难免会犯一些过错。这些瑕疵,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部分,它构成了我们平凡而又完整的人生。
学校边有一片苹果园,周围用土墙和铁丝网围着,有时我们会被安排去果园劳动。每年到了苹果成熟的季节,我们都要学习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这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队领队也教育大家不能私自去摘苹果。但是,苹果的诱惑力确实太大了。一个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熄灯以后偷偷地溜出了宿舍,从一处白天已经看好的土墙豁口跳进了苹果园。一进苹果园,我们就分散开来,手忙脚乱地开始摘苹果。天黑沉沉的,看不清,心怦怦地跳,直流汗。一刮风,树叶沙沙地响,我们就疑心是有人来。转了一圈,我们发现伸手够得着的的地方,苹果已经不多了。好不容易摘满了各自的挎包,我们迅速从原路撤回。到土墙豁口,正准备翻墙出去时,忽然从墙外“通!通!”跳进两个人来。双方都没有准备,几乎脸贴脸打了个照面,一刹那,大家都愣在那里了。借着月光,我一眼看出了他们是一队的学员,与此同时他们也认出了我们。大家彼此会心地点了个头,就各自分开了。挎包里的苹果,不敢带回宿舍,我们就找了个地方开吃。刚开始觉得非常香甜,渐渐吃不动了,最后吃的太撑了,整晚上都没有睡好。自那以后,我对苹果就有点望而生畏了。也算是对我那次行为的惩罚吧。
好吃是人的本性。那时,食品不丰富,肚子里的油水也很少,总想着搞一点好吃的打打牙祭。我和一个同学借帮厨的机会偷偷拿回食堂的鸡蛋,放在宿舍的炉子上煮着吃。那时候鸡蛋是稀罕食品,要生病吃病号饭,才能有一个鸡蛋。不过,到厨房干活的机会非常少,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偷吃的。后来在工作中,我对下属的小毛病都宽容,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大概也能从我的这次过错中找到缘由。
学校的作息制度很严格。熄灯号后不得讲话,起床号响起必须立即起床。毕业那年开始放松自己,早上起床号响后,有时装着听不见,任凭张金星叫“Getup,“Getup”,就是懒得下床。有时,我们也想着捉弄一下人,寻寻乐。有天晚上熄灯号响以前,我们把门虚掩上,在门上放了一个脸盆,装了半盆水。熄灯号响后,我们故意大声说话。某队干部不知有诈,进来批评我们,刚一推门那盆连同水一起砸了下来,淋了队干部一身,有几个人捂住被子都笑出声来。尽管我们几个被小小的惩罚了,但这次恶作剧让我们开心了好长时间。
我接的学生圆了我的“将军梦”
1974年的10月,离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和杨学平、沈理理、钟嘉铭以及黄国中,坐在大操场的草地上聊天。当谈到未来的打算时,我脱口而出:“六十岁时当军长,挂少将衔,遂平生之愿。”此话一出,语惊四座,钟嘉铭拍手称好。要知道当年我军取消军衔制已近十年了。我至今都记得当时说此话时的满怀豪情。
步入工作岗位后,随着时光的流逝,知道将军梦真的只是一个梦了,甚至连梦都称不上,因为从未梦到过当将军。但我离开部队十五年后,我的将军梦被我接来的学生实现了。严格来说,这段故事已经不是在外院期间发生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记录在此,与大家分享:
1982年7月,我们刚移防到湖北南漳不久,张耀勇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成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选拔一个应届毕业生。我到了科大后,校方说,“解放军来挑选毕业生,我们十分重视,已经提前做了准备,你们的指标是一个人,我们为你准备了三个预选对象,都是思想好、成绩好的优秀学生。”随即把名单和档案给了我。名单第一个是一位女同学,名字我忘记了,然后是张绍国、冉崇伟。三个人都是四川人,冉崇伟是四川省巫溪县人。十分凑巧,我的父亲曾在巫溪县当过武装部副部长、革委会副主任。我看过后,当即表态,部队常年担负战备任务,女同志可能胜任不了,我在两个男同学中选一个。他们的档案很简单,照片看上去都很精神。我把他们在校四年的各科成绩全部抄下来,做了统计对比,发现两个人难分伯仲,张绍国有一门成绩略高过冉崇伟。我内心倾向于张绍国,除去成绩这个小小的因素外,张绍国的外语课是英语,成绩是“优”,而小冉学习的是日语。我与系里领导商量后,与张绍国进行了面谈。我问了他学习的情况,家庭关系,本人的特长等相关问题。在谈话中,小张可能出于紧张,说话磕磕巴巴,叙事条理不清,与我的想法相距甚远。我有意识地问他“我今年20岁,英语怎么说?”他更紧张了,汗也流出来了,解释说:“我们学的是科技英语,口语基本没有练过。”小张不是理想人选,我勉励了小张几句,希望他服从组织的分配。随后我找到系领导,要求与冉崇伟谈话。系里不同意,说你跟学生见了面,就意味着你已经同意接收了,再换人,我们无法对学生本人交代,在同学中影响也不好。我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系里介绍的情况不够准确,比如档案中他的英语成绩是“优”,实际他连“我今年20岁”这样的句子都翻译不出来,怎么可能达到部队的要求呢?于是我顺理成章地与冉崇伟见了面,谈了几句话后,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理想人选,我要把他带走。但随后发生的情况令我十分头疼,小冉不愿意去部队,他想留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当老师。我用了很多时间来说服他,“我们有个很大的训练大队,培训的都是干部学员,你的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大有用武之地;部队驻地离武汉很近,条件很好;你一到部队就定为干部”,等等。现在看来,我是在“忽悠”人家。我还把小冉请到家里,让我爸爸帮助做工作。小冉的爸爸叫冉瑞禄,是巫溪县人民医院的院长,与我爸爸相识。经过一天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小冉同意到部队了。我立即到学校签了接收协议。为防止节外生枝,我为小冉买好了去襄樊的火车票,让他先去部队报到,然后再探家。小冉走后,我到成都科技大学向校领导表示感谢,又遇见了张绍国。小张拉着我的手说,“薛参谋,我好‘瓜’喔,‘Iamtwenty’我都搞忘了。”“瓜”在四川话中是“傻”的意思。我只好对他进行鼓励。现在想想,应该跟学校商量,把两个同学都接走。
小冉到了部队后,凭着他的天分和努力,成了业务尖子,后来又进修了硕士,博士,多次立功,获得军队最高等级的科技进步奖,当上了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他不到五十岁时,晋升为专业技术少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出类拔萃的中青年专家。我没有当上将军,我却招来了一个当上将军的学生。这是我在军队二十八年中唯一一次去选拔学生。
弹指一挥间 依依惜别四十年
1974年夏天,三班的同学要毕业了。他们都是某局来代训的,毕业后要回原单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教学楼,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教室里十分安静。三班的教室门虚掩着,我从门缝往里瞥了一眼,看见韩江鸣在黑板上写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每个字都有人的脸那么大。我没有惊动她,怕扰乱了她的思绪,轻轻地走开了。
1974年12月24日,队领导宣布了分配方案,在前一天,大队领导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然后我们照了毕业合影。先是全队在一起照,接着分班照。赖石昂校长、陈亚夫政委也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1974年12月27日,我们离开了学校,时间是晚上8点钟。天已经完全黑了,北风呼呼地吹。每个人的行李都十分简单,除了一个背包,就是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的是书籍、课本和杂物。队领导、教员和还没有离校的同学都来送我们。有人相互拉着手,有人在啜泣。等到大家都登上车后,我说了一句,来跟大家告个别吧。吴燕明扒着车后箱板对着沈理理说,“班长,让我再叫你一次班长吧”,立刻引来了车上车下的一片哭声。在1974年那个冬季,我们告别了母校,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那一年,我21岁。这一别,如今我们再聚首,已经是四十年后的今天了。当年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我们,而今,大多已从各自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尽享天伦之乐。
后记:绵绵不断的情缘
我们分别四十年后能重新在母校欢聚,四班的魏苏豫起了重要作用。2001年1月26日,苏豫在搜狐网上创建了三大队三队海军班的群网。2012年3月6日,他和卫晓东在QQ上建立了三大队三队的群。他像一个忠实的灯塔守护者,十三年来始终用光柱来呼唤着战友;他像一根金色的丝线,把同学们穿在一起,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四十年后,我们重新回到母校的怀抱里,徜徉在盛开的鲜花丛中,回顾着曾经的青春年华,倾诉着外院生涯结下的深厚友情,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衷心地祝福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我的同学,我的校友幸福安康。在此借用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诗句,作为我的文章结尾,我们“曾是洛阳花下客”,情缘绵绵无尽期。
——写于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作者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70级学员,现在上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