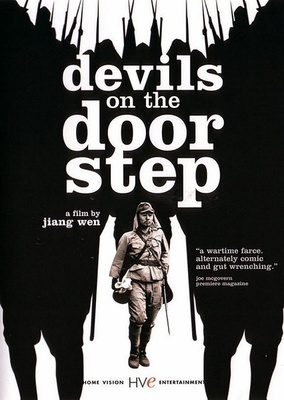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不肯用手机的女孩。
从2003年到2013年,从拉萨到丽江,我再没遇见过她这样的女孩。
1、背起手鼓去珠峰
初次见她是在蜗牛的酒吧,我喝多了青稞酒,去讨白开水。拉萨晚秋的夜已经很凉了,她依然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酷酷地抽着大前门。锡纸烫过的头发,包头的线帽,长得象极了瞿颖。那时候开往拉萨的火车还未开通,混在拉萨的女孩子们还都像是爷们儿一样的,一水儿的登山鞋。她却穿着带跟儿的小皮靴子,看起来很神气。
不熟,没怎么说话,一起坐在吧台边吸溜着喝白开水。蜗牛裹着毯子在吧台里吸溜,我抄着手趴在吧台上吸溜,她背靠吧台双手捧着大杯子吸溜。三个人用此起彼伏的吸溜声来打发午夜时间。
第二次遇见她是在藏医院路口。她给一个英国作家当临时翻译,满世界采访混在拉萨的人们。她冲我抿着嘴笑,抬起手做了个喝水的姿势。
我说:“唉,那个谁,留个手机号码给我,回头一起吃饭。”
她扭头和那个英国作家说:“你看,我还是蛮有市场的”。那个穿着雪白衬衫的威尔士女人挑剔地打量了我一眼,矜持地歪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
我心说你丫矜持个蛋啊,我又不是要请你吃饭,你腰那么粗,和头小牛似的……
我和她说:“快点快点,手机号给我。你的老板快要拿大蓝眼珠子瞪死我了。”
她跟我说:“抱歉啦,我没有手机也不用手机,要不然你把你的手机送给我。”
我舍不得我的手机,那个爱立信大鲨鱼是我唯一的家用电器,于是我就很没脸地走开了。
已经是入夜光景了,那段时间治安很差有人被打劫。走之前,我把随身带的英吉沙短刀借给了她,也没怎么多话,只是叮嘱了她,这个点儿有几条巷子最好别去。
天地良心我真没有想泡她的意思,就是想和她这样漂漂亮亮的小姑娘聊聊天扯扯淡吃吃饭什么的而已。我那时候是个五讲四美文明礼貌又单纯又感性还很随和的文艺小青年儿。
第三次见面是一周以后,她半夜来我的酒吧听歌。进门就窝进卡垫儿里,木木呆呆地一个人出神。我唱了一会儿歌,抬头看她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瓶酒开始喝酒。她失魂落魄,看也没看我一眼,所以我也没管她,继续唱我的歌。我唱了一首郑智化的《冬天怎么过》,唱完了以后瞅瞅她,她缩成一团靠在卡垫上,低着头,一点声音也不出,像睡着了一样。
我走过去戳戳她,发现泪水浸湿了她整个膝盖。她原来在安静地,哗哗地流眼泪。
这是怎么个情况?这首《冬季怎么过》,没什么毛病啊,怎么就把人家给惹哭了啊?这可如何是好。
【冬季怎么过】
冬季怎么过
在心里生把火
冬季怎么过
单身的被窝
冬季来临的时候
我总是想到我
明天是否依然
一个人生活
……
我蹲下来,说:“这个季节来混拉萨的谁没点儿故事,不管你有多坎坷,也没必要让别人看到你哭成这个熊样儿哦。”
……我觉着我挺会说话的一个人啊,怎么话一说完就把人家整哭了呢。
我想逗逗她,让她笑一下,别哭出个高原反应什么的最后死在我酒吧,就用话剧腔说:“朱丽叶,在秋天是没人会帮你擦去冬天的眼泪的。”
她埋着头说:“嗯嗯嗯……”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就是有一点小难受,慢慢就好了呢……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我回头看看酒吧里,一桌北欧穷老外已经彻底喝大了,头对头趴在桌子上淌口水,一桌是两个老房子着火的中年背包客,四目相对浓情蜜意呢喃不休,完全沉浸在二人世界。
我说:“好吧,我挺乐意陪你出去走走的,但你要把眼泪抹抹鼻子擤擤,不然一会儿出去了别人还以为我怎么招你了似的。”
我一边忙活着穿外套一边问她:“说吧,咱们去哪儿?”
我琢磨着公账不能动,但钱包里还有50多块,要不然就出次血带她去宇拓路吃个烤羊蹄儿吧。不是有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格言么:女人难过的时候,要不带她逛逛街买买东西,要不就喂她吃点儿食儿。反正看她这小细胳膊小细腰也吃不了多少……
她泪汪汪抬起头,说:“……去个比拉萨再远一点的地方。”
我一下子就乐了。
怎么个意思这是?演偶像剧呢?
我说好啊!我随手在身后的丝绸大藏区地图上一点,说:“您觉着去这儿怎么样?”我回头顺着手臂一看,手指点着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
她目光渺茫地看着地图上那一点,然后点点头说:“走”。
那就走呗。
她用力裹紧衣服,推开门走进拉萨深秋明亮的午夜。
我把手鼓背起来,想了想又放下了……最后还是背着出门了。
……
一个半小时后,我开始后悔。
这时,我们已经横穿出了拉萨城,沿着河谷走在国道上了。拉萨城的灯火早已被抛到了身后,眼前只有黑漆漆的山和一条被月光照得发白发光的路,河一样地绵延曲折没有尽头。
我心想坏了,看来这小姑娘是玩儿真的。然后我开始心痛那两桌注定跑单的客人。早知道就该先收钱再上酒,那桌北欧退伍兵指定是要在酒吧睡到天亮了,保不齐明天睡醒了以后他们就会自己跑到吧台自己开酒胡喝……我唯一那瓶为了撑门面才摆出来的瓷瓶派斯顿金色礼炮威士忌肯定保不住了,还有我自己都没舍得吃的新疆大葡萄干,都他妈便宜那帮维京海盗了……
不一会儿天就亮了,我实在是累了,赖在路边呼哧呼哧喘粗气。
开始,有一辆辆车路过我们身边,卷起一阵阵汽油味的风。我又冷又饿,掏了半天裤兜掏出来一块儿阿尔卑斯奶糖,立马飞快地偷偷塞进嘴里。一抬头,她没人事儿一样默默站在旁边看着我。
我瞅着她的鞋,说:“哎呦,厉害啊你,穿个小靴子还能走这么远。你属藏羚羊的啊你。”
我逗她,她也不接茬,只是拿鞋尖踢地上的石子,踢了一会儿自己跑到路边儿,伸出一只胳膊开始拦顺风车。她有个美丽的背影,修长的腿,纤细的脖颈和腰,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嚼着糖看着她拦车,心说厉害啊,技术娴熟经验老道,看来是个拦顺风车的老手。
没过一会儿,我们搭上了一辆开向后藏方向的中巴车。开车的是藏族人,满车都是藏族人。我挤在一个老人家旁边,老人家一身的羊肉味,和所有的藏族老人一样,不停转着手里那个长经筒。车每次一转弯,她手里转经筒的坠子就狠狠扇在我腮帮子上,我给扇急了,又不好和老人家发火,只好每被扇一次就大喊一声:丹玛泽左(丹玛泽左是呼神护卫佑持的意思)。
我每喊一次,老人家就笑笑地看我一眼,后来还伸过一只手来摸摸我的脸,说:“哦,好孩子。”
她这时终于有了一点儿笑容,她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出点儿躲避流星锤的空间。我紧贴着她坐着,心说这姑娘怎么这么瘦,隔着衣服都感觉骨头硌人。我想起一件事情,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玩儿着手指,说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说。
我说,好吧。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小名儿叫什么?”
她说:“我说了,别问了。”
她左右望望,然后把目光放在了车外。
我说:“OK,我不问了……那您老人家怎么称呼。”
她恶狠狠地叹了一口气……
旁边的老人家笑笑地摇着转经筒,我腆着脸搭讪。我说:“阿尼,名热卡?”(老人家您怎么称呼?)
老人家示意我等一下再说话,然后很神奇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吱吱响着的手机,开始接电话。
我捅捅她,说:“你看你看你连个手机都没有,连人家老阿尼都用手机。还是诺基亚”。
按理说她应该和我解释一下她不用手机的原因,但她没有。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原因。
就这样,我在二十浪荡岁时,跟着一个不肯说名字也不肯用手机的女人,一路颠簸,从拉萨去往珠峰的方向。
2、羊卓雍措的鱼
事实上没在车上颠簸多久,我们到了羊湖就被抛弃了。
这事儿说起来该怪我,说实话又不是第一次来羊湖,可那天羊卓雍措湖太美了,我之前和之后都没见过这么美的羊卓雍措。趁着司机停车,大家下车方便的空档,我拽上她就往湖边走。
藏地三大圣湖,纳木措、玛旁雍措和羊卓雍措。我差点把半条命丢在纳木措边。纳木错是神圣的,玛旁雍错是神秘的,至于羊卓雍措,于我而言是美丽而神奇的。
这是句废话,去过羊湖且双目健全的人没人会说羊湖不美。
那天的羊湖雾气缭绕,美得和假的似的,比大明湖美多了,比喀纳斯湖美多了,比雨西湖美多了。那不是水,是一整块儿大的要命的玉石,幽幽的碧色静止的水面,水面静止得让你觉得这哪儿是液体啊,简直就是固体。人要一直走到离湖面快五六米的地方,才能看到微风吹皱的一点点儿涟漪,微微颤颤的,那湖水像是有弹性的。
我和她说,今天这湖怎么和一大碗猕猴桃果冻一样?简直可以拿个大勺子挖着吃喽。
她啧啧感慨着,我也啧啧感慨着。
我们就站在湖边啧啧感慨着,感慨了很久。羊湖是神湖,我跪在湖边磕了长头,祈祷羊卓雍措达钦姆大湖主保佑我接下来一路平安别出车祸,零件完好地到珠峰。然后,我们踩着石头往回走,这时候才发现,坏了,车跑了。
所以说羊卓雍措真的是个法力无边的神湖,我只不过祈祷别出车祸,人家羊卓雍措达钦姆大湖主很负责任地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直接把车给我弄没了。
车上的人应该喊过我们,估计是我们走得太远又站在水边,所以没听到。现在就是想让老人家的转经筒扇我也扇不着了。
我说:“怎么办,我饿了”。
她指指羊卓雍措说:“吃吧,果冻。”
后来,沿着湖边走了一会儿,看见一个新开的小饭铺,专门卖鱼的小饭铺。我俩绕着铺子转了一圈又开始啧啧称奇。羊湖是神湖,藏民把所有的鱼都当成龙王的子孙,从来不吃,所以不论里面的高原裸鲤多么肥美也没人煮它们。藏地原住民不吃鱼是个基本常识,这家小鱼馆儿的出现让我们很惊奇。
我咽着口水说:“你看,这棚子连扇玻璃窗都没有,肯定是怕不吃鱼的信徒来砸。”
烧鱼的味道飘出来,她也开始咽口水。
我说:“你吃吗?”
她摇摇头说:“你不吃我就不吃。”
……
我说:“那我……吃不吃?”
她说:“好吧,那咱赶路吧。”
恩公!不吃鱼,咱炒个菜吃也行啊,下个面条吃也行啊,谁知道前面还有没有饭店了,难道还要绕着湖跑到南岸桑丁寺去找女活佛化斋不成?
我拽着她进屋坐下,其实算不上屋只是个棚子,紧挨着就是厨房。我在油腻腻的桌子上给她画了个羊卓雍措的环湖路线图,给她讲,如果我们去桑丁寺找食儿吃的话,大约会饿死在哪个位置。我说你看,羊卓雍措是个蝎子形的湖……
厨师兼服务员过来点单,一口川普:“朋友,你们打算来条几斤的鱼?”
我说:“我们不吃鱼,来两碗面条就好。”
服务员掐着腰说:“哦,吃鱼的话,面条5块钱一碗。不吃鱼的话面条20一碗。”
……你个天杀的!抢钱啊!
我吃完面条后,很想把面碗一起带走,她把我拦住了。付完面钱,我身上只有10块钱了,那个服务员坏,找了我一张五块的,剩下的都是一毛一毛的。看起来厚厚一沓很富有的样子,闻起来一股子生鱼腥味儿。她很客气地说:“你身上味儿太大了,走路的时候离我远一点点可以吗?”
我很委屈,我说你刚刚才吃了我一碗面!做人怎么能这么没有节操?
她很迅速地把四个口袋都翻过来,翻出来一块儿口香糖,一串钥匙,一本护照证件夹,一个小卡片相机,还有我那把短英吉沙……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真心佩服她,我说:“且不说你一分钱都没有就拽着我去珠峰,单说昨天晚上你怎么就敢一分钱都不带,跑到我酒吧里去喝酒,你就不怕付不起酒钱被我把相机给砸了?”
我想翻翻她的护照,她打死不让翻。
我跑到路对面摆了好多POSS让她给我拍照片,她假装拍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其实只拍了一张。
后来,羊卓雍措水边的小鱼馆有了窗户,还有了永固的四面墙壁,专门招待专程来吃高原裸鲤的游客。再后来,一度有一个传言,说羊湖上了观光游艇项目,还要在湖边设置200多个遮阳伞、沙滩椅供游客休息……也不知道最终到底叫停了没有。
3、日喀则的头花儿
千辛万苦,走去日喀则。
我们从羊湖开始拦车,边走边拦。汉族司机看到我们是两个没背行李的徒步者,根本就不停车。快走死了才拦到一辆藏族人的车,开了没多久就把我们撂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岔路边。继续接着走,人走得热气腾腾大汗淋漓,被风一吹立马冷得想蜕皮。我把手鼓扛着,甩着手臂走,她缩着肩膀走。
这姑娘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踢东西,她经常一边踢着路边石子一边走,像个皮孩子。
途中,我们在路旁的藏族村子里借宿过一晚。她摘下包头的帽子后,女主人很稀罕地摸着她的锡纸烫,很惊喜地说:“哎呀,羊毛一样。”说完又拍拍我的手鼓,很开心地说,“哎呀……响的呦。”
大姐,手鼓不响还叫手鼓吗?
她和女主人拉姆睡在一起,我和男主人才让丹喝了一晚上酒。才让丹喝高了以后张嘴说的全是藏语,一边说话一边大巴掌拍我后背。我会的藏语单词实在有限,只能一个劲儿应和:“欧呀!……欧呀!(是的)”我心里面琢磨,这伙计怎么和我们胶东老家的大老爷们儿一个德行,喝完了酒就爱拍人。但我们老家人不拍人后背,只拍大腿。
早知道那是我们一路上住得最舒服的一个夜晚,我就该讨点热水洗洗脸、烫烫脚了。后来的一路上,我一直很后悔没这么做。
才让丹第二天非要送我们一程。他把我和她挤在一辆老摩托的后座上,一直送出我们很远去。才让丹走的时候留给我们一小塑料袋油炸的果子。头天晚上喝酒的时候,才让丹表示很喜欢我的爱立信大鲨鱼手机。他小孩子一样翻来覆去把玩了很久,但什么也没说。我拎着果子琢磨要不干脆把大鲨鱼送给他得了……后来还是没舍得。所以,果子我没太好意思吃,都留给她吃了。
吃完果子以后又走了好久,我们一直没搭上车。中间有一辆自治区政府的车曾经停下来,给了我们两瓶矿泉水。我看车上还有空位,就说:“大哥,捎上我们一段儿吧。”
他说:“我们去日喀则出差……”
我说:“我们就是去日喀则哦。”
他说:“哦,你们再等等吧,后面好像有个车队。”
我们一直没等到后面的车队。那一路都是这样,藏族人的车明显比汉族人的车好搭。她说:“咱们不能怪那个大哥,人家还给了咱们两瓶水呢。”
我当然理解,我指指她的鞋再指指我的裤子。人家车里那么干净,当然不太乐意让咱们两个灰头土脸的人上车喽。她的小靴子现在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来了,鞋头破了一点儿,踢石头踢的。
后来,我们又遇到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装备精良地都穿着紧身秋裤,都戴着小头盔。我们互相打招呼。他们说他们是计划去珠峰捡垃圾的志愿者。他们知道我们要走路去珠峰的时候,很夸张地竖起大拇指说:“牛逼啊哥们,连个包都不背,就穿着这一身儿去珠峰?就这鞋?”
我们俩穿的都是日常棉服,她穿的小靴子,我脚上也是一双靴子。那时我是个很单纯很感性的文艺小青年,为了不让骑行者们看出我对他们胯下轱辘的羡慕之情,我尽量很淡定地和他们说:“徒步一定要穿1000块钱的登山鞋吗?去珠峰一定需要专业羽绒服吗?上天赐予我们两只脚,难道这不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吗?若说装备,音乐就是我最好的装备!—-我们要一路卖唱去珠峰!”
我举起手鼓摆POSS,心说,惭愧,走了两天还一次没敲过呢,哪儿唱过歌儿啊,光琢磨着蹭车找吃的了……
没想到这番话却深深打动了其中一个骑行者,他留了我一个电话。后来还在天涯社区发过帖子,描述他遇到了两个浪漫的原教旨主义徒步者,把我们夸得和花儿似的。
几年后,他在杭州萧山机场的安检前拦住我,说他后来没再怎么玩儿骑行,再出行都是用纯走的。
我说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他说:“你背着手鼓哦!”
我问:“你后来还去珠峰捡过垃圾没?”
他说:“捡啊!但不是再去珠峰捡,我觉得咱们这代人啊,不能老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事儿。”
我急着过安检上飞机,没等他说完就跑了。
又过了几年,宁波PX事件的时候,我在网络图片中看到过他那张忿怒的面孔。
……愿他安好。
天快黑了的时候,我们才走到日喀则城边。
那个季节的日喀则比想象中要人多点儿,街上一辆一辆的全是4500。后来听说是因为那几天扎什伦布寺有个什么活动。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已经饿成马了,站在寺前看了一会儿,我和她讲了讲世界上最高的强巴佛镀金铜像,高22米,和一座楼房似的……然后,我们往前走,路过一个个小饭店,各种香香的味道。我心里面这叫一个难受。我开玩笑说不行咱们就找个包子铺儿什么的,你掩护,我去抢个包子给你吃。
她当了真,拦着说:“要不咱看看有什么能卖的吧。”
好象没什么能卖的。
那个爱立信大鲨鱼是我唯一的家用电器,舍不得呀。
后来,我不止在一个地方看到这样一幕:一身冲锋衣的背包客举着一张白纸,要不然写着“求路费”,要不然写着“求饭钱”,旁边还放着登山杖和登山大包。其中有些是骗子,有些是为了好玩儿,应该也有些是真缺钱的吧。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干过。真山穷水尽了把冲锋衣卖了不行么?把大包里的零碎儿卖点不行吗?把手机卖了不行么?
也许有人会问:那你那爱立信大鲨鱼手机怎么没卖?
我不是还背着手鼓么,我不是还有手艺在身上么,我不是个已经背着手鼓在川藏滇藏线上一路卖唱,走过好几个来回的流浪歌手么我?
我和她说,你给我点儿力量,咱们来唱会儿歌挣点儿饭钱。
她给我一飞吻。
我们在扎什伦布寺旁边的马路边坐下,帽子摘下来摆在前面。我记得很清楚,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开始卖唱挣饭钱。
我一直很喜欢那些一边摆摊一边行走天涯的孩子,就像我一直很喜欢我那些一边卖唱,一边流浪江湖的兄弟。他们是些有骨气有廉耻相信自力更生的孩子。
人可以向往流浪,实践流浪,但流浪是个多么美好的词汇,无需和落魄挂钩,也不应该和乞讨划等号,他本应跟你自身的能力和魅力合二为一。穷游这个词儿没错,但穷游的精髓不是一分钱不带白吃白喝,真正的穷游者皆为能挣多少钱便走多远路,有多广的人脉行多远的天涯。偶尔厚着脸皮蹭车是可以的,但每时每刻都琢磨着靠占着陌生人的便宜往前走,那还不如回家坐电脑前学习痴汉电车东京热来的崇高。
我们坐在日喀则街头自力更生唱着歌,打算买点儿包子吃。夜色渐深,街上人不多,但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带着微笑走到我们面前,微笑着听一会儿,然后放下一点零钱。
藏民永远是乐善好施的,不论经济社会的辐射力怎么浸渍洗礼,都改变不了藏地文化基因里“布施”这一传统。这一点,是我对藏文化至今为止始终为之着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一毛一块的给散票子,但钱再少也是心意,善意的心意。
不一会儿人品爆发帽子里有了大约几十块钱。饭钱肯定够了。我想看看能不能再多挣包烟钱,就没停。
又唱了四五首歌的时候,来了几个拣垃圾的小孩子,背着蛇皮袋子,吵吵闹闹的围着我们。他们听不懂汉语,但很起劲地和着手鼓打拍子。我给他们唱红星闪闪,唱花仙子,唱多拉A梦,唱我会的所有儿歌,实在没得唱了就开始唱崔健和许巍。
其实唱什么都一样,这帮孩子未必就听过我唱的儿歌,未必人家不把崔健的歌儿当儿歌听。他们不会说汉话,应该是群周边农区来的没上过学的孩子,叽叽喳喳的后藏方言,和拉萨口音差别极大。
我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这帮孩子们乐,好像这边的孩子们有个习惯,就是不抠鼻子。每个人都是鼻孔眼上糊着一块黑黒黄黄的鼻屎,加上黑一道白一道的花脸,那脸真不知道是多久没洗了,上面汗水冲出来的泥沟一条条的清晰可见。衣服就更不用说了,我酒吧里的拖把也比他们的裤子能干净点儿。我让她帮忙拍了个照,那帮孩子推来推去的,谁也不肯好好和我合影。
我唱歌的间隙和她说:“接下来当是义务演出吧,反正挣的钱也够吃大包子了。”
她身旁坐着一个脏脏的小女孩儿,应该是其中年龄最小的。那小姑娘估计也就五岁的光景,一直吃着手指盯着她锡纸烫的头发看。
她摘下帽子,说:“来,你可以摸摸呀。”
我说:“你别整那些没用的,这小丫头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没想到那个孩子听懂了,小姑娘冲着她的方向,犹犹豫豫伸出一只脏乎乎的小爪子。她把孩子的手抓住,一下子摁在自己头发上。
小姑娘“咯”的一声笑了出来,所有的孩子都叽叽嘎嘎地笑了起来,然后挨个来摸她的头发。这会儿轮到她笑了,一边笑一边说:“哎呦哎呦,别揪别揪”
玩儿了有好一会儿,又唱了几首歌。我累了,热乎乎的大包子在前方召唤我。我起身拍着屁股上的土,跟她说:“收工走喽。”
那群流浪儿中有个年龄稍大的孩子,自始至终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他盯着我起身的动作,忽然走了过来……
不论正在看这段文字的人是谁,我都想告诉你我打这段文字时双手有多么的颤抖,呼吸有多么的急促和粗重。
整整八年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单纯莽撞青年变成了个圆滑世故的中年人,我早已失去了我的西藏我的拉萨。可八年前的那一幕,一直在灸刺着我,一直在提醒着我,我这一辈子该去坚持哪些放弃哪些,该如何走接下来的路,到死之前该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那个孩子掏出了薄薄的一叠毛票,橡皮筋扎着,大约有七八张。又黑又脏的手,抽出里面最新的一张,递到我面前,放在我手里。
他对我说:“吐金纳(谢谢)。”
每一个孩子都学着他的样子掏口袋,往我们手心里一毛一毛的放钱。
他们对我们说:“吐金纳(谢谢)。”
他们要拣多少垃圾才能换回这么一点点钱?我在拉萨见过一群和他们一样的小孩子,在街头跟着游客走出去好几条街,只为了等一个可乐罐。他们拣起空罐子,你挣我夺的放在嘴边舔上半天。他们要捡几蛇皮袋垃圾才能换来一毛钱,他们要挣多少个一毛钱才能挣够一罐可乐?
可他们听我唱完歌后给了我一毛钱,还对我说:谢谢。
我嗓子发干眼眶生疼,心口和胃里火烧一般。我看看站在我左前方的她,她低着头在掉眼泪,手捂在嘴上,又在不出声地哭。
若我来世复为人身,请护持我,让我远离心魔永远是个善良的人。
让我永远作个像孩子一样的人吧。
孩子慢慢都变得安静,他们围在她左右,有的蹲在她脚边抬头看她。
我和那群孩子一起,看着她哽咽到上气不接下气。
我沉默地看着她,孩子们奇怪地看着她。简易路灯的黄色光晕铺洒下来,我们站在一副中古的油画里,画外是海拔四千多米的蓝色日喀则,以及满天神佛海会诸菩萨。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个带花的头绳。是那个小女孩递给她的,应该是从垃圾里捡到的。她噙着眼泪边走边戴,后来一直戴着一直戴着,一直带到了珠峰,从她那天晚上戴上起我就没见她摘下来过。
……
八年了,那个头花你现在还留着吗?
四、一口真气过萨迦
一路向西走向萨迦,萨迦再往西是拉孜。然后是定日。
越往西走投宿点越少,当时中尼公路正在修建,能搭的车也少。我们有时候沿着路基走,有时候绕着走,满身的灰土,脏得像两只土狗。蹭过工地的帐篷,晚上一起吃大锅饭,吃完了给道班的人唱歌。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我每唱完一首他们都问:“还会不会其他的现在流行的歌?”他们用干电池帮我们充电,已经关机数天的爱立信大鲨鱼一开机短信箱立刻就满了。
在拉萨的同学们,在短信里对我抛店舍业的不辞而别表示了由衷的感慨和强烈的怀念,他们纷纷用一些生动的语气助词表达了他们心中激荡着的情愫,并对我重新回归后的情形做出了美好的畅想,情感之强烈,措辞之生猛,让我实在难以复述。事实上,我当时立马选择了拆电池关机。
我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找个人报个平安什么的。”她说:“不必了,我不用手机。”
事实上,我当时唯一的这台家用电器在离开我之前,起到的最后一次作用并不是通讯。接下来的旅途中,要不就是有电有插座的地方没万能充,或者有电有插座有万能充的地方没信号。再不然就是什么都没有。
有一段路,没吃没喝没车,没找到地方住,我们并排坐在石头后面,差点儿冻死在凌晨。我怕她当真睡着了被冻死了,就老找她说话还一个劲儿讲鬼,还讲了凶恶的“念”神喜欢出没的红色山崖、恐怖的“赞”神、恐怖的盘羊角。
后来,把她给说烦了,狠狠跺了我一脚。
反正脚都冻木了,我也不觉得太疼。
我们走路慢慢走出了点儿默契,有了个固定的节奏和方式。一般是我在前面走,她跟在我右后方,大约每走一个小时左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没车的时候路上安静得要人命,有车经过的时候老远就可以听到响动,让人精神一振,等车屁股都望不见的时候,又是要人命的安静。有时候,我实在闷得慌,非常想找人扯扯淡聊聊天磨磨牙,但很明显她不是个好的交流对象。我后来想,她真是个难得的话很少的女人,这点儿很罕见,值得肯定。
其实她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体力和耐力。海拔四千多米的长时间行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不过说来也怪,这一路我们走走停停翻山越岭,她居然一次高反都没出现过。
我腿长一点儿,有时候会把她落下十几米,她就捡小石子丢我,养成习惯以后懒得每次弯腰捡,就揣了一口袋。我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你不嫌沉啊?你张嘴喊我一声‘沉又怎么样’。”
陕北人赶羊时有个羊铲,领头羊领着羊群乱跑时,放羊娃用羊铲铲起一铲土石,准确地甩到乱跑的领头羊前面,挡住它让它按正确路线前进。
藏区放羊的时候也喜欢用石头,但不是铲子,而是一种叫“鳄多”的甩石鞭。有牛皮做的有牛毛作的,可以将鸡蛋大小的石头甩出一两百米远。这种鞭子神奇得很,不仅能拦羊,还是不错的武器。一百年前抗击英军的江孜保卫战中,鳄多曾大显神威,击碎过一个又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盗的脑袋瓜子。
我不是羊也不是英国流氓,所以我被石子砸中的时候会很委屈。
她有一回丢石子正好打在我后脑勺正中心,太疼了,疼得我虎躯一震菊花一紧。我是真被打急了,扭头“噔噔噔”跑回去抽她,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连蹦带跳地往旁边的青稞地里跑。我追了两步就不追了,看她好像弯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我冲她吼:“你几个意思啊!还打算捡块砖头扔我啊!”
她抬起脸来,一脸铁青。她也冲我吼,你追什么追追什么追!—-我踩着屎粑粑了!
……
在萨迦附近休息的时候,她袜子大脚趾的地方磨破了个洞。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解决这个难题,后来从衣服上拽出来一根线把窟窿扎了个疙瘩。她走了一会儿嫌脚尖难受,又自己把那个窟窿给掏开了。弄到新袜子之前,她走路都别别扭扭的,像崴了脚一样。
那时候有车就搭,搭上藏族司机的车好几次语言不通,只要大方向没错人家去哪儿我们去哪儿,于是时常莫名其妙投宿在一个离大路很远的地方。第二天想尽办法重新找回主路了一看,我操!怎么又倒回前天路过的地方了。
我已经都记不太清路过的村子的具体名字了,那时营养不良口内溃疡,高反眼花记性很差。但热萨乡的强工村,这个地名儿我一直没忘。
我们在强工村附近闯入了一次聚会。一群人傻乐傻乐地围着,我傻乐傻乐地敲鼓,有人傻乐傻乐地弹后藏六弦琴,几个半老不老的藏族老人傻乐傻乐地跳起了踢踏舞。全部的人里面只有她不是傻乐傻乐的,她坐在藏榻后,一直忙着埋头往嘴里塞油炸果子吃。丢死我的人了,怎么就没噎死她?
我跟老人们学了一会儿踢踏舞,我没藏袍穿,跳不出那个味儿来。
后来2007年看CCTV的春晚,这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拉孜堆谐舞。
我从沙发里站起来跟着节奏踏出舞步,一踩一跺,一踩一跺……
除夕的夜里,身后没有人在吃油炸果子,只有一扇开满烟花的落地窗。
五、天空中的石头龙达
海拔5248的嘉措拉山垭口是我一直无法忘却的地方。
我们到达嘉措拉山垭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个人样儿,又瘦又脏,已经不知道多少天没刷牙洗脸梳头了,两个人头上顶着两块儿毡,手都撕不动。
嘉措拉山垭口是中尼公路的最高点。站在垭口处已经能很清楚看到喜马拉雅群山了,一大堆雪白的峰峦横陈在眼前,一览无余,让人很有成就感,让人高兴得直想笑。翻过这个垭口就是定日县,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珠峰之旅进入倒计时。
有人站在那儿往经幡上绑哈达,大风把哈达吹成一条直线,特有仪式感,特让人眼馋,这把我们俩羡慕坏了。
她问我:“咱们去把别人系上去的哈达解下来,然后再系上去,这样算数吗?”
我说:“你别说的那么可怜行不行,你让我想想办法行不行。”
她在拉萨浮游吧里哭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心酸。一路上不论她看起来有多么饥寒交迫,我都没有感觉到心酸。唯独嘉措拉垭口里她可怜巴巴的这一句话,忽然一下子让我心酸得无以名状。
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吃剩下的捏好的糌粑,她像个赶集卖鸡蛋的农民一样站在我面前。起皮的嘴唇,深陷的两腮,和拉萨时的那个美丽女孩子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让我如何想办法?我只是个站在嘉措拉垭口大风里和你一样灰头土脸的流浪汉,身无分文只有那半袋子糌粑,我该上哪儿去弄根哈达?
我说:“不一定非要系哈达啊。你见过康巴人过垭口是怎么敬山神的吗?他们朝天上使劲儿抛洒印满经文的彩色纸片,一边高声喊着阿拉索索,也就是所谓的抛龙达。龙达多有气势啊!比哈达更有形式美感!况且龙达不一定非要用经文纸片,白纸片也行,没白纸片树叶子也行,实在不行石头子也行啊。”
我自己从没听说过抛石头子儿也算抛龙达……可我那会儿连一张白纸也没办法给她。我想山神是会原谅这种善意谎言的吧,总不至于打雷劈我吧。
我连忽悠带扯,她还真信了。她立马连石子带土的抓了一把朝天抛洒,一边高喊“阿拉索索”……话说还真就那么巧,还真就遭报应了。
迷眼了。
风横着吹!迷的是我的眼!
我立马用一声亲切的语气助词问候了她的大伯父,然后使劲揉眼。我揉得眼泪哗哗的。我说:“等着!回头回拉萨了我非给弄来十斤龙达让你抛不可,我累不死你个倒霉催的。”
她没理我。我隔着指头缝看见她又朝天空抛了一把石头子龙达,又喊了一声“阿拉索索”。
我忽然想起两句歌词: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梦里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
六、流星划过珠穆朗玛
我当时唯一的家用电器(爱立信大鲨鱼R320蓝色)在离开我之前,起到的最后一次作用并不是通讯。我和它分离在定日边检站,它跟着一个开三菱越野的司机走了,它用离去换来了我们最后的上山盘缠,和过边检站的机会。
没有这条大鲨鱼的话,我们指定会功亏一篑在珠穆朗玛前,所以我永远缅怀它。
在大鲨鱼离开我的同时,她右脚靴子的鞋底部分也发出了离她而去的警告。我把手鼓的皮背带裁下来一长条,帮她捆住整只右脚。
快到绒布寺的时候,已经能看到珠峰的全貌,还拍到了日照金顶。我想庆贺一下,就跑去花20块钱买了一罐不知道什么年份的健力宝,我们分着喝,从舌头爽到了脚趾头,居然有了一种极致奢华的感觉。
晚上,我们住到了绒布寺对面的旅馆,服务员不肯还价,我们赖着不走,磨了半天,被安排到一间烧着柴火的屋子过夜。夯土地面冰凉冰凉的,我们和一屋子的藏族马夫围着火堆默默烤火。火烤得每个人的脸都是红彤彤的,背后和屁股底下却是冰凉的。我轻轻拍起手鼓唱歌,人们安静地听,有个扎着红色英雄节的康巴汉子走过来拽起我,然后往我下面铺上一方卡垫。
那是个漫长的夜晚,屋里是噼噼啪啪的柴火,屋外是呜呜咽咽的喜马拉雅山风。围着火堆的人们跟着我的鼓点儿摇晃着身体,分抽着烟,似睡似醒的眯着眼睛。
她抱着膝盖坐在我身旁,乱成毛线球一样的头发被火光映成酒红色。一整夜,我没唱那首惹哭了她的歌。
半夜,我拉她出来看星空。珠穆朗玛的星空之瑰丽,不是笔墨可以诠释的,所有的星星都在闪烁,亮得像亿万颗钻石,让人惊喜的是,我们居然看到了流星。货真价实的流星,像是有生命一样地跑过天空,然后便不知落入了哪一国的红尘中。
我说:“你相信流星许愿这回事儿吗?”
她说:“曾经信过,以后或许还会信吧。你说,一颗流星,意味着一个人死去了,还是一个人出生?”
山风扑面,我听不清她说的是“出生”还是“重生”。
我们在星空下站了许久,抬着头,各自审视自己短暂的半生。
天亮后,好心的马夫请我们吃了方便面,又把我们塞进小马车,一路马铃踱向珠峰。
山路曲徊,空气干冷且硬,那时珠峰刚被重新测量过高度,8844.43米,我们摇晃在马车上,海拔每攀升一截,心跳就加快一点儿。我知道,那不是因为高原反应。
我们终于来到了珠峰大本营。
我们走过一顶顶帐篷,爬上大本营旁的玛尼堆,在风马旗旁迎风抛洒了一把石头龙达。矮矮胖胖的珠穆朗玛峰从丝绸地图上遥远的一点儿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庞然大物。
我履行了承诺,带她站在了当初手指所点的那一点上,一个“比拉萨还要远的地方”。一口长长的气从胸中叹出来,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不知道该拿什么去填充。
她忽然问我:“大冰,你记不记得咱们有多少天没洗过脸了?”
还洗脸呢,我整个人早都馊了好不好。
我看看她那锈色斑斑的脸颊,看看她草一样的头发,以及上面的花,看看她已经分辨不出本来颜色的衣服和用皮条子绑着的靴子。看看她一路上曾流淌过的眼泪和曾带给我的心酸,还有她眼中的我自己。
我说:“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第一个抱着手鼓在这唱歌的流浪歌手,也不确定咱们算不算第一对一路卖唱来珠峰的神奇组合。我甚至不确定在这座高山上应该献给你一首什么样的歌。”
她说:“你给我唱《流浪歌手的情人》吧,哎呀好开心呀,好难为情啊,赶紧唱吧赶紧唱吧。”
她不是这样说的。
她站在猎猎风马旗下,微笑着对我说:“再给我唱一次《冬季怎么过》吧。”
她孩子一样背着手,对我说:“这次我不会再哭了。”
七、嘿,你还好吗?
你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用手机吗?
我一直不知晓你的真实姓名。
中尼公路早就修好了,听说现在从拉萨到珠峰只需要一天。这条路我后来不止一次坐车经过,每过一个垭口,都迎风抛洒一把龙达。想起与你的同行,总觉得如同一场大梦。
我背着的那只手鼓早就已经丢了。
八年了,那个头花你现在还留着吗?
你知道的噢,我不爱你,真的,咱俩真谈不上爱,连喜欢也算不上吧。
我想,你我之间的关系比陌生人多一点儿,比好朋友少一点儿,比擦肩而过复杂点儿,比萍水相逢简单点儿。
一种历久弥新的暧昧而已。
象秋天里两片落下的树叶
在空中幸福的交错片刻
然后一片落入水中随波逐流,一片飘在风里浪荡天涯。
 爱华网
爱华网